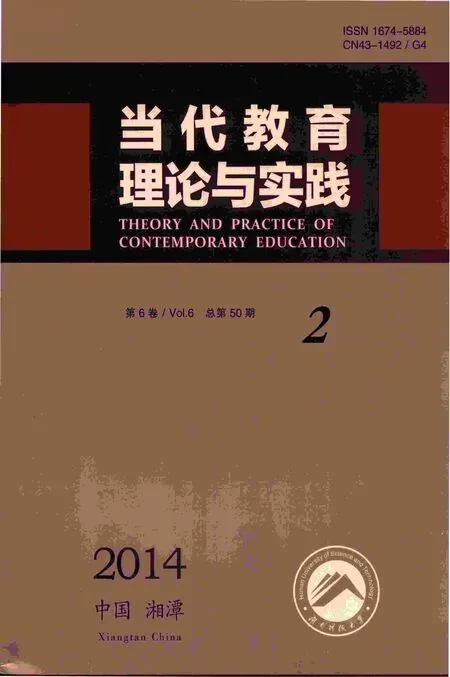論語言知識的特性及其教學策略*
吳 照,李 學
(湖南科技大學a.教育學院;b.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論語言知識的特性及其教學策略*
吳 照a,李 學b
(湖南科技大學a.教育學院;b.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我國語文課程的語言知識內容是在20世紀50年代漢語和文學分科、加強語文“雙基”教學理念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對促進學生語言能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審理百年語文課程中的語言知識狀況可以發現,語言知識在語文課程中的地位動蕩不定,并未受到足夠重視。通過掌握語言知識的層次性、基礎性、實踐性特征,基于現象—概念—規則的語言發展思路、立足于培養人文內涵、語言知識教學應著重于體驗、領悟、實踐等策略的運用。
語言知識;特性;教學策略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思維工具、交際工具、文化載體,具有調節功能和非體系特征的,處在不斷地從無序向有序運動過程之間的,一種復雜開放的多層次多等級的動態平衡的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1]。語言知識即“從語言中抽取出來的對語言這一事物的規律性認識”[2],人們從不同角度來認識和研究語言知識問題,如有的學者從語言科學研究角度探明語言的深層運作機理,有的學者從教師在教學中應掌握的語言知識角度來對語言知識進行研究,本文所提及的語言知識是從教學和學生語言能力提高的角度而言的。課程標準中要求的閱讀、鑒賞、寫作和口語交際能力都是建立在對語言知識掌握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掌握相應的語言知識,語言能力的培養將會是紙上談兵,語文素養的提升也將會止步不前。
1 語言知識的特性
語言知識在語文教學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為了更好地掌握我們所需的語言知識,要求我們必須對語文教學中語言知識有整體的認識,了解語言知識的特性,才能切實可行高效地運用語言知識教學方法。
1.1 層次性
美國心理學家加涅最早提出知識體系結構一說,他認為知識體系的結構猶如“金字塔”,最底層是大量的現象、事實,中間層是概念知識,頂層則是數量相對較少的規則知識,亦或原理知識。用加涅的這一知識體系結構理論觀照語文教學中的語言知識,不難得出如下結論:語言知識體系結構具有層次性特征,它們依次是語言現象知識、語言概念知識和語言規則知識。
語言教學中語言知識的現象知識主要是指具體的語言即言語。實踐證明,語言知識教學過程中,并不是直接學習語言原理或規則知識,而是從學習具體的言語(現象知識)入手,由個別的、大量的、分散的言語的學習再至普遍的、簡明的、系統的語言規則的掌握,因此現象知識是學生掌握語言理論的基礎。對大量的現象知識的熟悉、積累,久之,就會出于本能或認知形成無意識的語感——語音感、語義感、語法感、修辭感等。但這種通過接觸言語現象而形成的語感缺乏嚴謹性、可靠性,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學習語言知識中的概念知識。
概念在很多學科領域被認為是學科的基礎,或知識體系的細胞,語言知識中的概念知識是對現象知識進行分類,將它們的共同本質特征抽象出來,加以概括的知識。相比語言現象知識與規則知識,語言概念知識的重要性不足一提,甚至有學者用“雞肋”一詞形容它在語言知識中的地位。但是語言概念知識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一面,首先,它在語言現象知識與語言規則知識中起承上啟下的作用,語言規則知識的掌握依賴于對概念的理解,如常用的概念有:形聲字、近義詞、反義詞、比喻等。其次,在語言知識教學中學生對概念知識的掌握是體現學生知識修養的重要表現。因此在語言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要求我們對概念知識的學習可停留在大致了解的層面上,可不深究,而對語言知識中規則知識的掌握才是我們的落腳點,且要求更高。
無論是教育學者還是語言教育家都非常重視知識體系結構中居于“金字塔”頂層的規則知識。美國著名教育學家布魯納認為:“懂得基本原理使學科知識更容易理解”,提倡在教材中和教學上給予規則知識以“中心地位”[3]。規則知識貫穿于語言知識各個領域,如語音中的語氣詞“啊”的音變規律、“一七八不”變調規律;詞匯中的近義詞、褒義詞、貶義詞的表達效果、用詞的規范化要求;語法中的具體實詞和虛詞用法上的要求、多項定語的排序等。如果說上文所提及的接觸大量現象知識而形成的無意識的本能的語感缺乏可靠性,那么在掌握規則知識基礎上進行練習而形成的語感則是可靠、持久的,這種語感知識通過有效的訓練能轉化為真正的語言知識。
1.2 基礎性
語言知識是語言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礎。首先,語言現象知識為語言能力形成提供大量的素材,熟悉、記誦大量的言語現象,有利于積累日常所需的字詞,從而提高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同時語言現象知識為學生掌握概念、規則知識打下良好的基礎,因為任何理論知識都是來源于對素材的分析、概括。其次,語言概念知識是語言能力形成的規范,雖然概念在語言教學中沒有受到特別重視,但是它對語言能力的形成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語言現象知識提供的只是大量的、繁雜的素材,并未對其分析、歸類,而語言概念知識是從聚合的角度為學生提供一種規范,如形聲字,在語言教學中先讓學生接觸一定數量的基本字和偏旁部首,接著讓學生對直觀的字詞進行分析與比較,抽象概括出這類漢字的構成規律,從而得出基本字表音、偏旁部首表義的形聲字概念,對這一概念的掌握有利于對此類知識的靈活運用、順利遷移。最后,語言規則知識是語言能力形成的基石。規則知識是屬于“如何做才正確的知識”,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具有指導作用,遷移理論也認為它是進行訓練遷移的最重要的手段。雖然它不能直接轉化為語言能力,但是通過訓練就能順利形成相應的語言能力,有學者通過公式來說明語言規則知識與語言能力的關系:規則+訓練=能力。
語言知識是情感態度形成的依托。情感態度的形成是建立在對知識的掌握以及活動展開這二者基礎上的,因此在語文教學中對語言知識的掌握是前提和基礎。語文教學中語言文字及其組合運用,蘊含著人類豐富的情感、思想和人文內涵,于是有學者認為“語文知識不是客觀知識,而是蘊含人情感和思想的人文知識”,此外,語言知識中表達形式如音節、格調、韻律、結構等也是一種重要的人文特征,“更確切地說,語言的形式反映了一種極為獨特的追求,一個民族正是通過這種追求,才能夠在語言中實現其思維和感知活動”[4]。
1.3 實踐性
按照語言知識的功能來對其進行分類,可劃分為陳述性語言知識和程序性語言知識。陳述性語言知識即“是什么”亦或“用來使用”的語言知識,是指學生在閱讀、寫作、口語交際過程中經常使用的,諸如語匯、句式、修辭等這類知識,它在語言知識的掌握中起輔助的作用,如一般人認為是靜態語言知識的語音知識,在他們看來能認識、讀寫便可,但王榮生等學者卻認為“字音(包括聲、韻、調)往往與抒情表意有一定的關系”[5],從而引導學生從音韻角度來鑒賞詩文。在語言知識教學中,學生需要重點把握的應是程序性語言知識,程序性語言知識即“怎么做”的語言知識,它以產生式來表征,是一種動態的語言知識,這類知識主要運用于實踐,在實踐中操作,指導學生將需要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來,凡是在閱讀、寫作、口語交際中指導怎么做的這一部分知識以及與人們實際運用語言的活動相關聯的知識都屬于這一范疇。如修辭學從運用語言的方式角度告訴我們語言是否有效;文法從語言習慣角度告訴我們語言是否合適;論理學從思想遵循的角度出發告訴我們語言是否合理。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對聽說讀寫能力起輔助作用的靜態的陳述性語言知識,更要重視對語言能力的提升起關鍵性作用的動態的程序性語言知識。
2 中學語言知識教學策略
在語文教學中,對語言知識特性的掌握能更好的引導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制定適切的、有效的語言知識教學方法,探討基于現象-概念-規則、立足于培養人文內涵、形成以培養語言能力為核心的語言知識教學策略。
2.1 引導體驗豐富語言知識
經過提煉而形成的科學的、有序的學科系統知識只是語言知識的一部分,語言知識中更多的是無法言傳的現象、事實知識,這類知識通常與人們記憶中的詞句及其具體情境相關聯。因此在語言教學中,體驗是學習這部分知識最好的方法,即通過直覺的方式直接把語料事實積淀在主體內部。教師應引導學生結合自身經驗從已有語言圖式出發,不斷積累這類感性的現象語言知識。如于漪老師在引導學生鑒賞《春》最后三段,“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領著我們上前去。”首先引導學生對文章的修辭手法的把握,春天像娃娃、像小姑娘、像健壯的青年這一擬人手法的運用,接著延伸至讓學生推導出描寫春天景色的詞語:春意盎然、千姿百態、青春活力。將描寫春天的修辭與詞語運用緊密結合,有利于讓學生形成一套對季節的描述方法,由此建立和儲存更多的關于“擬人”的言語材料和情景圖式。
2.2 通過領悟提煉語言知識
語言教學中既要重視學生已有的言語實踐,也要運用理性的語言概念、規則知識來概括提煉實踐經驗,并促成新經驗的形成,需要在教學中引導學生領悟看似雜亂無章的語言知識現象所包含的共同規律,在語文課程中提煉出最基本、最需要的語言知識。比如在學生積累一定的言語材料并掌握一定感性語言知識基礎上,可以結合上下文或具體情景引入概念,再用方法性規則知識進行指導,促使學生反省并調整原有的知識圖式,形成更高層的語言能力。反過來,在具體的語文活動中,又能夠以這些規則為標準來鑒賞課文,或評價修改自己的聽說讀寫作業。如與“幽”字組合的詞有:“幽靜”、“幽寂”等詞,粗看似乎差不多,但要仔細辨別才能知曉彼此的差別,“幽靜”和“幽寂”有何不同,各自該用在何處都需運用一定的語言規則知識來進行甄別、領悟、比較、提煉,因為這些存在細微差別的詞語是學習和生活中的常用詞,且對表達是否準確、交流是否順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2.3 反復實踐運用語言知識
語言知識轉化為語言能力是建立在教學得法的基礎上的,因為語言知識轉化為語言能力存在中介環節,是與社會環境、言語主體的心理因素等成分緊密聯系的,因此,語言知識轉化為語言能力的前提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反復運用語言知識以至形成語言習慣。如果語言知識不能成為一種習慣,學習的時候似乎會了,但不能按照學到的知識去運用,并形成一種不期然而然的潛意識行為,那么知識轉化為能力只能是一紙空文,當知識轉化成了習慣,就算知識模糊了,但這些知識已經融化于語言運用中,學生將受用無窮。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在語言教學中須加強練習,包括單項練習及安排在各個教學環節中的結合聽說讀寫實踐的練習。學生經過屢次實踐,讀寫的行為能從意識的形態中解放出來,變為潛意識的習慣性行為。
2.4 深刻反思內化語言知識
這里的反思是指從語言知識與民族情節、審美教育、思維訓練以及語言修養的結合來對語言知識教學進行反思,是從學生的文化內涵層面著手以尋求更好的發展道路的反思。首先,語言體現著不同民族的認識世界的方法,也體現民族的價值觀念,它不僅是人類進行交流的工具,還是民族個性的標志、精神文化的象征。語言教學要進行實在的思想和靈魂的教育,要將文化情節滲透到學生的思想中去,維護和提升漢民族語言的地位和重要性。另外,實現語文教學的人文性,是立足于言語知識的運用這一中心,通過反思性實踐指向所有語文活動,致力于學生人格完善,有意識加強學習語言知識過程中的思想情感熏陶。“只有導向教育的自我強迫,才會對教育產生效用,而其他所有外在強迫都不具有教育作用,相反,對學生的精神害處極大,最終會將學生引向對有用性世俗的追求。”[6]這種教育上的“自我強迫”就是一種反思實踐,在反思中學生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語文教學中,“通過本文學習,要理解……高尚的品質,要品味偉大的……精神,要樹立……遠大的理想”等指令性話語不少見,這些宏大的正確的空話并不能深入人心。只有通過自我反思實踐活動,將“我”投身到具體情境內容中去體驗、感悟,經過探討,才能有效地建構教學內容的個人意義[7]。語言知識的內容同樣需要深刻的反思實踐才能夠內化為學生的語文素養。
[1]倪寶元.語言學與語文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2]鄒賢敏.打開學習語言的大門[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美)Jerome S.Bruner.教學論[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
[4]王榮生,韓雪屛.初中語言1·語言知識新視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5]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鄒 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7]李 學.也談語文教學的人文性及其實現[J].中國教育學刊,2012(12):60-63.
G642.0
A
1674-5884(2014)02-0129-03
2013-11-04
湖南科技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課題(S130052);湖南省教育科學基礎教育教學研究基地成果
吳 照(1988-),女,湖南岳陽人,碩士生,主要從事語文學科教學研究。
(責任校對 羅 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