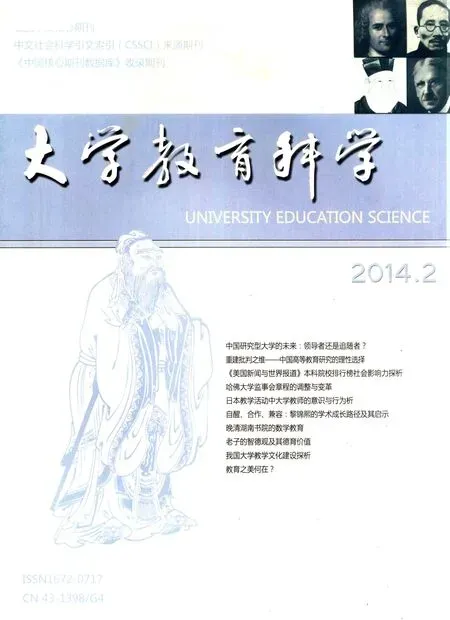《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本科院校排行榜社會影響力探析
□ 劉寶存 李函穎
近年來,大學排行榜成為高等教育的熱門話題之一,同時也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 & World Report,以下簡稱《美新》)雜志于1983年推出本科院校排行榜(America’s Best Colleges),主要以美國國內高校的本科生教育為評選對象。自1987年起,《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由此前的兩年一次改為每年出版一次。在1983年誕生之時,連雜志工作人員都從未料想到其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今天,《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不僅成為美國各類學術論文、學術會議的研究主題,而且對美國的高等院校、社會大眾、甚至政府部門都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一、《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學生擇校的影響
《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誕生之初就是以幫助學生挑選適合自己的大學為宗旨,學生群體作為高等教育的受眾一直是《美新》雜志的主要目標人群。許多美國學者也在研究中證實了《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學生擇校的影響力。一般而言,擇校時更傾向于參考《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人群主要有五類: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高收入家庭、致力于繼續深造的優秀高中生、異地求學者、亞裔家庭,而使用排行榜進行擇校的學生基本都進入了新生錄取標準更為嚴苛的私立大學[1]。此外,中產家庭對排行榜的使用率最高,其他人一般只是用排行榜來確認自己的選擇,很少根據排行榜直接擇校,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比其他人更少使用大學排行榜[2]。具體而言,《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會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學生擇校產生影響。
一是直接為學生和家長提供高等學校的有效信息。《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將其評估的所有高等學校分門別類,學生和家長在擇校時可以便捷地了解到一所大學在同類型大學中的相對位置。同時,它還包括最具性價比大學排行榜、本科教學最佳大學排行榜、次優學生可以選擇的頂級大學排行榜、傳統黑人大學排行榜等指向性明確的特色排行信息,可以滿足不同客戶個性化的需求。此外,《美新》雜志每年發行的“最佳大學指南”特刊中還包括學校的地理位置、獎學金項目、申請日期等額外信息。
二是賦予高中升學咨詢教師話語權,間接影響學生擇校。在美國,每所高中都會為學生配備升學咨詢教師,指導學生申請大學。一般而言,他們都是對于美國高等教育十分熟悉的專業人士。2010年,《美新》雜志將“高中升學咨詢教師調查”納入評估指標體系,此舉不僅進一步提高了《美新》排行榜在高中生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提高了《美新》排行榜在高中升學咨詢教師心中的地位,從而間接影響學生擇校。
三是通過影響高等學校的新生錄取標準來影響學生的擇校行為。一般而言,除了有特定目標的學生外,大部分學生在擇校過程中都需要細致地考察各所學校的錄取標準和錄取率,結合自身的優劣勢,選擇最有可能被錄取的學校,盡量減少被高校拒之門外的幾率。有學者在對“《美新》排行榜與高校錄取率之間的關系”做過研究后發現,一所學校的排名上升后會導致其錄取率的下降,反之亦然[3](P6-7)。
當然,在看到《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于學生擇校的影響的同時,也應注意不能過分夸大其影響。事實上,學生在選擇高等學校時的考量因素有許多,既包括經濟因素(例如學校所能提供的獎學金數量),也包括學校的學術聲譽、生師比、學校離家距離等因素,大學排行榜上的名次只是影響因素之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2012年的“全美大學新生調查”(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or Fall 2012)中公布了“大學新生擇校的影響因素”,其中排名前6名的因素分別是:這所學校有很好的學術聲譽(63.8%)、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找到了好工作(55.9%)、我得到了這所學校的經濟資助(45.6%)、就讀這所學校的費用(43.3%)、我曾經到過這所學校(41.8%)、這所學校的社交活動很有名(40.2%)。《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美新》是美國唯一一本刊登大學排行榜的全國性雜志)的影響力在23個選項中僅排名第12[4]。
二、《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高校發展的影響
雖然《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初衷是為學生及家長擇校提供信息,但隨著排行規模的日益擴大,其對美國高等學校的影響力逐步顯現,部分學校甚至會將其在《美新》上的排名寫入招生簡章作為招攬學生的砝碼。盡管大學校長們不愿正面承認《美新》排行榜對其所在學校的影響,但許多事實證明《美新》排行榜在校長們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2000年,由于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學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的一名管理人員沒有及時將學校當年的最新數據呈報給《美新》雜志,致使《美新》在對全國性文理學院進行排行時使用的是其以前的數據,該校名次從第二梯隊(Tier2)滑落至第三梯隊(Tier3)。學校為此大為惱火,直接將這名管理人員開除[5]。具體而言,《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高等學校的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強化了高等學校間的競爭環境
美國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4000多所各種類型的高等學校間自然存在相互比較和競爭。《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將評估對象分門別類,以數字這種直觀的形式反映同類型學校間的差距。因此,《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出現不僅使原本學校間的“私下較勁”顯像化,而且也使競爭更具有指向性。尤其是在排名方法進行標準分改革之后,一所學校在排行榜上的具體名次不僅取決于學校自身的實力,而且還要取決于同類型其它學校的表現,更是讓校際間的競爭白熱化。需要指出的是,不同類型之間的高等學校不具備可比性,且同一分類體系中名次相隔太遠的兩所學校一般也不將對方視為競爭對手。如作為全國性大學的哈佛大學與作為全國性文理學院的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雖然經常同為這兩類排行榜中的第1名,但人們一般不將這兩種不同層級的學校進行比較。
雖然《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強化了同類型高等學校之間的競爭,但是這并不會導致院校間合作的減少。例如,雖然《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將“班級規模”列為評估指標之一,倡導小規模班級越多越好,但是這并不影響院校間合作開展遠程教育。雖然遠程教育涉及的學生人數眾多,但一般參與遠程課程授課的教師對于其它學校而言屬于兼職教師,這類教師不在《美新》的統計范圍之內,其所開設的課程也不會影響學校的排名。因此,“如果高等學校間的合作有所減少,絕不應該歸咎于《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6](P19)。
此外,《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所引發的激烈競爭還催生了一個“新精英大學階層”。這個階層的成員包括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埃默里大學、賴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美國優秀高中畢業生的規模遠超過傳統精英大學(一般指“常春藤名校”,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等)的招生規模。在供需不平等的條件下必然致使大批優秀高中畢業生無法進入傳統精英大學,這批“多余”的優質生源理所當然地成為其它名校競相爭奪的目標。《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將“新精英大學”的名次排得很高,使得優質生源覺得申請這些學校也是可以接受的[7](P226)。
(二)促使名牌大學開始重視本科生教育
在美國,許多知名大學將大部分的教育經費用于科研而非教學上。原因很簡單,因為從事科學研究既能為學者和其所在學校帶來榮譽,而且當其轉化為現實產品后也能給學者個人及學校帶來大筆收入。因此,擁有眾多一流學者的名牌大學樂此不疲地將教育經費投入到科研領域,學者一旦成名后也極少親自給本科生授課。這種大學發展模式基本上是以犧牲本科教育為代價的。正因為如此,美國許多文理學院的本科教育質量要高于名牌大學。《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評估對象是各所學校的本科教育質量,這對于一向以研究生教育為主的名牌大學而言無疑是當頭棒喝。隨著其影響力的擴大,為了爭奪優秀國內生源和留學生,眾多名牌大學也開始將發展本科生教育提上議事日程。以哥倫比亞大學(下稱“哥大”)為例,1992年喬治·魯普(George Rupp)剛剛就任哥大校長時就提出要將工作重點放在發展本科生教育上。9年任期內他對哥大兩個本科生院的教務和學務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哥大的本科申請人數翻了一番。由于錄取總人數基本保持不變,哥大的錄取率足足降低了50%,其在《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上的名次也是扶搖直上[8](P101-102)。
(三)影響了高等學校的新生入學要求
“新生錄取標準”是《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重要評估指標之一,它包括錄取率、新生的高中排名、SAT分數等內容。這些評估指標都會對高等學校產生一定的影響。蒙克斯(James Monks)和埃倫伯格(Ronald G.Ehrenberg)對1987~1997年間《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中前25名的私立院校(包括私立大學和私立文理學院)排行結果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當大學排名上升時,其新生錄取標準也會有所上升。具體而言,當一所學校的排名每上升1位,這所學校第二年就會收到更多的入學申請,從而使學校的新生錄取率(新生錄取總人數/申請該校的總人數)降低0.399%,錄取學生的SAT平均分數上升2.8分,新生注冊率(大學新生人數/錄取人數)上升0.2%。此外,為了吸引更多學生注冊,排名下降的學校也會增加助學金的數目[3](P6-7)。馬克·梅雷迪斯(Marc Meredith)拓寬了研究對象的范圍,進一步證實了《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高等學校新生錄取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梅雷迪斯發現《美新》排名對公立大學的影響要大于私立大學。因為即使是排名靠后的私立學校,其錄取學生的SAT平均分也比較高[9](P459-460)。
為了提升在《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中的名次,許多排名靠前的大學通過“提前錄取”(early decision)來降低錄取率,以此扭轉自己的被動地位。主要做法是:在正式錄取之前讓應屆高中生在畢業前一年的秋天就提前申請一所他們最心儀的大學,一旦被錄取,學生們就不允許再申請其它大學。此舉不僅能夠有效地提高被錄取學生的注冊率,而且能夠降低錄取率。例如,按正常招生步驟來計算,某所大學有10000名申請人,而它的錄取名額是4000人,最后注冊人數為2000人。該校的的錄取率就應該是40%,注冊率為50%。但假如這所學校實行“提前錄取”政策,10000名申請人中有2000人提前申請,而它錄取其中的1000人,所有這1000人必須注冊入學。在完成“提前錄取”后,假如該校通過正常途徑申請的學生也能保持50%的注冊率,那么這所學校只需要在剩下的8000名申請人中錄取2000人。最終,這所學校的錄取率為30%,注冊率則達到67%[6](P11)。“提前錄取”除了可以降低錄取率、提升注冊率外,還能減少學校助學金的金額,緩解財政赤字。因為“提前錄取”意味著無選擇性,學生被錄取后不得申請其它學校,因此,參與“提前錄取”的學生大多都是來自中上階層的家庭。而貧困家庭的學生一般傾向于參加正常招生程序,同時獲得多所學校的錄取之后,選擇進入提供助學金更多的學校。
(四)對大學經費的影響
美國大學籌措教育經費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學生學費。《美新》本科院校排行評估指標體系中有一項指標是“生均教育經費”,一所學校的生均教育經費越高,其在排行榜中的名次也會越高。相反,學校在《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中的名次也會促使學校對學費進行調節。有學者曾對《美新》排行榜與大學學費之間的關系做過研究,他們發現一所私立學校在《美新》排行榜上每上升1名,它第二年的學費就會上漲0.3%。由于在美國人心目中,低收費就意味著低質量,因此,當頂級私立學校的名次下降時,其并不會降低學費標準,而是以提供更多的助學金這一變相降低學費的方式來吸引優質生源[3](P9)。就學費而言,《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私立大學的影響比公立大學大,因為私立大學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能及時根據排名變化調整自己學校的學費。同時,《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排名較低的大學的影響比排名較高的大學大[9](P459-460)。
大學經費的另一個來源就是校友捐贈。校友捐贈是私立高等學校獲得經費的主要途徑,以往公立高等學校并不十分重視這一領域。但隨著州政府撥款的減少,公立高校開始加大對校友募捐的宣傳力度。同時,《美新》雜志認為校友捐贈比例是畢業生對學校教學質量認可的表現方式之一,將其納為評估指標,因此,提升校友募捐額度可謂一石二鳥。一般而言,當一所學校的排名上升時,其能獲得的校友捐贈也會有所增加。因此,高等學校一方面努力改善在校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環境,以求他們將來能為母校慷慨解囊。另一方面,各所學校也開始向歷屆校友展開猛烈攻勢,呼吁他們踴躍捐款[8](P100)。
在美國,高等教育工作者對《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感情十分復雜,愛恨交織。他們既享受學校排名上升所帶來的好處,如容易吸收更多的優秀學生、提高就業率等,同時又痛恨《美新》簡單地以數字的形式來對高等學校的質量進行排名。其實,無論排行結果是否公正,《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極好地依托了《美新》雜志這一媒體平臺,從外部對高等教育系統施壓,迫使其進行調整,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時也應注意到,高等學校各方面的變化并非是《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一家之力,而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
三、《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公共政策、大學評估和雇主的影響
《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影響力的輻射范圍絕不局限于學生和高校,它還對公共政策、大學評估、雇主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在美國,人們經常將新聞媒體的形象與“客觀”、“公正”聯系起來。由于排名方法公開、透明,因此,《美新》雜志在對大學進行排名時不僅獲得了大部分民眾的認可,同時也為政府或其他組織的決策提供了信息依據。
《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是否有其獨特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2007年,有學者對《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與公立大學所獲州政府撥款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美新》本科排行榜的刺激下,公立大學的生均支出增長了3.2%,州政府的生均教育撥款也增長了6.8%,但是學生的學費并沒有因此而增加。研究認為,“《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引起了人們對大學質量的關注,而州政府對排名所作出的回應是增加對公立大學的生均教育撥款,而不是提高學費,這對于學生而言是一個好消息”。同時,他們還強調,“雖然目前有超過100種介紹大學的書籍和手冊,但《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仍然牢牢地統領著大學排名的這個市場”[10]。
此外,《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高等學校的績效責任。2006年,美國聯邦教育部發布報告指出,美國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在入學機會(accessibility)、支付能力(affordability)、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和質量(quality)四個方面。其中,《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被看作是績效責任的一個重要因素和質量評價標準。報告呼吁美國高校應當“重視績效責任和透明度,提供有用且可靠的數據信息,以便對同一類型的高等學校進行比較和排名”[11]。盡管聯邦教育部公開認可《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地位的這一做法遭到了許多大學的批評,他們認為此舉會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的多樣化,但這份報告仍然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幾個主要的大學團體參與到高校績效責任運動中來。如美國州立大學和贈地學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 and Land-Grant Colleges)與美國州立高等學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聯合開發了“自愿績效責任系統”,這是唯一一個要求高校提供評價數據和學生學習成果數據的系統[7](P224-225)。
(二)對大學評估的影響
《美新》排行榜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和其所帶來的巨額經濟利潤,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它組織或機構參與到大學評估中來。例如,1999年,在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下印第安納大學推出了全美學生學習參與情況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不過,由于NSSE曾向高等學校的管理者承諾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不會公開數據,因此,其很大程度上僅是高等學校用來了解學生學習參與的內部工具。目前,NSSE已開始與《美新》合作,為其提供部分教師調查問卷[12]。此外,《美新》排行榜所使用的排行方法也引起眾多機構的效仿,如我國的網大排行榜所使用的評估指標體系就基本上是以《美新》為模板的。
(三)對雇主的影響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文憑是學生進入就業市場的“敲門磚”。美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就進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因此,學生要獲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其實并不高。在這種情況下,雇主對聘用人員的選擇標準會參考兩個條件:一是學生的在校成績,二是這所學校的排名。一般而言,在應聘人員同等優秀的條件下,其所畢業學校的聲譽會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另外,由于許多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后選擇的工作與自己在大學學習的專業并不一致,也就是說,雇主在招聘時會遇到許多來自不同專業的應聘者。在對應聘者專業不熟悉的情形下,雇主一般也會以《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作為錄取的參考依據之一。2004年,美國法律專業就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 Placement, NALP)曾對139家律師事務所的221名管理者進行過調查,其中72.1%的受訪者承認《美新》排行榜會影響到他們的聘用流程,只有“近期畢業生的表現”一項指標的影響力超過《美新》排行榜,達到77.9%。此外,這些受訪者還表示《美新》雜志是他們會經常咨詢的對象,83.6%的人表示曾使用過《美新》排行榜。盡管這是針對《美新》研究生院排行榜的影響力調查,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雇主的影響[13]。
四、《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對《美新》雜志自身的影響
《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是《美新》雜志的產物之一,但其對《美新》雜志本身產生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附屬物的地位。在很多人心中,《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甚至已經可以完全代表《美新》雜志本身了。具體而言,其對雜志本身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為雜志帶來巨額的經濟利潤。據統計,包含《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9月份特刊的發行量則高達200多萬冊,是其平時發行量的好幾十倍。每年就能為雜志帶來幾千萬美元的收益。此外,排行榜的巨大影響力也為雜志吸引了眾多的廣告贊助。《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已經成為《美新》雜志名副其實的“搖錢樹”。
二是提升雜志在世界范圍內的知名度。《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雖然是編輯的偶然之作,但隨著其影響力的擴大,逐步將《美新》雜志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雖然排行榜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指責,但也從另一方面提升了其在世界范圍內的知名度。每年九月,當最新一期排行榜公布后,各國高等教育研究者們都會在第一時間內對其進行研究。
三是形成以排行榜為特色的雜志內容。1983年以前,《美新》雜志的主要形態是專題述評,但自從嘗到本科院校排行榜為其帶來的甜頭后,《美新》雜志對于排行榜的熱衷便一發不可收拾。本科院校排行榜之后,其又推出了研究生專業排行榜、高中排行榜、醫院排行榜、汽車排行榜等,排行范圍從教育領域拓展至日常生活領域。目前,各種類型的排行榜已經成為《美新》雜志的特色內容。
五、結語
《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作為大學排行榜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各個利益相關者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贏得了社會大眾的認可;另一方面也遭受了多方攻擊,許多學者認為它只是媒體的商業行為之一,是嘩眾取寵的小丑。盡管社會各界對《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的評價毀譽參半,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已經成功引起了美國社會乃至世界范圍的關注,而且對美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一點可以確定的是,無論美國高等教育界人士如何抵制,在可預見的將來《美新》本科院校排行榜還會年復一年地發行。
大學排行榜對社會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不加分析地完全肯定或者一味地排斥大學排行榜的影響,都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理性看待大學排行榜,正確利用大學排行榜影響力的正能量,引導高等學校提高教育質量,幫助學生做出正確選擇,指導政府做出正確決策。
[1]Patricia M.McDonough,Anthony Lising Antonio,Mary Beth Walpole,Leonor Xóchitl Pérez.College Rankings:Democratized Knowledge for Whom?[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8(5).
[2]Howard McManus Michele.Student use of rankings in national magazines in the college decisionmaking process[D].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2002:18.
[3]James Monks,Ronald G.Ehrenberg.The Impact of U.S.News & World Report College Rankings on Admissions Outcomes and Pricing Policies at Selective Private Institution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July 1999.
[4]UCLA.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or Fall 2012[EB/OL].http://www.heri.ucla.edu/monographs/TheAmericanFreshman2012.pdf,41.
[5]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dministrator Ousted After Failing to Reply to “U.S.News’Questionnaire”[EB/OL].http://chronicle.com/section/Home/433,2011-02-02.
[6]Ronald G.Ehrenberg.Reaching for the Brass Ring:How the“U.S.News & World Report”Rankings Shape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n U.S.Higher Education[A].Macalester College,June 12th,2001.
[7]劉念才,程瑩,Jan Sadlak.大學排名:國際化與多元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9.
[8]程星.細讀美國大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9]Marc Meredith.Why Do Universities Compete in the Ratings Ga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he U.S.News and World Report College Rankings[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Volume 45,No.5,August 2004.
[10]U.S.News & World Report.How the Rankings Affect State Education Spending [EB/OL].http://www.usnews.com/blogs/college-rankingsblog/2008/02/11/how-the-rankings-affect-stateeducation-spending.html,2011-02-01.
[11]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A Test of Leadership: Charting the Future of U.S.Higher Education[EB/OL].http://www2.ed.gov/about/bdscomm/list/hiedfuture/reports/final-report.pdf,2011-02-01.
[12]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About NSSE[EB/OL].http://nsse.iub.edu/html/about.cfm,2011-02-01.
[13]Michael Sauder,Wendy Espeland.Fear of Falling:The Effect of U.S.News & World Report Rankings on U.S.Law Schools[R].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October 200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