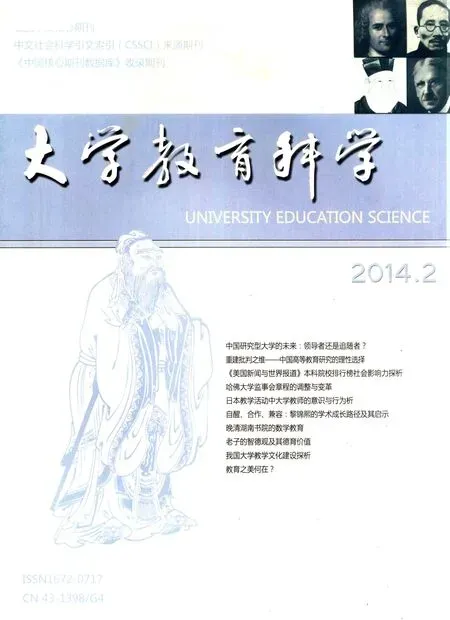中國研究型大學的未來:領導者還是追隨者?
□ [美]約翰·奧布雷·道格拉斯著 徐丹 蔣扇扇譯 胡弼成校
中國迅速擴張高等教育系統并推動一批大學躋身世界一流的雄心似乎所向披靡。這一雄心最早提出是在1998年,當時中國政府正啟動一系列推動中國部分經濟和機構面向市場的政策。北京大學慶祝100周年華誕之際,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當眾宣布中國大學將實行擴招和改革。當時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很小,每年只有約20萬名畢業生,事實上這些畢業生以本科生為主,碩士研究生很少。1998年之后,普通高校的招生幾乎翻了兩番,現在超過3000所高校每年培養的大學畢業生超過630萬。中國的在讀大學生數已經超過2900萬,數量排名世界第一。到2010年,大約24%的18~24歲傳統高等教育適齡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
但是,無論是江澤民主席那一屆政府還是其后續政府,他們的雄心都不只是高等學校入學人數的量的增長。過去十年里,中國日益關注國立和地方大學的質量,尤其是大學如何才能幫助中國在知識經濟社會發展。中國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國家政策,由985工程開始(發表于1998年,見表1和表2),到最近的國家中長期教育與改革發展綱要(也稱2020藍圖[1]),目的都是推動建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學。

表1:985工程初期9所大學(中國常青藤聯盟)

表2.985工程后期增加的30所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重慶大學大連理工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吉林大學蘭州大學南開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東北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中國海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天津大學同濟大學中國電子科技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
2020藍圖在支持一些中國大學向世界最優秀、最有影響的大學邁進上似乎有所進展,包括提供更多自治權以及更多政府津貼來改善學術管理。中國政府提出,不僅要發展大眾高等教育,而且要建設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因為這些世界一流大學是未來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和民族自豪感的核心要素。
接下來將呈現中國高等教育的雄心將面臨的主要挑戰的基本背景。包括: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不斷增長的大學入學需求;大學入學人數的增長和大學畢業生高失業率;影響學習過程并可能抑制創造性的文化因素;境外大學分校的合適角色;還有對重點高校的管理與領導的擔憂。這一系列問題不僅在中國學術界正得到廣泛討論,而且對于那些觀察到中國大學實現的實質性進步——從毛澤東時代作為浪費的特權和蔑視的一個符號轉化為促進中國形成自由市場、加強國際參與的核心力量——的人來說,也是熱烈討論的議題。大學比任何國企或私人企業,任何其它單一機構,更能展現新中國的氣象。
決定中國能否成功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尤其是能否實現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熱望的,可能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首先,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學一樣,中國大學有更大的動力從不斷增加的教育部的要求和干預轉向大學自身追求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質量提升的院校文化。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世界一流大學的真正內涵。迄今為止,中國大學(像其他大學一樣)只是在追求少量指標:教師獲得諾貝爾獎及其它頂尖國際獎的數目、論文引用指標、科研經費、研究生百分比、授予學位數及其它類似數據(例如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所采用指標)。然而,其它沒有轉化為加權數據的因素也值得考慮。
研究型大學僅僅只是它們存在于其中的社會的反映,是遵從當地文化和政治準則呢,還是社會的領袖、創新思想和論爭的產生地?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們沒有公開討論過這個問題。然而,這個隱藏的問題是緊張的根源,問題最終可能會隨著中國中央政府或快或慢地推進經濟自由而慢慢浮現。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學在世界舞臺上主要是追隨者,受政府主導的政治文化制約,同時也不免受到世界事件(例如阿拉伯之春①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又稱“阿拉伯的覺醒”、“阿拉伯起義”,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反政府運動。——譯者注)影響,但是一些跡象表明這一狀況可能會發生變化。全球化,包括與美國、歐洲及其它地區大學教師和領導層越來越頻繁的互動,使得中國學術領導們逐步形成共識,即大學需要不斷提升獨立的水平,包括提高學術自由水平和改進院校內部驅動的質量控制的水平,才可能完全成熟起來。這毫無疑問將會是一個受制于中國社會準則和強大的政府之手的緩慢過程。
一、2020年藍圖
正如前文提到的,985工程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旨在支持一些頂尖的高校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舉措。這一工程最初從9所大學開始,到2004年支持對象已經擴大到40所①實際為39所。——譯者注大學[2]。
那么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競賽效果如何?依據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過去十年,中國大學排名有了明顯進步,但是想要進入精英行列,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中國2200所高等學校中,只有6所位列前300名,還有11所在301~500名之中。由于排名指標對科技領域的偏好,排名最前的是清華大學,位于第151~200位之間。北京大學同樣位列200名之內。其它排名,其結果近似,反映了對頂尖大學相對狹窄的理解。
考慮到中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和重點建設一批一流大學(包括在所謂的211工程之下將實施前蘇聯專業化模式的700所高校合并為300所)的時間不長,這個結果已經是很大進步。但是,同樣清楚的是,中國教育部和大部分高校期望今后10年有更好的排名結果。
正如北大副教授蔣凱所說,“建設一個高質量”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高等教育系統(高等教育強國)在中國已經成為主要的政治議題[3]。這不僅包括對選擇的精英大學增加支持,而且還包括全面提高質量,后者將會隨著中央政府要求院權問責和一些其它舉措(例如政府關于教師發展的政策)而得到強化。
2020藍圖是直接反映高等教育強國概念的最新政府政策,內容包括國家面臨更大壓力和興趣支持邊遠和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的大學[4]。2020藍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中國脆弱的學術文化和環境(甚至最頂尖的中國大學也如此)的回應。藍圖提出:“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要求。”[1]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大前校長許智宏,在華中科技大學的一個演講中宣稱,中國事實上沒有世界一流大學。據《人民日報》報道,許智宏列出了他認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具備的三個特征:(1)有世界知名的教授從事高水平科研;(2)產出能夠影響人類文明和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成果;(3)擁有眾多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杰出校友。許智宏說:“如果一所大學具備這些特征,它就能稱為世界一流大學。”[5]在他看來,沒有哪一所中國大學具備這些特征。
許智宏的評論出來不久,中央政府就頒布了2020藍圖。2020藍圖其實部分地是江澤民北大指示的延續,其主要組成部分是推動最頂尖的40所大學邁向更高水平的自治,獲得更豐富的資源,為中國大學現代化奠定基石,以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它意圖通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發展“國際知名的重點學科”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來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全球競爭力。
2020藍圖指出,中國高等教育未來還會持續擴招,但是將放慢步伐。到2020年,在校大學生數比起當前還會增加500萬。其目標是將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從2009年的12.4年提高到2020年的13.5年。藍圖也將支持將適齡青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當前的25%提高至40%。此次藍圖較之前的政策更多地強調了學前教育和成人教育。除了這些宏觀的量化目標,2020藍圖希望在高等教育方式和組織上取得實質進展[6]。包括改變傳統教育的死記硬背這一越來越被視為阻礙創新思維和創造力的因素。
約克大學的查強教授說:“這些目標使我想起圍繞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展開的討論。所謂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指為了同時保證效率和GDP增長,在經濟領域以市場化為特征,而在政治領域依然維持集權模式。”查強教授對2020藍圖持批評態度,理由不在規劃所提倡和禁止的內容,而是因為這個規劃回避了一些東西。中國政府所提出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以效率和達到目標的速度為由,依然以強烈的政府意志為特征,并采用至上而下的方式推進。這種模式吸收了鄧小平‘不要爭論,只要去做’的智慧”[7]。
就短期而言,藍圖對中國大學意味著什么?2020藍圖似乎只是強調了要擴大仍然十分有限的大學自治權,以及要為985工程大學提供更多尤其用于大學質量保障上的資金支持。
二、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背景概覽
2020藍圖偶爾提及但是沒有直接提到的,是創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學所面臨的一些挑戰,更一般地說,是演進中的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所面臨的挑戰。包括的宏觀問題有:城市化與貧窮帶來的并發癥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的不斷升高與入學需求的不斷上升,以及對中國教育質量的擔憂。在我看來還有兩個主要問題:首先,官僚主義和對科層制和榮譽職位的持續激情;其次,缺乏對院校管理和師生個人自由而言非常重要的大學自治。
1.城市化和貧窮
中國和其它許多發展中國家當前正在經歷的一個重大轉變便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人們希望在城市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教育機會。近十年來,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人口,造成了諸多問題。這一狀況部分是國家政策影響的結果。首先,農村人口的流失以及中國廣大的西部省份的經濟遲緩已經向政府提出挑戰,即中央政府如何才能通過為這些地區的城鄉發展提供支持從而將人口流動控制在合理范圍。由于重點大學主要分布在東部大城市,區域間分布不均,而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經濟貧困地區極易發生社會動蕩,這些都推動政府頒布政策增加那些地區的受教育機會和其它公共服務。
其次,城市增長的性質帶來困境。中國不允許人口自由流動,若要居住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需要獲得戶籍許可(戶口)。在近五億的整個城市勞動力中,大約65%是有戶口的,他們有安定的工作、相對較高的薪水和福利。其他35%的勞動力則是獲得暫時許可,在“非正式”行業如制造業、工程和服務業中從業。
國家的政策越來越傾向于阻止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和他們的家人)享受城市公共教育資源和服務,包括上大學的機會。與此同時,嚴格限制流動的國家政策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就業有很大影響。城市求學的學生基本都面臨著如果在城市就業可否獲得戶口的問題。因此,美國以及歐盟出現的勞動力自由市場在中國尚未出現,這對于中國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經濟流動將產生重要影響。
2.難以滿足的入學需求與就業難問題
就像亞洲的多數國家一樣,中國文化對教育有著近乎宗教般的虔誠,認為教育是實現社會經濟流動和獲得社會地位的唯一路徑。人才分布在社會各階層這個概念早在公元600年的科舉考試制度中就已扎下歷史根基,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擔任政府機關高級文職,1898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同樣認可了這個概念。中國人對教育的虔誠在20世紀60年代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但是隨著江澤民宣布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對教育的狂熱又回來了(見表3)。
傳統文化和中央政府希望提升教育成就的愿望有助于解釋中國人對教育的無止境的渴望,不管身處何種社會背景,中國人都重視自己的教育成就,且希望確保孩子進入大學。而且,鑒于質量觀念和升入名牌大學的有限機會,也可以理解為什么越來越多中上階層家庭的孩子出國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

表3.中國大學史上的重大事件
將大學視為獲得高等學校學位和成功就業的優先路徑,這個觀念是有問題的,因為常常沒有足夠的令人滿意的就業機會去滿足大量競爭力(如果競爭力狹隘地局限于技能)通常不相上下的畢業生的要求。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Loran Brandt解釋,“過去人文學科的畢業生在外國公司或者上海、北京的中國金融機構找一份待遇豐厚的工作是不難的”[8]。然而現在,隨著中國快速合并現有的高校而且以理想的研究型大學模式建立新大學,已經沒有政策要發展其它或者更職業導向的大學。甚至在精英大學,學生正在降低他們的期望值,或滿足于考上公務員,資本主義承諾潛在財富增長和聲望提升的時代及理想雇主都已經不復存在了[9]。
同時,中國的經濟繼續維持在大約9%的年增長率。由于全球經濟衰退,去年的增長稍慢。中國官方統計的失業率現在是4.3%,但是有證據表明,包括城市在內,全國實際失業率要遠高于4.3%。大學畢業生也正面臨潛在的失業危機。在需求方面,中國經濟主體依然是對專業人才需求有限的、主要使用廉價勞動力的制造業。將近50%的GDP來自制造業和自然資源。與最可能吸納大學畢業生的專業性工作相關的服務業只貢獻了大約40%的GDP。雖然中央與地方政府及家庭都對知識經濟有明確的渴求與投資,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卻是,在這個政府限制人口流動的國家,經濟在地理上呈分散性。在供給方面,大學多集中在城市,全國各地的學生包括農村學生都涌向城市上學,然后希望在城市就業。幾乎沒有畢業生愿意回到農村或者西部地區。在那些地方,經濟發展更分散,水平更落后。但是,這些大學生大多都面臨戶口帶來的限制。國務院——中國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已經宣布學生回西部或中部就業,國家將會代償其全部學費,這一項目被稱為“服務西部代償學費”計劃。畢業生如參軍也會獲得補貼。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學生也成為爭奪國內工作機會的不可小覷的群體。這些人被戲稱為“海歸”,因為他們海外求學只為回到他們出生的海岸。對企業而言,海歸通常比國內對手更有吸引力,這進一步影響國內大學生的失業率。
一些畢業生正考慮在不那么發達的小城市就業。其他人升造或延遲就業,還有些人考慮改行,這在美國很常見。美國人認為在工商和公共事業部門工作需要寬廣的可轉換的技能,大學畢業證是通向這些技能的路徑。但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并非如此。新華社消息稱,2012年大學畢業生(本科和碩士)將達到680萬,與2011年相比增加20萬,而2011年,官方統計的高校畢業生失業率已經高達25%,非官方的統計結果比例更高。大約三分之一的大學生畢業后無法找到一份工作。同時,就業市場的構成情況是,外來工和農民工的總體就業率不高。
在2011年6月國務院為減少失業和滿足不發達省份人才需要而公布的舉措中,總理溫家寶提議城市消除畢業生的戶籍限制以減少失業。但是提高畢業生流動性不適用大部分熱門城市[10]。國務院也將鼓勵大學生在不發達的地區就業或者是自主創業。國家將為想要創辦小型公司的大學生提供國家貸款和優惠的稅務政策。
有助于解釋中國許多大學畢業生現在蕭條的就業前景的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他們自身的能力和其教育經歷的質量。中國教育部確定的目標是額外增加約140萬MBA學位。原因之一是中國不斷發展的工商業需要大量高級領導和管理人才。然而,這些極高的目標隱藏著對教育質量的擔憂。
3.關于質量的持續擔憂
在應該如何提高中國大學質量的爭論中,兩項議題處于討論前沿。最受關注的是學生學術投入的過程如何受中國文化影響,后者的特點是通過順從等級秩序,避免爭執和討論。強調自我修養、修身養性的儒家價值觀念能培養出勤奮、渴求社會和諧、避免沖突的人。這種價值觀與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頂尖大學推崇——即便不一定踐行——的蘇格拉底法不同。中國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總是將自己視為聽從者或附屬者。哪怕是中國頂尖大學的學生也是如此。在中國學者看來,他們是杰出的應試者,但比起西方同輩群體而言,缺乏創新和創造力。雖然課堂教學正在發生變化,但仍然主要是傳遞信息的單行道。
盡管有出乎意料的高失業率,但是國內外關注中國經濟的人,都會敏銳地發現,中國缺乏未來競爭力所必需的人才。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黃亞聲指出:“雖然中國大學并不缺少優秀人才的貯備和許多有利的機會,但是,他們粗制濫造大量高期待和低技能的人”。他注意到經理和企業家們正抱怨缺少具備合適技能和意向的人。中國培養的人記誦既成事實而不是發現新的事實,尋求現成的解決方案卻不喜歡探究新方案,寧可執行命令而不愿創新。換句話說,他們不為他們的雇主解決問題[9]。
第二個與之相關的議題是教師水平和對他們的期待。盡管存在一些地域差異,但總體而言中國大學只有很低比例的教師獲得博士或受過專門的研究和教學方法的訓練。這一點對于一個快速發展的高等教育系統來說不奇怪。直到1978年,中國才開始有博士生項目。最早一批大學之一的北京大學1981年只有三位博士生注冊入學[11]。在教育部主管的75所國立大學中,正教授大約占23%,而其他大學教授比例只占10%。
從歷史的角度看,由于毛澤東時期大學遭遇悲慘的損毀,學術在中國是一個相對年輕的職業。雖然高等教育國際準則逐漸得到強調,然而到目前為止,高等教育主要受國家背景影響,被不斷增加項目和擴大規模的需求所驅動。許多教師未掌握更好的引導學生投入學習的教學方法,由此導致的不利后果是強化死記硬背式教學方法,維持教學中強烈的等級秩序感。令人鼓舞的是,中央政府和學者們都越來越感覺到改善教學和研究質量的必要性了。可以說,盡管文化規范影響很大,還是可以鼓勵學生更獨立地思考。例如一些證據表明,用英語授課,加上一個更加探究式的課程和課堂氣氛,會對學生行為形成正面影響。在中國諾丁漢大學教書的Geoff Hall認為,“英語正在改變中國,這一過程需要中國未來的公民和領導人更進一步、更廣泛地了解”[12]。
中國如何才能解決這些教學和研究上的質量問題?中國似乎期待由政府政策自上而下地解決大部分問題。最初重點放在科研生產力上。政府指示已經在許多主要大學里形成高壓環境,政府要求大學產出可能影響國內國際排名的論文和科研成果,而且將之與薪水激勵掛鉤。強調大學增強問責和監督管理方案的風潮似乎可能快速提高在中國大學的國際排名中的位置。然而,在推進這些政策的過程中,政府可能并未充分估計政策對中國和其它國家大學及大學內部個體行為的影響。
也許為了改善個人在大學的地位,同時在滿足科研產出要求的壓力之下,中國學者的欺騙和剽竊行為此起彼伏。在2008年公開發表在《浙江大學學報科學版》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31%的論文存在“不合理”的剽竊。在計算機和生命科學研究領域中這一比例幾乎達到40%。科學網(一個在線科學社區)的編輯趙燕說:“中國文化中有不利于創新的弱點,例如懼怕批評,害怕表現個性或獨立思考。這些對科學文化的建設是很大的阻礙。”[13]
很清楚的是,中國政府為了研究和發展構筑的文化和資金系統投入已經在顯現成果。中國的研發費用預計在2015年上升至GDP的2.2%,遠遠超過2011年的1.7%。重點將聚集在新興產業,例如納米技術、新能源、干細胞研究以及建立新的研究實驗室和研究中心這類基礎的科學機構。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科研生產力的一個指標是科學和工程領域論文的數量和論文被期刊引用數。在世界被引論文中中國所占份額從2%上升至7.5%——令人驚嘆的增長。與此同時,美國和歐盟被引論文比率下降了(見表4)。這確實標志中國能力在逐漸增強。由于私企獲得的研發基金相對較少,這些科研成果其實主要集中在大學。

表4:部分國家和地區2000和2010年科學與工程學科論文、引文及國際性期刊引文占國際份額(百分比)
但是中國增長的被引論文大都發表在中國本土出版物上。2000~2010年間,中國被引論文中,發表在國際刊物上的論文比率,實際上從60.3%下降到50.8%。正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年度報告考察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科研產出時指出的,中國科學與工程論文產出的大量增長,大多發生在中國國內,這些論文的被引也主要是在國內。一個原因是,中國出版的在全球有影響的科技期刊在增多[14]。相應地,發表在這些期刊上的科技文章也有所增加。這就進一步表明中國科技的繁榮。科技期刊和專利都在不斷增長。同時,關于中國科研的質量和中國在全球研發競爭中的影響也有質疑。同一份國家科學基金委報告指出,其他亞洲八國或地區(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臺灣和)都未占得合理份額:中國的論文按第99個百分位計算比2010年預期少51%,日本比預期少39%。
“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無法發展”,溫家寶總理在2011年5月的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大會上如是說,“我們的未來依靠科學和技術的未來[16]”。但是,看不到院校自治、學術自由和建立在廣闊學科領域內全面優秀的綜合性大學三者之間的共生關系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好消息是,通常是在中央政府發動下,目前中國出現了廣泛討論這個問題的趨勢。然而講到質量,政府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生成問責機制而不是建立一個能培養高質量和杰出人才的“院校氛圍”。例如,在2010年政府公開2020年藍圖的四個月前,教育部成立了一個新的教育質量評估機構。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這些全國頂尖大學,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評估中心和上海教育評估院在內的超過200個教育機構都是其成員。這個質量評估機構被正式認證為非官方組織。它將致力于教學質量、課程設計評價,為2012年即將到來的全國性本科教育質量評估做好準備[17]。此前的2008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出于對生師比升高、研究生指導和課程發展問題的擔憂,宣布教育部直屬高校控制博士生招生數,年增長幅度不超過2%[18]。
三、院校自治:一個科層組織疲勞的案例
中國高等教育承擔著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經濟階層流動的指定職能,持續獲得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教師水平不斷上升,大學的科研生產力不斷增強,國際交流合作也不斷加強,這些因素以及其他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保持健康活力的因素,是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提高質量和生產力的保證。簡言之,中國頂尖大學不差錢,但是僅有錢是不夠的。其它兩個挑戰標明了中國大學尚未實現但至關重要的轉型:(1)形成內部生成和驅動的質量保障以及自我改進的院校文化;(2)充分的院校自治和師生學術自由。
許多頂尖大學,包括初批985大學都在進行本科教育改革,包括融合通識教育元素以及努力提高教學質量。南京大學提供了一個范例,為填補章駿校長所謂的“教學科研的縫隙”[19],它嚴肅地考慮課程改革的需要。但即使在最具創新性的大學,這些大學由理解大學上述問題的學術領導執掌,它們也持續面臨被教育部的政策和指令嚴重影響的困境。例如,教育部仍然指定大學生必修課程,包括那些為了讓學生保持對中國共產黨的絕對忠誠而開設的意識形態課程。在三年制專業中,有四門課程是這類必修課程,約占所有必修課學時的9.3%。比起2005年前要求的八門必修課程這已是進步。大約五年前,南京大學啟動面向全體學生的通識教育改革,要求所有學生修滿30學分的通識教育課程。然而,學生在諸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毛澤東思想導論”之類課程上還是要修14學分,這樣一來就限制了院校積極改革課程的自由[20]。
正如章駿校長在慶祝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言:“本科課程和人才培養模式深受計劃經濟影響。”[19]教育部針對教師評價也出臺特別條例,嘗試建立一個基于科研業績的教師晉升機制——動機沒什么不好,但是將科研生產力與論文數量(例如那些教育部指定的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聯系起來了。許多大學課程指定教材,嚴重影響教學內容——這種侵犯課程自由的做法在世界大部分大學是不容許發生的。在如何培養更有創造力和更有才能的人的問題上,章駿懷有民族憂患意識,他不無惋惜地認為當前系統對課程開發的約束和國家教師評價體制的管制“遏制了多樣化、個性及人性”[19]。
在某些情況下,教育部試圖改革中國大學還是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是這種中央指令的文化制約著由院校驅動的更有效的質量評估和質量改進活動。教育部對中等教育的政策也存在很大問題,中學生很早分流為適合上大學和不適合上大學的人群,并要決定他們未來的專業領域;死記硬背是通行的學習模式;學生所有精力投入到追求高分和入學率的目標上。這個過程不鼓勵學習興趣和大學階段期待的學術投入行為。
但是科層控制并不僅僅體現在對大學運行的控制上。對中國的大學來說,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多層權力中—這種權力有時候是形式上的,有時則是實質性的—最高層和大部分最有聲望的職位時常通過行政指令,主要根據當事人的政治表現而非個人才能來任命。這種嚴密的官僚控制是中國特色;其中有文化原因,不過在其它一些國家也存在機械式學習和官僚社會—歐洲就曾經這樣。然而,世界最卓越的大學都不采用這種模式;它浪費時間和金錢;降低或限制了教師的創業動機和創造能力,尤其對于年輕教師和人數不多的女教師影響更大。這種模式中通行的觀念是大部分教師都不是擁有共同責任的獨立個體,而是對領導唯命是從的工作人員。中國大學就像理當過時但變化緩慢的男權社會的殘余。
總之,教育部的影響和中國大學的官僚政治合起來,產生一種可以稱之為“科層疲憊”的現象。在匆忙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焦點是院校發展和合并這些問題,較少關注能促進院校持續改進和創新的院校管理實踐。一所現代、有競爭力、高質量的大學的管理,需要大學內部管理機構的努力和充分的大學自治,才可以實現內部驅動的改良。這要求扁平的組織結構,學術權力和權威更平均分配到教師手中。最終決定中國大學質量的是教師。大學也需要更強大的院校研究(IR)能力,以便大學運用適當數據和分析,為學術管理和決策提供信息和指導。充分的院校研究能力是通向基于證據的院校改進的必經之途。中國大學與其它習慣聽從教育部指令的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的大學一樣,正逐漸意識到院校研究的需求。
四、學術自由和世界一流大學
最后,能持續制約教師質量和他們的創新能力及其專業發展的、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充分的學術自主或自由。“科層疲憊”制約教師學術自治,但是在這里我更關注公民社會的基本自由。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真正的好大學都有濃厚的學術自由傳統,允許師生公開評論和批評社會以及國家領導,并為學術追求和課程教學提供更廣闊的自由。
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大學是否只是回應它們所處的社會,必須遵守社會的文化、政治基準?還是作為社會的領袖,是一個產生創新想法和自由論爭的場所?一流大學的確是社會的引領者——科學家、工程師、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科教師不僅參與本領域而且參與整個社會的倫理問題及其影響的討論。
作為上述模式的拓展,一流大學是由一個學者和學生組成的更大社團,這些師生討論現在與未來的重大問題。那些只將目光聚集在某個知識領域如工程學,或一般性的科學領域的大學,其目標不夠開闊,難當世界領袖之名。查強也提到:“中國的長期繁榮,將取決于一系列進步,包括進一步開放經濟,更開放,更民主,進一步提升文化的自由度和社會與地區間的公平等。”[7]大學能夠,也應該成為社會進程的引領者。
民族國家在匆忙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同時,試圖建立一批得到國際認可的大學,在這個過程中,學術自由的作用雖然是基礎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這是高等教育全球語境下的一個事實——不僅限于中國。同樣地,在政治環境不穩定或那些公然歧視女性或特定種族的社會,大學也面臨很大局限。這樣的大學教育不能培養具有廣闊知識的學生,不能產生擁有國際視野的教師。這些院校只能是追隨者,而非擁有強大科研生產力的一流大學。
當然,隨著阿拉伯之春運動的發生,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面臨更緊張狀態,政府施加更大力量來責難和控制言論。將行政和學術安排混合起來——例如,如前文所述,學術領導幾乎都是由政府任命且是中共黨員——使得學者和學生獨立思考的興趣和努力狀況進一步復雜化。
以下的三個例子有助于闡述這種緊張,同時也向國家領導揭示了一個在中國學者看來隱蔽、發展緩慢且情形令人沮喪,但日漸明顯的事實,即若不進一步擴大自由度,中國將無法全面地實現其成為全球首領的目標。
1.一出戲劇與一場計劃的對話
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一同位居中國首都,在創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的國家目標中是先驅,為國家培養了許多政治和知識精英。因此,當由于政府難以避免的疏忽導致紐約制片的《絕密:五角大樓文件之戰》于2011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學上演時,它被視為充滿希望的指標——標志著中國有意愿(這種意愿盡管有限但是有意義)質疑自由言論的社會價值(這部劇戲劇化地再現了1971年華盛頓郵報與美國政府之間針對是否將美國卷入越戰悲劇的多份文件公之于眾的問題產生的對峙,1991年首次在美上演)。正如劇中一個人物所說:“此事與國家安全和間諜組織無關。它關乎政治,控制和困境。他們不想要我們暴露他們的虛偽和謊言。”[21]
北大教師計劃在演出結束之后舉行一次討論,但就在演出開場前,政府官員下達了一份文件,警告組織者:如果展開討論可能發生難以預見的后果而將影響擴大到劇場之外,因此要有計劃地組織討論。最終,組織者取消了演出后的討論。此劇在北大用英語演出,觀眾大多是師生,之前在上海和廣東早已上演。根據美國時報報道:“觀眾幾乎都是中國年輕人,許多人通過微博了解到演出信息。微博已經改變了中國人的交流方式,包括通過微博表達對政府瀆職行為的不滿[22]。就像最近對薄熙來案件的熱議,使得微博的評論功能在幾天內崩潰了。
2.一份學術期刊
南京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已經有25年聯合培養法學、國際關系和金融專業研究生的歷史。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越來越多美國大學(如杜克大學和紐約大學)采用的一種模式,但是,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學術話語規范會給國家之間的這類交流帶來什么限制呢?
當在霍普金斯-南大就讀的一位名叫布蘭登·斯圖亞特的美國研究生,創辦了一份學術期刊發表該中心中美學生的研究成果時,他不完全了解學術自由限于課堂的規則。學校管理人員禁止刊物在校外流通,一名學生還迫于壓力撤回了一篇關于中國抗議活動的文章,75本刊物壓存在宿舍的箱子里一年。
“對斯圖亞特所辦刊物的封鎖顯示了美國大學在中國對學術自由所作妥協”,商業周刊的丹尼爾·戈登和奧利薇·斯特雷說:“盡管學者和學生可以在霍普金斯—南大校園公開地討論像西藏獨立運動或1989年學潮這類敏感主題,但他們不能在公共場合討論,甚至校園內也僅限在課堂上討論,休息室播放紀錄片這類美國校園里典型的學生活動在霍普金斯-南大校園里是沒有的。”[23]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以及中國問題研究專家June Teufel Dreyen教授稱:“這些新生拿著中國數百萬的補助金,他們可能危害作為美國高等教育特征的知識共享。”[23]
2002年何清漣在文章中寫到:
中國從未享有真正的學術自由,甚至實行經濟改革的近十年也如此。大部分限制自由言論的方法西方學者聞所未聞。然而,這些限制言論自由的方法,在過去20年中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和人民質疑政府的意愿不斷上升而有所改變[20][24]。
3.人才引進
中國政府和中國頂尖大學長時期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人才外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才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然后在國外開始他們有創造力的學術生涯這種模式。為了努力提升國內大學質量,提高科研水平,鼓勵加強博士項目和研究中心的發展和管理,現在已經有一個重大項目吸引學術人才回國。證據顯示,這一促進留學人員回國的舉措十分有效。許多知名科學家已經回國,他們被委以重任,并獲得巨大的物質支持,包括最新的實驗室設備;許多歸國專家也表示希望幫助中國提高研究質量,并培育一個創新環境。
范桁是回國的學者之一,他是一位量子計算專家,2005年離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回到中國科學院。他說:“十年前我們希望出國學習經驗,現在我們想回國做我們自己的研究。”一項政府研究指出,已經有3100多名學者回國獲得終身教職,配備研究實驗室以及一般來說人均15萬美金的一次性的津貼。范說:“趨勢慢慢就徹底扭轉了,一些研究者想要回國,但是卻沒有機會,畢竟位置是有限的。”[16]
但是也有些回國的科學家感受到自由探究上的持續限制、官僚體制及很難擺脫的政策控制。引進學者回國這項計劃的凈成果——那些回國并最終呆下來的人才——仍然只是半成品。一項研究表明,對于那些已經習慣國外的廣泛自由和強大的精英主導的晉升系統的學者而言,回國的吸引力正在降低。在20世紀80年代期間,25.9%的中國博士生完成學業后立即回國,但在2000年,這一比例下降到7.4%。印度的數據也相當低:1980年13.1%的博士生回國,而2000年就只有10.3%了[25]。
還有一些其它因素限制學術研究的范圍和預期影響力,包括:仍在演變中的知識產權法;初現端倪的民間風險資本;以及相對較低的技術轉讓率,后者部分由于中國經濟大都以低技術含量的制造業為主而受到限制。可以證明的是,中國大學(甚至包括頂尖大學)的學術環境是妨礙大學形成追求研究、教學、公共服務領域的卓越的強勢文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五、結語:一個漸進的未來?
過去十年內,媒體已經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發展嘖嘖稱奇。2010年一項預測表明2030年中國將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體,2040年中國經濟產出可能會達至123萬億美元,是2000年世界經濟產出總量的3倍多[26]。中國的GDP在過去30年都以平均每年約10%的速度增長,另一項估計表明約5億中國人已經脫離貧困[27]。
然而也有跡象表明,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率難以持續。實際上,受全球經濟倒退和廉價勞動力競爭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降低。這也可能表明中國在創造一個更公平和更開放的社會方面缺乏進步。世界銀行近期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必須實現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以強化“市場經濟的基礎”。報告指出“構建和諧社會也要求更公平的增長,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安定”[28]。這樣的經濟改革要求受教育者比率的增加以及大學的質量和生產力的提高。對于一些批評中國過分強調維穩的評論者而言,和諧社會也要求充分的公民自由權。
在大多數追求社會經濟階層流動和經濟競爭力的國家,大學的一個獨特使命是為社會提供一個創新和反思、寬容和異見的場所。然而無論在美國和其它地區,大學的充分成熟都經歷了時間的洗禮,此進程受大學所存在的社會的影響,且需要長期穩定的財政和政治支持。可以將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令人驚嘆的快速變革,以及適當控制、管理和自治水平等議題,都視為系統發展曲線的一部分。而且,高等教育系統的成熟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共同的興趣所在。
“考慮到中國大學地位不斷上升,它們已經逐漸成為對現代國家及其政治權力的批評的合法來源”,査強說,“這種改變將會使大學在爭取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權利時獲得前所未有的優勢,而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反過來也應該成為整個社會開放的催化劑”[7]。這是個充滿希望的觀點。換句話說,中國的大學如同金礦里的金絲雀①過去在煤礦里用鳥(金絲雀)來探測危險氣體積聚情況。如有危險氣體存在,呼吸速率本來就比較快的金絲雀,就會搶在呼吸較慢的礦工之前昏迷不醒,因此,礦工們察覺到這種情景后,可立即撤出礦井,避免傷亡事故的發生。“礦山中的金絲雀”喻義起警示作用的東西。——譯者注——是衡量國家走向更為開放,更具生產力的社會的發展進程之基準。許多的大學領導和教師都明白中央政府過多的控制是一種妨礙;從本土經驗和對其它卓越大學的了解中,他們認識到“科層疲憊”問題,認識到發展自我提升的內部文化的需要,認識到學術自治的重要作用。這些都是建設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學必須是社會變革的代理人。
中國大學,尤其是985院校,在未來的10年將成為領袖還是追隨者?只要條件允許,中國大學可以逐漸走向成熟,取得更大成就,不斷提升其地位,并且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揮更重要影響。
[1]2020Blueprint.[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862/201010/109029.html.
[2]Li,Lee,John Whalley,Shunming Zhang,Xiliang Zhao.2008.“The Highe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Paper No.13849,March.[EB/OL]http://www.nber.org/papers/w13849.
[3]Jiang,Kai.2010.“Building a Stro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hina’s Ambition.”Inside Higher Education,November..[EB/OL]http://www.insidehighered.com/blogs/the_world_view/building_a_strong_higher_education_system_china_s_ambition#ixzz1fVQqA9IP.
[4]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0.A Blueprint for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June30.[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862/201010/109029.html.
[5]Peoples Daily Online.2010.“China Lacks Global Top-ranking Universities,Says Academic.”April 16.[EB/OL]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82/90873/6953072.html.
[6]Zhao Litao.2011.“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China’s Plan fo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2010-2020).”EAI Background Brief No.616.East Asian Institut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April 5.[EB/OL]http://www.eai.nus.edu.sg/BB616.pdf.
[7]Zha,Qiang.2011.“What Kind of Higher-Education System Does China Need?”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12..[EB/OL]http://chronicle.com/blogs/worldwise/what-kind-ofhigher-educationsystem-does-china-need/28664.
[8]Brandt,Loren.2010.“College Educations,Needed and Desired.”Room for Debate Blog.New York Times,March7.[EB/OL]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3/07/educated-andfearing-the-future-in-china/#loren.
[9]Huang,Yasheng.2010.”A Terrible Education System.” Room for Debate Blog.New York Times,March7 .[EB/OL]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3/07/educated-andfearing-the-future-inchina/#huanga.
[10]Sharma,Yojana.2011.“China: Guidelines to Ease Graduate Unemployment.” University World News, June 12.
[11]Ma, Wenhua.2009.“An Upward Trajectory:Doctoral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In John Aubrey Douglass et al.,Globalization’s Muse: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a Changing World.Berkeley:Berkeley Public Policy Press.
[12]Hall,Geoff.2012.“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English.”University World News,February26.[EB/OL]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2022310450891&query=china.
[13]Lim,Louisa.2011a.“China Aims to Renew Status as Scientific Superpower.”National Public Radio,August1.[EB/OL]http://www.npr.org/2011/08/01/138837512/china-aims-to-renewstatusas-scientific-superpower.
[14]Sawahei,Wagdy.2012.“US Tops List of International Patent-Filing Universities.”University World News,March11.[EB/OL]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20309132555536&query=china.
[15]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2.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Washington, D.C.
[16]Lim,Louisa.2011b.“Plagiarism Plague Hinders China’s Scientific Ambition,”National Public Radio,August3.[EB/OL]http://www.npr.org/2011/08/03/138937778/plagiarism-plaguehinders-chinasscientific-ambition.
[17]Xinhua.2010.“National Network Launched to Evaluate Quality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China Weekly,November1.[EB/OL] [18]“China to Limit Enrollment in Doctoral Programs.”2008.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May 1.[EB/OL]http://chronicle.com/article/China-to-Limit-Enrollments-in/40902/ [19]Zhang,Jun.2012.Remarks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ndergraduate Creative Education in the Globalized Era,held on the occas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s 1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Nanjing University, May 20. [20]Lai,Manhong,and Leslie Lo.2011.“Struggling to Balance Various Stakeholders’Perceptions: The Working Life of Ideo-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333-349. [21]Isherwood,Charles.2010.“Fighting a War of Words about a Lot of Words About a War.”New YorkTimes,March10..[EB/OL]http://topics.nytimes.com/top/reference/timestopics/organizations/n/new_york_theater_workshop/index.html?inline=nyt-org. [22]Jacobs,Andrew.2011.“Chinese Allow Play on Pentagon Papers,but Not a Talk About It.”New York Times,December2.[EB/OL]http://www.nytimes.com/2011/12/03/theater/play-onpentagon-papers-goes-on-inbeijing-but-not-atalk.html?pagewanted=all. [23]Staley,Oliver,and Daniel Golden.2011.“China Halts U.S.Academic Freedom at Classroom Door for Colleges.”Bloomberg News,November29..[EB/OL]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1-11-29/china-halts-u-s-academic-freedom-at-classroom-door-for-colleges.html. [24]He,Qinglian.2002.“Academic Freedom in China: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in China Have Prompted More Sophistic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rol of Intellectuals.”Academe, May-June..[EB/OL]http:// www.aaup.org/AAUP/pubsres/academe/2002/MJ/Feat/Qing.htm. [25]Altbach,Philip.2012.“The Complexities of 21st Century Brain‘Exchange’”University World News,February26.[EB/OL]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20223155324935. [26]Foegel,Robert,2010.“$123,000,000,000,000:China’s Estimated Economy by the Year 2040.Be Warned.”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EB/OL]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1/04/123000000000000. [27]Ravallion,M.,and Chen,S.2007.“China’s(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2:1-42..[EB/OL]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PGLP/Resources/ShaohuaPaper.pdf. [28]World Bank.2012.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