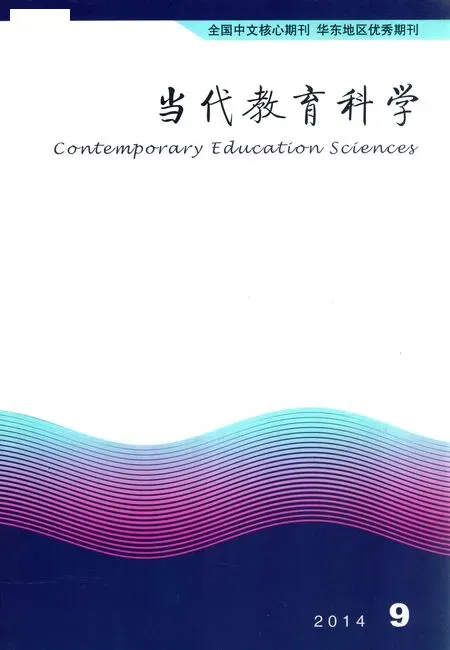教學研究價值取向的轉移:從“一般”到“特殊”
● 馬鵬云
教學論在學科發展過程中不斷走向成熟,這與研究者共同體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教學論的不同發展階段,研究者為著一定的信念而努力,并因此組成一定的研究共同體,形成一定的研究文化。在價值觀念層面,思維方式層面及行為規范層面,研究者有著基本一致的表現。縱觀教學研究的發展歷程,研究者所追求的價值取向呈現出從“一般”到“特殊”的轉向。在20世紀50、60年代以前,研究者主要探究普適性的教學本質和規律,努力構建宏大的教學理論體系。50、60年代以后,隨著生存論哲學、現象學、情境教學等思潮的興起,研究者的研究重心轉向尋求情景化的教學意義,并由此帶來了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的變革。探討研究者價值取向轉移的特點,有利于加強教學論學科自身的建設,提高理論研究的自覺性。
一、價值觀念:從揭示教學的普適性規律到尋求教學的情境化意義
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總是受一定價值觀念的指引,為了一定的研究任務而努力。教學論在發展之初,需要從其他學科尋求理論基礎,哲學作為一切學科的母學科,理所當然的成為教學研究的尋求方向。受當時哲學主客二分的客觀主義認識論影響,研究者深信在教學中存在著普適性的本質和規律,它能指導一切教學活動。這種堅定的信念指引著他們為此不懈努力。回顧20世紀50、60年代以前的國內外教育思想,大多是關于教學本質、教學規律、教學原則等方面的闡述。國外從夸美紐斯在《大教學論》中論述的關于教學活動的直觀性原則、鞏固性原則、量力性原則[1],到赫爾巴特提出的“明了—聯合—系統—方法”的教學形式階段理論,再到前蘇聯贊科夫的五條發展性教學原則,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等,均被認為是對教學本質和規律的把握,并被奉為經典廣為流傳。國內學者對教學本質和規律的考究也有著同樣的偏好。如王策三先生在《教學論稿》一書中強調要堅持把教學規律作為研究的任務[2],李秉德先生主編的《教學論》注重對教學過程的本質、教學原則等的專門論述[3]等。仔細考察不難發現,這些所謂的規律和原則大多是從教學經驗中總結得出,或者是從哲學、心理學等學科中通過理論演繹得出,究竟是否是關于教學的真正認識,并沒有切實可靠的證據。同時,一味追求教學認識的確定性和絕對性,容易導致對現實教學活動的遮蔽和遺忘,使教學論研究陷入純粹形而上的思辨之中[4]。
由于本質主義的教學研究帶來的困境,以及生存論哲學、現象學及情境教學興起的影響,教學研究者的研究旨趣發生了向“領域特殊”的轉移。生存論哲學認為,“生活世界不是符號化的抽象的、純粹觀念的世界,而是一個日常的、可感的、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經驗的實在世界”[5],存在先于本質,從存在入手揭示背后的意義。教學論研究要關注教學存在,在學生的真實生活情境中尋求教學的意義。現象學教育學派同樣反對抽象的教育學,其代表人物范梅南曾指出,“教育學不能從抽象的理論論文或分析系統中去尋找,而應該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尋找,……教育學使得一個際遇、一個關系、一個情境或活動變得有教育學意義”[6]。20世紀80年代,心理學領域的情境認知理論取代信息加工理論成為研究的熱點,情境認知理論反對抽象的、空洞的知識,認為知識只有在它產生和應用的活動或情境中去解釋才有意義。學習者必須置身于知識所在的情境或活動中不斷學習和探索,才能掌握知識的真正意義。這種觀念在教學中的應用就是情境教學,情境教學強調在教學中創設與現實相似的真實問題情境,使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理解知識和建構意義。通過情境教學,“將人文學科的字詞句篇、科學學科的定理公式融入具體生動的情境中,融知識性、育人性、發展性于一體”[7]。研究者轉向關注真實的教學生活,以現象學,社會學等多元化的視角對其解釋,揭示教學事件背后的意義和價值,使得教學理論更加貼近教學實踐,教育研究也變得生動活潑。
二、思維方式:從主客二分的對象性思維到主客合一的關系性思維
研究的價值取向深受思維方式的影響。持“一般”價值取向的研究者將研究旨趣定位于把握教學的本質和規律,內蘊的實則是主客二分的對象性思維方式。而持“特殊”研究價值取向的研究者偏向尋求教學的情境化意義,則是主客合一的關系性思維在起作用。
對象性思維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傳統思維方式,滲透在教學研究中,主要表現在對教學規律、教學現象、教學問題等的追問,關注教學“應該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問題,注重的是教學目的和結果的實現,忽視了教學的內容和手段,研究呈現目的與手段分離,內容與形式分離的狀況[8]。如16世紀的形式訓練說,這種觀點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打開心智,使官能得到發展。學校設置課程,并不是為了這些學科本身的價值,而在于這些學科對心智的訓練價值。又如,研究者在進行有效教學研究時,并不關心是在數學、語文或者物理等哪門學科中進行,亦不考慮作為研究對象的教師或學生有著怎樣的個性差異,這些因素的影響作用被排除在研究目的之外,成為研究目的的背景或常量。
生存論哲學批判主客相分離的認識方式,認為它“見物不見人”,忽略了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生存論哲學倡導主客合一的認識原則,其關照下的思維方式是關系性思維。所謂關系性思維,是指不再把“存在者”即任何客觀的事物當作沒有自身結構、孤立的、抽象的實體,而是從內外部結構、聯系、系統等關系狀態來把握它的存在,從運動、相互作用、聯系和關系即“存在方式”的意義上來理解現實世界,從而進一步把握豐富、深刻、動態的“存在”[10]。關系性思維支配下的教學研究呈現目的和手段,內容和形式相互作用的狀況。針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教學研究大多集中在一般教學法方面,卻不關注學科內容的現象,美國學者舒爾曼呼吁對學科內容和結構的理解與重視,并提出“學科教學知識”的概念[11]。又如,20世紀70、80年代,認知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通過一系列以專家新手為典型的實驗發現,具體領域的學科知識結構對思維能力的培養起著重要作用[12]。此后,研究者逐步開始重視具體學科知識結構的作用,并對之加強了研究。
三、行為規范:從重視科學性的實驗研究到重視解釋性的自然研究
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思維方式決定了研究者的行為規范,這主要表現在研究者進行研究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持“領域一般”取向的研究者堅信教學規律是可以通過實驗加以證實的,教育學要像心理學,數學等自然科學那樣達到科學化水平,必須排除情感,價值觀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在對象性思維方式支配下,研究者將教學視為外在于研究者的客觀存在,為了追求教育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勢必要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觀因素的影響,因而多采用調查、觀察、實驗等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例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實驗教育學運動,批判傳統教育學以邏輯推理和抽象思辨為主,缺乏以實驗方法所作的嚴密論證,阻礙了教育科學的發展。他們主張采用觀察、調查、測量及統計等方法進行研究,努力使教育學提升科學化水平[13]。采用實驗的研究范式無疑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學化水平,但研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時總是持有一定的價值立場,實驗結果難以保證完全的客觀、公正。同時,教學作為使學生身心得以自由發展的活動,旨在激發學生的理想,塑造學生的品性,這就決定了它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追求絕對的科學性。教學作為一種在特定時空背景下進行的活動,有著動態性和差異性,通過某一實驗情境得出的結論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簡單復制到其他教學情境中,杜郎口中學的成功做法難以被有效借鑒即是明證,這同時也是教學理論被教學實踐所疏遠和責難的重要原因。
持“領域特殊”取向的研究者采用關系性思維看待教學研究,為把握教學現象內外部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好地解釋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的教育意義,研究者多采用教育敘事研究、田野考察法、行動研究等質的研究方法。以教育敘事研究為例,“以教育生活世界為出發點,把教育經驗組織成有意義的事件,通過對事件的描述分析,挖掘內隱于教育事件背后的教育理想、教育信念和教育理論,揭示教育的本質和意義”[14]。這種研究方法使得研究者更多地關注日常教育生活中的事件和個人,教育研究因此變得有血有肉。采用自然主義的研究范式,回歸教育生活世界,有利于研究者從整體性、動態性視角把握豐富多彩的教育現象,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揭示隱含在其后的教育價值和意義。
四、結語:從對立、分化走向互補、整合
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教育科學的繁榮,研究者的價值取向呈現從“一般”到“特殊”的轉向,是教學論這門學科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表現,有著不可否認的深遠意義,這種轉向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肯定這種轉向的同時,需要研究者冷靜地反思這種轉向所帶來的影響。在強調“領域特殊”的同時,“領域一般”研究取向是否就缺乏存在的必要性了呢?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是不可取的,雖然如前文所述,“領域一般”取向有著諸多的弊端,但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教學論作為一門學科,明晰自身的研究對象和任務,構建規范的學科理論體系和基本框架,是學科走向完善的必要條件。認清“教學到底是什么”,“教學研究的目的何在”等問題,是教學論展開進一步研究的立足點。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我們不能因為教學的多元認識而輕易否定教學是什么的追問對教學論研究和教學實踐的意義;恰恰相反,教學是什么的追問正是教學論研究得以不斷深化的重要動力,也是賦予教學實踐以理性的基本前提”[4]。放棄教學本質和規律的研究,容易導致教學研究領域缺乏基本的研究規范,繼而引發實踐中的混亂。教學研究不能僅僅是關于教學本質和規律的研究,但絕不能沒有教學本質和規律的研究。總之,保持“領域一般”和“領域特殊”之間的張力,是教學研究的應有追求。
[1][捷]夸美紐斯.傅任敢譯.大教學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90-120.
[2]王策三.教學論稿(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52.
[3]李秉德.教學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1.
[4]徐繼存,趙昌本.教學本質追問的困惑與質疑[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11).
[5]劉小新.當代哲學生存論探析[J].哲學研究,2006,(3).
[6][加]馬克斯·范梅南.李樹英譯.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43.
[7]田慧生.情境教學——情境教育的時代特征與意義[J].課程·教材·教法,1999,(7).
[8]陸明玉.從對象性思維到反思性思維教學論研究思維方式的新走向[D].天津師范大學,2009,29.
[9]陳琦,劉儒德.當代教育心理學(第2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346-348.
[10]李德順.價值論——一種主體性的研究(第2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4.
[11]徐學福.理論失位與實踐轉向——20世紀美國課程與教學研究的重心轉移[J].全球教育展望,2011(5).
[12]Glaser,R. (1984).Education and thinking:The role of knowledge.American Psychologist,39,93-104.
[13]吳式穎.外國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65-466.
[14]徐勤玲.教育敘事研究的理性反思[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