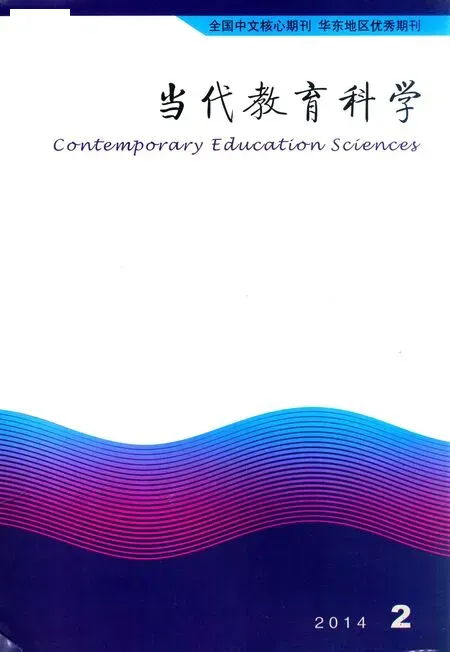在模糊與精確之間
——論教師的算度可能與現實困境
●宗錦蓮
在模糊與精確之間
——論教師的算度可能與現實困境
●宗錦蓮
算度作為操控教師的現代技術,其本質屬性在于“精確”,而在算度的背后卻充滿著各種飄忽不定的模糊性,如教師難以精準的客觀基礎以及算度者難以一致的主觀感受。即便如此,掌權者卻仍然實現了算度從模糊導向精確的可能,并使其葆有著不容質疑的精確面貌。究其原因,簡單性思維與恐慌的社會氛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教師也因此陷入價值異化與無奈屈從的現實困境之中。
教師;算度;模糊;精確
算度是指通過一種精細化的手段、精確化的形式對人的行動及價值進行有關分數式的測量與評估,從而將人分門別類。在當今社會,“人無往不在算度之中”,而對于被科層體制完全鉗制著的教師們來說,算度早已以一種無限理解與全面審查的姿態出現在他們的日常教育教學生活中,操控著他們的言行,鞭笞著他們的馴順與服從。
算度的核心機理與本質屬性在于“精確”,毫無節制地制造、夸大甚至神化精確是掌權者包裝算度最樂此不疲的事。但算度真如其所標榜的那樣,無時無刻都與精確相伴相隨嗎?算度真的徹底地與“模糊”絕緣嗎?掌權者通過怎樣的機制實現了算度在“模糊”的基礎上對“精確”的達成,從而保證了算度自身的正當性?而在這種模糊與精確之間,教師又在經歷著怎樣的生存困境與現實無奈呢?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追問的時候了。
一、算度內在的模糊必然:教師與掌權者
算度的內部生產,如內容的選擇、分值的賦予、方法的設計以及結果的確定,常常被當作一種合法化前提被人們所忽視。原因很簡單,一是這些“背后的故事”于己而言并無太多關系,二是即便窺見了不能說的秘密,一己之力也難有作為。何況人人皆在算度之中,與其做無謂的抗爭,不如將精力轉向更具實際意義的算度競爭中去。普遍的不關注給了掌權者游刃有余的操作空間,難以捉摸的精確性被棄置一邊,無處不在的模糊性被吸納為算度生產的救命稻草。在算度精確的外在表象下,模糊成為一種必然內在地支配著算度的作為。
(一)客觀性實存
現實世界從來就是模糊多于精確,虛幻多于真實的。模糊現象普遍而廣泛,精確只是模糊的特例。一切對于精確的強求都是徒勞,有如愛因斯坦畢其一生企圖構造出精確和諧的宇宙統一模型終以失敗收場一樣。即便如此,掌權者仍舊期望經由算度創造一個精確審判的世界,將教師進行精確化地處理,再通過教師精確化學生,最終實現對整個世界的精確化統治。而所有這些企圖都無法回避被算度者(教師以及學生)具有模糊性的確實性存在。
教師的模糊,單純從其客觀具有的角度來看至少涉及三大系統:一是連教師自己都捉摸不透的內部系統,統攝了情感、態度、意志、性格、品質、能力與旨趣等機制的錯綜關聯。這些沉潛于教師內部的存在,既不具備可一目了然的可視性特征,也無法通過儀器設備精準地探尋其可能的狀態。人們只有依靠體悟、感覺或是猜測才能大致對其進行描述,而這畢竟不是事實本身,尤其當教師出于身份考量掩飾起自己的不完美而扮演“圣人”與“楷模”的角色時,試圖用刻意改善過的外部表象為依據去揣摩教師的真實動機只能是自欺歁人。在這一層面上,教師已然是難解的謎,模糊感始終包裹著教師,難以名狀,亦難辨真假。
二是與教師普遍關聯的外部系統。教師不是孤立存在的職業類型,其一切活動都建立在與社會其他群體千絲萬縷的聯系之中,其他職業的些許變化都可能引發教師自我認知的波動,也可能改變其價值判斷。孤立地審視教師是難以周全的,而當社會各方的復雜因素摻雜進來,教師的越發模糊便成了一種必然。同時,教師又不只是教師,還擔負著多重的社會角色,極有可能既是父母,又是子女;既是特約撰稿人,又是公益組織者,等等。為了避免混雜不清,試圖將教師從其共在性的角色中剝離出來只是徒勞。因為這些類別不
一、體驗各異的角色類型早已不約而同地投射到教師角色中,影響著教師的角色理解及扮演方式。各種角色相互交織、彼此作用所生成的慣習已經深入到主體內部,很難分清是否為教師角色所獨有。
三是教師不斷變化著的自更新系統。教師不是靜止待量的物,更不會為了迎合某種階段性的確鑿命名而一成不變,他們時刻都在發生著程度不一的變化。不管是觀念的漸進或突變、行為的修正與改善,或是關系網絡的收縮與重構,都是構成教師的重要部分。變化意味著,即便立即能夠給出一個精確判斷,但也很有可能即刻便被推翻,成為與事實不符的炮灰。在變幻的時空里,教師飄忽不定,我們捕捉不到他們確切的模樣,更別說將其精準地定位在事先繪制好的座標圖中了。
當然,作為另一個算度對象——學生,就其尚處于未完成狀態這一點來說,其模糊性絲毫不會遜色于教師(在此不作展開)。被算度者本身的界限不清與性狀不明,已經足以讓算度的精確化裁決變成不可能的任務,而掌權者非但沒有懼怕模糊的客觀性實存,反倒不遺余力地將自己的主觀模糊源源不斷地輸入到算度生產的過程之中,個中緣由發人深省。
(二)主觀性嵌入
審美場的模糊性來源于三個方面:藝術品本身的模糊性;欣賞者的模糊感受;審美場的介質:時代與環境的變動。[1]算度場的模糊性與之大致相似,其中對應著“欣賞者”的“算度者”,其主觀感受對算度事先決策、過程操作以及結果運用的直接參與是導致算度模糊的核心根源,不可視而不見。
教師模糊的客觀性實存同時構成了掌權者在認知上的模糊不清。原本就縹緲不定的對象無論如何轉化,都無法在認識者腦中投射出澄清的圖象。真實又完整的教師被隱藏了起來,掌權者對他們的認知永遠都只能是有限的——或是某種狹窄的局部,或是被夸大了的特性,或是被層層包裹后的表象。當然,教師的模糊只是一個方面,掌權者對教師形象的主觀加工更加劇了這種復雜性。掌權者所站的立場、所處的境遇與所有的經歷與教師大相徑庭,試圖以局外人的經驗達成對教師的理解看起來并沒有那么容易,甚至掌權者的主觀建構極有可能變成對教師在一定程度上的臆斷與歪曲。教師本身的不確定與掌權者理解的局限相互交織,構成了算度的雙重模糊。
掌權者并非沒有意識到模糊性的普遍存在,但他們掌控全局的野心遠大于對現實的敬畏,模糊的客觀現實未能阻擋其執意算度的步伐。于是,一場改造模糊性的革命開始了。這其中,掌權者的主觀性嵌入居功至偉。算度背后,到處都泛濫著掌權者的主觀決策,彌漫著其個人感受與主觀色彩,他們試圖對教師所進行的從模糊到精確的轉變并不是基于現實的澄清,而是不斷放任主觀性干預的結果。
一方面,掌權者過份地依賴并信任主觀經驗,即便這些經驗對現實的反映從未經歷過準確性的論證,即便它們遠遠地滯后或相悖于現實的新變化,但卻依舊能夠成為評判與遴選教師的準繩。對于掌權者而言,“教師是什么”與“教師應該怎么樣”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現實的教師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經驗體認,甚至滿足其對教師的主觀想象。而經由經驗與想象所形成觀念可能是掌權者的靈光一閃,可能是難以自拔的偏執,也可能是大差不差、馬馬虎虎。不管是哪一種,不僅與算度所標榜的“精確”相去甚遠,而且還伴隨著難以預料的隨意與巧合。這也還是一種模糊——一種沉潛于算度機制內部,深刻地影響著算度運作的模糊。
另一方面,掌權者又十分強調自我欲求的彰顯,體現于對偏好的傾向設置上。掌權者會根據個人喜好制定算度標準,放大所偏好的品質、個性、技能,甚至某種事物的價值,引發教師的集體性崇拜與效仿。這種喜好不以是否凸顯核心價值為衡量標準,卻往往將焦點集中在掌權者自己極為擅長的內容之上。這意味著,當主觀偏好作為算度著重考量的內容被不斷抬捧時,掌權者的權威與地位也將隨之升高,尤其對利于統治的考量成為了算度的主基調。算度在本質上是掌權者實施控制的手段,只要某項技術能夠加深教師的服從,都將被取而用之。不管是出于情緒上的喜愛,還是功利性的目的,基于偏好的算度都是主觀判斷大于客觀依據,主觀權重多于客觀概率,這更是一種模糊——一種深藏著掌權者意志與價值取向的,看似擇善而從、化繁為簡,實則別有用心的模糊。
算度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是在模糊化邏輯的支配下進行的,不管掌權者關于算度“精確性”的吹噓如何地竭盡所能,我們都必須清醒地認識這一點。
二、算度外在的精確圖景:數字、因果與總體
依照常識,教師的模糊經由掌權者的模糊化處理所輸出的應該是更為復雜多變的模糊,但恰恰相反,模糊經過各種騰挪翻轉后消失了,內蘊著模糊本質的“精確”魔幻般地生成了。掌權者將教師編碼為清晰有序的確鑿模樣,仿佛每一個部分拆卸下來都可以逐一稱量,仿佛被稱量后的部分之和便是完整的教師。教師既無能為力于精確化的強加,又不自覺地將這種“精確化”視作職業承擔的必須,即便忍辱負重,也要佯裝順從地走下去。
(一)數字威權
近代科學將自然中的一切非神秘化的、不能加以數量化的東西統統排除掉,所剩下的真實的東西是具有廣延、形狀、慣性等數量特征的物質性實體世界,而氣味、顏色、聲音等具有感性特征的東西則被看作是不真實的。[2]而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對數字化表達的熱愛也不遜色。數字代表的是一種排他的確定性,數字的篤定讓人們不用糾結于模棱兩可的似是而非,并因此感到安全。算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尋找到了合法化的借口,堂而皇之地將豐富的人改造成確鑿無誤的數字符號,在這其中,不僅算度者享受著“一切皆在掌握”的安全感,連被算度者也因為“生存有望”而倍感寬慰。
不管算度出爐前的狀況如何地混濁,當算度作為權威性的篩選與分類工具出現在教師面前時,它已經完成了滿裹著數字的精確化轉身。無論是在算度的內容設置、操作方式,還是結果轉化中,數字都無比活躍地主導著算度的整個進程。
第一,數字應用于表達預設的全部,如總分100,代表著教師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分值。當然,只要掌權者愿意,150或200分也未嘗不可,但數字一旦敲定,其嚴肅性將受到絕對的保護。
第二,數字代表著部分的價值,例如,師德水平25分,教育水平20分等。用以表征部分的數字必須在整體的框架范圍下給出,各部分之和須恰好與總分持平,不足或溢出的情況將不被允許。同時,分值間一目了然的數量差異意味著價值的高低不一,“25優于20”是一條不用特別強調便人人皆知的基本規則。
第三,數字意味著教師所可能達到的程度。數字設置的目的最終要落到教師的身上,究竟可以在“100分”中收獲幾分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教師可能完美表現全取百分,也可能差強人意勉強及格,不管能否真正接受,這些分數都將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對他們自身價值的認定。
第四,數字用以呈現等級的差別,前10名與后10名明確地代表著各自不同的兩個層級,雖然同在一個算度框架內,但所可能享受到的福利對待卻是大相徑庭的,這便涉及到數字的又一種功能,即對應于具體數值的結果兌換。前10名可以兌換到晉升機會、榮譽嘉獎與財富回報,而后10名收獲的則是錯失良機、榮譽剝奪與較少受惠。還有一種更為赤裸的匹配方式,即分值與金錢數額的一一對應,例如當學生考分超越區平均分時,每多1分獎勵200元等。
數字、數字的各種形式以及數字所代表的各種意義充斥在算度之中,構成了算度最為基本的操作邏輯。與其說數字寓于算度之中,還不如說算度依賴著數字而存在。滿眼的數字所帶來的震懾,不只是確切的安全,更是肅穆的威嚴。在數字威權的浪潮中,教師要么審時度勢,成為弄潮兒;要么隨波逐流,變成漂流瓶。
(二)線性因果
算度另一種形式的精確體現在其明朗的線性因果上,這是算度一直傳達給教師的一種直白的邏輯關系,即一個原因可導致一個結果。而完全可逆地,一個結果也可反推出某一原因。算度本身封閉的設置形式與公開的呈現方式為事實與結果間的線性因果律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從一開始,掌權者就牢牢地把控著對算度的設置權,通過對算度內容的選擇以及操作方式的規定,用以暴露他們所認為的關于重要或不重要、有用或沒有用的主觀闡釋。這意味著,算度設置一定不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掌權者不會也不能割讓任何一點自主空間給教師,賦予其自由的表達訴求以及添補價值的權利。掌權者的目的是排除一切可能的變數,避免因意外情況的發生而導致的猝不及防。科學性與合理性在算度中的無足輕重也從另一個側重映襯著精確性的重要地位。精確尚不限于此,掌權者還不遺余力地將手伸向了結構內部,通過對每一個條目的數量化加工,賦予其可操作定義,明確相對應的各級步驟與程序。在掌權者可計量與可操作的煞費苦心下,原因與結果間的脈絡關聯清晰可見。
如果說算度的封閉性設置在于讓教師最大限度地可見的話,那么在呈現方式上的公開透明則意在讓算度反向可見于教師。意圖在于發揮教師的主體性,通過教師的自覺行動進一步保障算度所宣揚的線性因果。當用以算度教師的一個個確定條目以及一項項量化操作暴露在教師眼前時,因為利益攸關,幾乎所有教師都會首先就自身的現有狀況與算度內容進行逐一對照,檢驗對目標的達成度,并找出與理想型的差距,或稱作為“自測”。“自測”意味著放棄自我的價值標準,完全地從屬于算度的規定,既不會逾越到算度框架之外去找尋認同,也不甘心較少地適應于算度體系。教師表現只有精準地匹配算度的規定,并在更大程度上符合規定的最優化標準,才有可能成為算度中的最大受惠者。
自測之后,教師將義無反顧地選擇契合掌權者的意圖,踏上算度所鋪設好的臺階,通往算度所認為的“成功之路”,這一過程本身也是明朗的。當然,教師能否“成功”關鍵在于他們有多大的企圖心、能在多大程度上妥協與適應以及能夠做出怎樣的堅持。掌權者并不在乎哪些教師最終獲得了“成功”,他們在乎的是,教師在所謂“線性因果”的蠱惑下,將全部的人生都投入到算度所明確規定的那幾件事上,在狹小的范圍內疲于奔命、計較得失。
(三)總體性判斷
算度的過程大致遵循了“總—分—總”的邏輯順序。前一個“總”是指掌權者根據統治的需要與價值偏好所構建的關于教師應然的理想模型,表現為總體性的概念體系與框架結構;“分”是指將“總”分解為若干項目,用以表達“總”的具體內涵;而后一個“總”是指教師在“分”項目中所分別得到的分數之和,即“總”的實際得分,也是算度對教師總體性價值的認定。這種認定一旦成形,其背后的構成性分數便已達成使命,并將瞬間退場。以總分形式出現的總體性價值被抽象為一種總括性的命名(例如“骨干教師”、“學科帶頭人”等),成為一定時期內對教師的蓋棺定論,這種結果集中的方式可被稱作“總體性判斷”。
總體性判斷是一種全納的判斷,它把教師各有千秋的諸方面表現都兼容并包了進來,并將其抹平為一種“無差別”的存在,賦予其與最終結果相一致的判斷。也就是說,當得到“優秀”的總體性判斷時,那么構成教師的每個部分都是無偏頗的優秀,而相應的,如若“不優秀”也將演變成處處“不優秀”。這種全納判斷掩蓋了總體背后多樣性的存在,我們無從得知支撐“優秀”的具體表現,而在“優秀”中可能裹挾著的“不優秀”也將被忽略不計。總體性判斷又是一種靜止的判斷,它試圖統攝教師的過去、現在甚至將來,并意在延展為教師一貫的表現狀態。當得到“優秀”的總體性判斷時,教師從始至終的表現都成為無波動的優秀,包括其未來都將被貼上“優秀”的標簽。
本質上來說,總體性判斷大概是在挑戰人類發展的基本規律,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無瑕,任何事物都在持續不斷地發展變化。試圖以大一統抹煞多樣、以靜止抹煞變化是極端荒謬的,但它卻扎實地存在著,還尤為普遍地被運用于社會的許多領域。不得不說,它自有其內在的合理性。
一方面,總體性判斷滿足了人們對“簡便表達”的需要。在節奏飛快的現代社會,沒有人有耐性停下來深究“是其然”與其“所以然”,沒有人有心情透過結果去審視其中蘊含著的多樣性、復雜性與可能變動。結果生產出來就是要迅速投入使用的,這是工業化社會最高效的處理方法。急不可待的社會整體心態催生了總體性判斷的繁榮,以至于無人問津于算度背后的模糊與算度過程中的一切不合理。掌權者當然比誰都愿意看到這一局面的出現。
另一方面,總體性判斷得到了一批握有話語權的教師精英的強烈追捧。教師一旦被鑒定為“優秀”,也就意味著全部且全時段地“優秀”,他們的精英身份將瞬間被建立起來,并不費吹灰之力地得以保持。為了能在總體性判斷中持續地獲益,教師精英們不遺余力地為總體性判斷站臺背書,通過增強其合法性與權威性保全與提升自身地位。
三、算度何以可能:由模糊導向的精確
發生在教師模糊性基礎與掌權者模糊性操作間的反應,孵化出一幅精確化的圖景,這種精確不僅體現在無比確鑿的過程操作中,而且還直接作用于對教師無比精準的結果處理上。算度后臺的含混不清究竟如何能夠雕琢出前臺的確切明朗,繼而導向針對教師真實的嘉獎與懲戒?模糊中究竟蘊含著怎樣的力量推波助瀾于精確的生成,又要借助何種支撐保障精確合法地挺立于算度之中,并外顯為算度的基本邏輯?
(一)簡單性思維盛行
這是一個崇拜非人格化的客觀性的時代,一個積累客觀知識并在技術上加以利用的時代,一個信仰經過科學方法的中介自動進步的時代。這是一個體系、制度、機構和統計平均的時代。[3]這個時代害怕復雜、害怕主觀,害怕一切因為不確定而引發的各種風險,所以它狂熱于將所有模糊的定性認識都轉變為精確的定量分析,寧可拋棄世界的真實也要取得技術處理上的成功。這種典型的簡單性思維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襲來,動搖著人們一曾有過的關于復雜與多樣的堅守。又或許正是因為人類無法完全認識與控制模糊的客觀現實,所以才尋求一種偏狹化、甚至異化現實的方式來強裝自身的無所不能。
算度是簡單性思維的產物,簡單性思維的無處不在是促成算度將模糊變成精確的根本原因。其一,它強調對確定性的絕對崇拜。確定性意味著邊界的清晰、邏輯的有常與權威的牢固。算度從現實(to be)中抽取出應該(ought to be)的判斷,用以標定自身有限的范疇;從多種價值傾向中強推一種計算的邏輯,用以確保固定結果的得出;將自己塑造成絕對權威,掌控著算度的各個環節以及教師的一舉一動。掌權者無懼于現實的模糊性而展開的對算度確定性模型的構建,在為教師傳遞出一種可依賴與棲居的安全感的同時,也更進一步地加深了教師對確定性的認同與崇拜。而追逐確定性的過程卻又是教師潛在的創造能力被慢慢吞噬的過程,教師卻未察覺到這一點。
其二,它強調對事物盡可能細小的分解。分解得越細小,那么事物將變得越簡單,也就越有可能為一系列理想化了的問題尋找答案。算度的分解從對教師整體性與連貫性的破壞開始,即便只是單一地鋪陳了教師各種碎片化的拼接,即便背離了教師真實的本來面貌,但也因為足夠地簡明扼要而得以安然地存活下來。
其三,它強調對事物的精致編碼與精確計算。對模糊的描述是一件繁瑣而冗長的事,沒有人敢夸口自己的描述是最準確的。為了不被這種眾說紛紜所牽累,掌權者通過對模糊事物的精致化編碼,輔之以精確的數學計算,來達成統一性的認識。在數學實踐中,我們達到了在經驗實踐中達不到的東西,即精確性。因為,用絕對的恒等式來確定理想形式是可能的。一旦人們擁有這些公式,人們就會擁有在實踐中所期望的先見之明。[4]
其四,它強調技術的全面介入。技術是簡單性思維的物化產品,在不斷創新中設計生成的各種技術手段,例如切割、測量、統計、排序、關聯技術等被廣泛地運用到算度之中,目的是通過技術實現對模糊不清的教師的窺見。技術無比活躍地介入到對教師的宰制中去,而當技術成為一種新的極權時,教師一方面順服技術所規定的工作流程,另一方面成為技術的附屬物。技術對教師的奴役,在以某種看似合理化的形式支配著教師的存在。正是在技術的步步緊逼與教師的一再妥協下,消滅模糊并創造精確才變得異乎尋常的順利。
其五,它強調轉向契約簽署的行動。算度不是掌權者的一廂情愿,將模糊導向精確也不是算度者的自說自話,如若得不到教師的認同與積極回應,那只能是一個虛構而空洞的游戲,可能還未開始,便已經結束了。在簡單性思維的指導下,與教師簽署一份算度契約將是最為穩妥的促使教師成為游戲玩家的安全保障。這并不難辦到,教師體制中人的身份、掌權者的權威壓迫以及現實的利益相關,早就預示了教師“不得不簽約”的必然。而只要有契約約束,即便出現“霸王條款”、即便明知壓榨與剝削,教師也只能任由擺布了。
從模糊到精確,經過簡單性思維作用下的各種緩沖與轉化處理,其中的突兀感被漸漸地消解,其合理性得到越發的強調。同時,模糊與精確也并非相互對立,二者彼此粘著,難以分割。精確的得出導源于模糊的主觀決策,而模糊的實質則得益于精確的外部掩蓋。
(二)恐慌的社會氛圍
如果說簡單性思維的大行其道促成了從模糊導向精確的可能,那么社會整體變動不居、惶恐不安的狀態則將這種“可能”推向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境地。現代人的普遍不幸福與不安全已是常態。其痛苦的根源來自于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的各種不確定與未知的風險。人們越發地感到,自我開始失控,而寄希望于自我的救贖變得無濟于事。在極度的恐慌與焦慮的折磨下,人們紛紛選擇將自我的掌控權交到掌權者的手中,并通過徹底地依附而明哲保身。無論掌權者做出怎樣的決定,人們都將默默地聽從與照做,尤其是當掌權者將當下不甚明了的現實導入確定化的軌道時,慌張的人們則將更為熱情地擁戴這種改善,并如饑似渴地投身其中。
教師作為兼具著多重身份,并承擔著歷史文化傳承及教書育人等多重使命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成員,其恐慌的程度不會比其他任何人低,而由此引發的自我迷失也不會更少。教師的恐慌,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怕成為“被集體拋棄的個別人”。算度是一項集體性契約,乙方包括了被命名為教師的所有人。當所有教師都圍繞著掌權者的指令,進行著精確化的自我改造時,任何置身事外、橫眉冷對的個體都將被視作異類,面臨被踢出局的危險。個體被與別人不同的異樣感覺團團圍住,越發地惴惴不安起來。被“大多數”拋棄是一件悲慘的事,不管“大多數”是否必然地代表了真理和真正的價值歸屬,個體的單獨行動都不是明智之舉。
二是怕成為“窮追不舍的落后者”。世界的快速變化與功利傾向讓所有人的浮躁已迫近警戒線,“忙”成為社會人的基本狀態,“急”成為人們一遇事便不自覺地緊張起來的基本情緒。對生怕“來不及”、生怕“趕不上”、生怕“落于人后”與生怕“錯過時機”的擔憂無節制地爆發與泛濫。教師沒有時間深究自己所一直追求的目標、正在完成的任務、四處輾轉的奔波是否真正值得,更沒有耐心琢磨社會、自身以及學生是否復雜多變,他們只顧著埋頭往前趕,既無暇思量去往的遠方,也無心丈量走過的地方。至于算度將模糊生產為精確的神秘過程,教師的視若無睹與集體漠視亦在意料之中。
三是怕成為“承擔數量劣勢的失敗者”。過度競爭的現狀讓教師主動放棄了從容不迫的優雅,而瘋狂地熱衷于各種物化成果在數量上的激增。對于自身發展的限度與適可而止,教師早已失去了獨立的判斷能力。在教師看來,只有一遍遍地重復算度的要求,并從中獲得越來越多單一維度的肯定才能感到踏實與安全。“肯定”的級別越高,則越有成就感。
因為對算度精確框架內單一事件的過度熱情,教師在算度之外所有的潛能與創造也隨之被大面積地扼殺了,這同時也引發了教師的第四種恐慌,即怕成為“精確審判下的無用人”。如古人般煮上一壺清酒吟詩作對,在現代人的眼中大概是一種奢侈。而將日常的杯碗筷碟雕刻得美倫美煥,大概也是工業社會只有頭腦發熱才會做出的選擇。古人將事物的藝術審美與道德情感價值看得與功能效用一樣或更為重要,而在現代,卻完全相反。功用價值被無限地放大,甚至成為人們行動的唯一標尺,在這個什么都與績效扯上關系的現實世界中,任何漫無目的的嘗試都將被看作是虛度光陰,事情一旦被冠上了“無用”的頭銜終將被打入冷宮。教師害怕掉入無用之功的泥潭中碌碌無為,而算度的到來猶如點亮了一盞“明燈”,令教師在有的放矢的權威導引中看到了希望,看到可以前進的“正確”而“有用”的方向。同時,“努力就能勝利”也成為一種勵志的信念鼓舞了一批批教師的前赴后繼。而被掌權者建構出來的以“有用”為前提的所謂“勝利”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了教師自身的價值呢?答案難免悲觀。
被恐慌折騰得焦躁不安的教師強烈地感到自身的無能為力,他們對自己感到了徹底的失望與不自信,甚至迷失了自己的價值。個人的自我已受到削弱,因此他覺得無權力和極度地不安全,他生活在一個與他已失去關聯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里,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成為工具,他成為他雙手建造的機器的一部分。[5]自我被物化為用以滿足某種需求的工具,而算度與自我算度也被內化為教師自然而然的行動慣習。壓迫者的成功有賴于誘使受害者的理性計算比達到其原初目的的可能性存在得更為長久;也有賴于能夠讓人們——至少是某些人,在某段時間里——在一個公認的非理性環境里做出理性的行為。[6]
恐慌的社會氛圍創造了算度的不可懷疑,而一切可能由教師發起的對算度的懷疑,最終也只會因陷入無盡的自我懷疑之中而悲涼收場。
[1]周易,遠藤.模糊美學研究:過程論[J].外國文學研究,1990,(2).
[2]吳玉軍,王秀江.確定性的解構與現代人的非安全感[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
[3][美]杰拉耳德·霍耳頓.科學與反科學[M].范貸年,陳養惠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220.
[4][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130.
[5][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M].馮川等譯.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01.
[6][英]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M].楊渝東,史建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188.
(責任編輯:曾慶偉)
宗錦蓮/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教育學原理和教育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