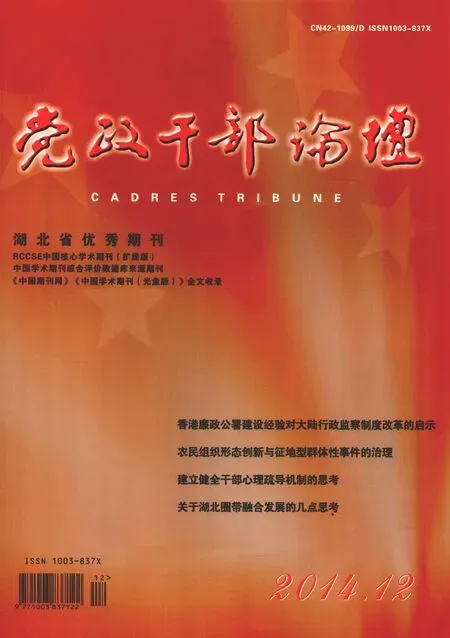我國土地征收存在的問題及農(nóng)民權(quán)益保障措施
○ 彭建軍 任艷坤
目前我國土地征收征用領(lǐng)域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在一些地方,土地財(cái)政居于地方財(cái)政的支配地位,一些不符合法律規(guī)范、缺乏程序、忽視農(nóng)民利益的現(xiàn)象大量存在。國土資源部的調(diào)查顯示,地方一些市、縣政府主導(dǎo)的違法違規(guī)行為屢禁不止,當(dāng)前土地管理面臨的形勢依然比較嚴(yán)峻。2014年國土資源部發(fā)布的《國家土地督察公告》(第7號)透露,2013年例行督察共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存在2.38萬個(gè)問題,涉及土地面積20.12萬公頃[1]。而由此導(dǎo)致的侵犯農(nóng)民合法權(quán)益、引發(fā)社會(huì)矛盾的隱患也時(shí)有發(fā)生。因此需要對這一問題持續(xù)關(guān)注。
一、土地征收中的違法違規(guī)現(xiàn)象分析
2014年4月至6月,國家土地督察機(jī)構(gòu)對全國56個(gè)市(州、盟、區(qū)、縣)土地利用和管理情況開展了監(jiān)督檢查,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的土地違法違規(guī)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有以下方面:
1.征地補(bǔ)償安置落實(shí)不到位。如山東省濟(jì)寧市2013年有3個(gè)縣(市)的5個(gè)城鎮(zhèn)批次用地1200畝已批準(zhǔn)征收土地,但超過批準(zhǔn)時(shí)間3個(gè)月未實(shí)施征地補(bǔ)償,拖欠被征地農(nóng)民征地補(bǔ)償安置費(fèi)用2081.23萬元。2013年上報(bào)134個(gè)城鎮(zhèn)批次用地,涉及征收土地2.99萬畝,需繳納被征地農(nóng)民社會(huì)保障資金4.09億元,未落實(shí)到被征地農(nóng)民個(gè)人。
2.土地出讓收支管理不規(guī)范。以山東為例,截至2014年4月,濟(jì)寧市存在3.41億元土地出讓收入未按規(guī)定征收到位,涉及24宗地。其中,濟(jì)寧北湖恒大名都置業(yè)有限公司欠繳土地出讓收入12778萬元,嘉祥縣山東原申投資有限公司欠繳土地出讓收入4600萬元。有關(guān)縣、市、區(qū)有30宗已供土地未按規(guī)定繳納滯納金3493.27萬元。曲阜市違規(guī)將5000萬元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解決農(nóng)信社不良貸款。
3.違規(guī)返還土地出讓資金。以吉林省四平市土地違法違規(guī)問題中涉及的幾種情況為代表:一是土地出讓收支管理不規(guī)范,四平市政府以會(huì)議紀(jì)要形式違規(guī)減免四平市公安局、四平市紀(jì)律檢查委員會(huì)廉政教育中心等5個(gè)項(xiàng)目的土地劃撥價(jià)款,涉及金額2097.35萬元;二是梨樹縣政府違規(guī)批準(zhǔn)向天成工貿(mào)有限公司項(xiàng)目返還土地出讓收入,涉及金額328萬元;三是四平特驅(qū)飼料有限公司等5個(gè)項(xiàng)目違反了土地出讓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規(guī)定,涉及金額3763.68萬元;四是四平市東南新城、四平市經(jīng)濟(jì)開發(fā)區(qū)、公主嶺嶺西新城在未取得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和土地征收批準(zhǔn)前,擅自實(shí)施土地征收行為,導(dǎo)致大量耕地閑置、荒蕪,涉及土地面積3912.45畝(其中耕地3902.85畝)。
4.違規(guī)抵押融資。2011年以來,湖州市及所轄的有關(guān)區(qū)縣政府在未履行土地出讓等程序,未繳納土地出讓收入的情況下,通過會(huì)議紀(jì)要和抄告單的形式要求相關(guān)部門將494宗、2.4萬畝土地違規(guī)登記給湖州市城市建設(shè)發(fā)展總公司等74家國有公司用于抵押融資。截至2014年4月,湖州市存在8.35億元土地出讓收入、5365.65萬元土地劃撥款未按規(guī)定征收到位。其中,長興縣出讓給浙江美合生態(tài)旅游發(fā)展有限公司的79.65畝商業(yè)用地,欠繳土地出讓收入4160萬元。
5.耕地占補(bǔ)平衡落實(shí)不到位。據(jù)統(tǒng)計(jì),在2013年驗(yàn)收或用于補(bǔ)充耕地的土地整治項(xiàng)目中,有24個(gè)項(xiàng)目新增耕地的部分地塊在立項(xiàng)前為耕地,涉及面積1647.9畝;有97個(gè)項(xiàng)目驗(yàn)收的新增耕地實(shí)際為林地、養(yǎng)殖水面等農(nóng)用地,涉及面積1.08萬畝。此外,有18宗劃撥土地未按規(guī)定繳納耕地開墾費(fèi)等相關(guān)費(fèi)用,涉及金額1119.75萬元[2]。
以上五種情況顯示,由土地出讓而產(chǎn)生的利益(土地資本)與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選擇性利用,甚至是違反規(guī)定的利用,導(dǎo)致很多土地并未地盡其利,地顯其值,資金不僅難以到位,很多土地用途被擅自更改、土地費(fèi)用被隨意減免。農(nóng)民不僅得不到基本的補(bǔ)償,更難論其他利益。
二、我國法律法規(guī)對土地征收的權(quán)益保障
權(quán)益是指在社會(huì)中產(chǎn)生,并以一定的社會(huì)承認(rèn)作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權(quán)能和利益[3]。被征地農(nóng)民權(quán)益,是指被征地農(nóng)民在征地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享有的不被侵犯的權(quán)利和利益,包括實(shí)體權(quán)利和程序權(quán)利。實(shí)體權(quán)利為補(bǔ)償權(quán)、安置權(quán)、社會(huì)保障權(quán),二者主要表現(xiàn)為經(jīng)濟(jì)利益,可以通過貨幣與金錢給付完成;程序權(quán)利包括知情權(quán)、建議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這對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社會(huì)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有直接影響。這些權(quán)利都需要通過具體的法律和政策來保障,針對這些問題我國已經(jīng)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土地征收征用法律體系。
(一)憲法對征收與補(bǔ)償?shù)幕疽?guī)定
2004年憲法修改時(shí)對征收權(quán)力與補(bǔ)償權(quán)利進(jìn)行了完善。《憲法》第10條規(guī)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shí)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bǔ)償。”該條規(guī)定的關(guān)鍵詞為“國家”、“公共利益”、“依法”、“征收或征用”、“給予補(bǔ)償”。該條款反映出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的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國家依法可行使征收權(quán)(征用權(quán)),而利益相對方則擁有補(bǔ)償權(quán)。征收權(quán)由行政機(jī)關(guān)行使,力量相對強(qiáng)大,而相對方則處于明顯弱勢,需要更具體的制度設(shè)計(jì)來保障和均衡。因此,法律對利益相對方的保障更為重要。因此,以憲法規(guī)定來看:一是目的要正當(dāng),即需要出于“公共利益”;二是依據(jù)要明確,即需要“依法”,無論依哪種“法律”或規(guī)范性文件,都需要于法有據(jù);三是行為要規(guī)范,即只能是法律規(guī)定、正當(dāng)途徑之內(nèi)的征收、征用行為;四是程序要健全,需要履行嚴(yán)格和完整的程序;五是要體現(xiàn)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則,要能體現(xiàn)“對價(jià)”,這種對價(jià)必須以國家規(guī)定的標(biāo)準(zhǔn)來落實(shí),既不能無限抬高也不能隨意降低;六是要有必要的制度和措施,以嚴(yán)格體現(xiàn)憲法的精神和法律的權(quán)威,包括動(dòng)用必要的立法、行政監(jiān)督、司法、公眾輿論監(jiān)督等公共資源來保障這些條款中所涉及群體和個(gè)體的利益。
(二)物權(quán)法、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中的補(bǔ)償方式及標(biāo)準(zhǔn)
《物權(quán)法》第42條規(guī)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yīng)當(dāng)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bǔ)償費(fèi)、安置補(bǔ)助費(fèi)、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bǔ)償費(fèi)用,安排被征地農(nóng)民的社會(huì)保障等費(fèi)用。”而《土地管理法》也有多處提到對農(nóng)民進(jìn)行補(bǔ)償,明確表達(dá)了對被征地農(nóng)民進(jìn)行合理公平補(bǔ)償符合社會(huì)主義價(jià)值理念,體現(xiàn)了國家對弱者的保護(hù)。《物權(quán)法》是對憲法的細(xì)化,也與土地法相互補(bǔ)充。其權(quán)利列舉方式使得被征地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jì)補(bǔ)償和社會(huì)保障有法可依,但沒有明確土地征收補(bǔ)償原則和具體執(zhí)行機(jī)制。“集體所有的土地”在權(quán)利主體的界定上沒有問題,但在權(quán)利分享和利益實(shí)現(xiàn)中則暴露出很多問題。
此外,物權(quán)法在征收程序中指出:“被征地的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應(yīng)當(dāng)將征收土地的補(bǔ)償費(fèi)用的收支狀況向本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成員公布,接受監(jiān)督。”國家立法已經(jīng)注意到了需要通過保障知情權(quán)的方式來體現(xiàn)被征地農(nóng)民的監(jiān)督權(quán)。但如何公布,公布哪些項(xiàng)目,地方政府執(zhí)行得還不夠理想。
(三)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中的補(bǔ)償對象及分配方式
我國土地管理的法規(guī)規(guī)定,土地補(bǔ)償費(fèi)歸農(nó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bǔ)償費(fèi)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享有。
從權(quán)利主體和權(quán)益分享對象來說,涉及農(nóng)村土地承包權(quán)人切身利益的主要是土地補(bǔ)償費(fèi)和青苗補(bǔ)償費(fèi)。一般來說青苗補(bǔ)償費(fèi)是指對被征地的地上生長的農(nóng)作物,如水稻、玉米、小麥等造成的損失所給予的一次性經(jīng)濟(jì)補(bǔ)償費(fèi)用。如依《土地管理法》第47條第2款的規(guī)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補(bǔ)償費(fèi),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chǎn)值的6至10倍;安置補(bǔ)助標(biāo)準(zhǔn),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chǎn)值的4至6倍,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chǎn)值的15倍;該條第6款規(guī)定,土地補(bǔ)償費(fèi)和安置補(bǔ)助費(fèi)的總和不得超過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chǎn)值的30倍。被征地農(nóng)民群眾普遍認(rèn)為,按照法律規(guī)定的土地補(bǔ)償費(fèi)和安置補(bǔ)助費(fèi)最高不超過被征地前3年平均年產(chǎn)值30倍的標(biāo)準(zhǔn),難以滿足自己及后代的生活需求,忽視了土地潛在的長久保障功能和長期利益。同時(shí)這種“產(chǎn)值倍數(shù)法”的補(bǔ)償計(jì)算方式?jīng)]有綜合考慮土地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商業(yè)功能,僅僅是以過往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來作為評判的標(biāo)準(zhǔn),不夠科學(xué)與合理。
(四)《行政復(fù)議法》及《土地管理法實(shí)施條例》規(guī)定中的爭議解決機(jī)制
《行政復(fù)議法》第6條及第30條第2款規(guī)定:“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對國務(wù)院、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決定不服的,可以申請行政復(fù)議,但行政復(fù)議的決定為最終裁決。”
《土地管理法實(shí)施條例》第25條規(guī)定:“對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xié)調(diào);協(xié)調(diào)不成的,由批準(zhǔn)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征地補(bǔ)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shí)施。”在本條法規(guī)中僅僅規(guī)定了被征地農(nóng)民可以質(zhì)疑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但卻沒有對具體的裁決作出規(guī)定,這就出現(xiàn)了法律空白點(diǎn),在利益的驅(qū)動(dòng)下,很多執(zhí)法者將會(huì)作出違法行為,使被征地農(nóng)民無法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權(quán)利。再者,沒有正當(dāng)?shù)恼鞯爻绦颍徽鞯剞r(nóng)民就不能保證自己在征地過程中因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的缺乏而受到的侵害,而這應(yīng)是造成大量土地糾紛的主要原因。
三、土地征收制度的權(quán)益保障對策
部分地方政府征地補(bǔ)償安置政策落實(shí)不到位,侵害被征地農(nóng)民合法權(quán)益的問題在最近的督察中被曝光。如《國家土地督察公告》(第7號)公告表示,14個(gè)城市存在征地補(bǔ)償不到位、安置不落實(shí)、被征地農(nóng)民社保落實(shí)不到位等問題,拖欠征地補(bǔ)償安置費(fèi)用19.82億元,未落實(shí)社保資金2.41億元,涉及19517人[4]。這一數(shù)據(jù)反映出當(dāng)前土地征收制度的執(zhí)行存在很大問題,需要完善制度,加強(qiáng)保障措施。
(一)根據(jù)不同情況合理確定補(bǔ)償原則
土地補(bǔ)償原則有三種:完全、不完全和公正補(bǔ)償原則。完全補(bǔ)償原則是指國家對因土地征收過程受到的損失進(jìn)行全額補(bǔ)償。這種原則遵從了所有權(quán)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和平等原則,也保障了被征地農(nóng)民的生存權(quán)。不完全補(bǔ)償原則是國家對被征地農(nóng)民給予一定的補(bǔ)償,即補(bǔ)償數(shù)額小于權(quán)益損失。這種原則更強(qiáng)調(diào)國家的利益,公民有忍受相當(dāng)犧牲義務(wù)。公正補(bǔ)償原則,則是分情況而采取前兩種補(bǔ)償方式。
不同學(xué)者給出了不同意見:江平教授主張“完全補(bǔ)償”說,認(rèn)為“征收私人財(cái)產(chǎn)必須給予完全補(bǔ)償”[5]。梁慧星教授則贊同公正補(bǔ)償原則:“憲法要規(guī)定給予公正補(bǔ)償”[6]。筆者以為,我國還屬于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jì)還不夠發(fā)達(dá),采取完全補(bǔ)償原則不現(xiàn)實(shí)。我國應(yīng)當(dāng)采取第三種公正補(bǔ)償原則,對于一些商業(yè)用地的征收可以采取完全補(bǔ)償原則,對于純粹的公共利益的土地征收如學(xué)校用地,可以采取公正補(bǔ)償原則。
(二)合理分配土地征收補(bǔ)償收益
首先要保證征收補(bǔ)償及安置政策落實(shí)到位。實(shí)踐中這一類問題仍然較為突出。如關(guān)于“征地補(bǔ)償安置落實(shí)不到位”的案例:邢臺至衡水高速公路邢臺段等36個(gè)項(xiàng)目,拖欠被征地農(nóng)民征地補(bǔ)償安置費(fèi)用2.21億元。其中,河北省政府批準(zhǔn)的邢臺至衡水高速公路邢臺段項(xiàng)目,涉及征地面積1.47萬畝,拖欠被征地農(nóng)民征地補(bǔ)償安置費(fèi)用0.73億元[7]。
鑒于農(nóng)村土地所有權(quán)主體虛位的弊端(名義為集體所有,實(shí)際為一些鄉(xiāng)村干部控制),應(yīng)使補(bǔ)償收益更多偏向失地農(nóng)民,強(qiáng)化對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的補(bǔ)償,使土地補(bǔ)償費(fèi)能真正分配給農(nóng)民,使農(nóng)民能再就業(yè)并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現(xiàn)行土地征收過程中給村集體數(shù)目較大的補(bǔ)償安置費(fèi),大多不僅沒能壯大集體經(jīng)濟(jì),反而為少數(shù)鄉(xiāng)村干部腐化提供了便利條件,成為惡化干群關(guān)系的焦點(diǎn);而農(nóng)民失去土地后所獲得的有限補(bǔ)償難以維持長期的生計(jì)。由于被征地農(nóng)民將永遠(yuǎn)失去土地的經(jīng)營權(quán)、可靠的生活來源和社會(huì)保障,在土地補(bǔ)償中尤其應(yīng)考慮這一特殊性,使補(bǔ)償收益更多地偏向被征地農(nóng)民。如果讓被征地農(nóng)民獲得收益的中頭,不僅可以大幅減少中間交易成本,有效遏制“尋租”,而且會(huì)增強(qiáng)被征地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從而化解被征地農(nóng)民問題。
(三)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經(jīng)驗(yàn),適當(dāng)增加補(bǔ)償范圍
由于各國(地區(qū))立法的不同,補(bǔ)償范圍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如日本法律對補(bǔ)償范圍作了如下規(guī)定:(1)征用損失補(bǔ)償,按被征用財(cái)產(chǎn)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計(jì)價(jià)補(bǔ)償;(2)通損補(bǔ)償,即因征地而通常可能受到的附帶性損失補(bǔ)償。包括地上建筑物、設(shè)備、樹木補(bǔ)償;遷移費(fèi)補(bǔ)償;歇業(yè)、停業(yè)補(bǔ)償;營業(yè)規(guī)模縮小補(bǔ)償以及農(nóng)業(yè)補(bǔ)償和林業(yè)補(bǔ)償;(3)少數(shù)殘存地補(bǔ)償;(4)離職者補(bǔ)償;(5)事業(yè)損失補(bǔ)償[8]。德國法律對土地征收補(bǔ)償范圍作了如下規(guī)定:(1)土地或其他標(biāo)的物權(quán)利損失補(bǔ)償;(2)營業(yè)損失補(bǔ)償;(3)征收標(biāo)的物上的一切附帶損失補(bǔ)償[9]。我國臺灣地區(qū)土地法所確定的補(bǔ)償范圍則是:(1)地價(jià)補(bǔ)償;(2)改良物的補(bǔ)償;(3)接連地的損害補(bǔ)償[10]。
與其他國家設(shè)身處地、細(xì)致周密地考慮補(bǔ)償對象的直接損失、生計(jì)和各種利益相比,我國土地征收的補(bǔ)償范圍明顯偏窄。農(nóng)民失去土地之后,首先面臨就業(yè)的壓力,勞動(dòng)力的轉(zhuǎn)移問題應(yīng)運(yùn)而生,如果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進(jìn)一步會(huì)產(chǎn)生醫(yī)療保險(xiǎn)、社會(huì)保障、子女上學(xué)等一系列的問題。但是在現(xiàn)有的征地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當(dāng)中,這些問題并未得到相應(yīng)的解決。因此在制度設(shè)計(jì)時(shí)需要重點(diǎn)考慮土地的生計(jì)功能、保障功能,以充分實(shí)現(xiàn)土地的市場價(jià)值和社會(huì)功能。
(四)重視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shí)行土地征收信息公開透明
案例:四平市東南新城、四平市經(jīng)濟(jì)開發(fā)區(qū)、公主嶺嶺西新城在未取得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和土地征收批準(zhǔn)前,擅自實(shí)施土地征收行為,導(dǎo)致大量耕地閑置、荒蕪,涉及土地面積3912.45畝(其中耕地3902.85畝)。
該案例顯示,是否得到征地權(quán),往往由行政機(jī)關(guān)主導(dǎo),其前置性行政行為既屬于自由裁量權(quán)的性質(zhì),無須相對人知曉,但也正如此,才使得行政機(jī)關(guān)將本應(yīng)公開的其他行政行為和程序也一并省略。行政程序最重要的特征是行政相對人的知曉和參與,相對人通過參與實(shí)現(xiàn)公民權(quán)利對政府權(quán)力的制約,實(shí)現(xiàn)“以權(quán)利制約權(quán)力”。我國農(nóng)民作為集體成員在涉及自己權(quán)益的財(cái)產(chǎn)被征收時(shí),理應(yīng)享有參與到征收程序之中的權(quán)利。只有依靠程序公正也就是切實(shí)保證農(nóng)民的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及異議權(quán),才能最終防止政府強(qiáng)大的公權(quán)力侵犯私權(quán)。
為貫徹落實(shí)黨中央、國務(wù)院部署要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13年1月,國土資源部印發(fā)《關(guān)于做好征地信息公開工作的通知》(國土資廳發(fā)〔2013〕3號),明確了各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職責(zé),規(guī)范了公開渠道和辦理要求。并明確指出當(dāng)前存在的信息公開問題:如普遍存在征地信息公開不到位問題,主要體現(xiàn)在基層征地信息公開內(nèi)容不全面、公開行為不規(guī)范、公開程序不健全、群眾獲知公開信息不便捷不及時(shí)等方面,與農(nóng)民群眾的期望還有較大差距,影響了征地實(shí)施工作。當(dāng)前應(yīng)要求市、縣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guī)定,切實(shí)將征地信息公開列為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重點(diǎn)。
(五)完善司法救濟(jì),確保土地征收符合社會(huì)正義
司法作為公民救濟(jì)的最后一道防線,其公正性和權(quán)威性成了公民救濟(jì)的強(qiáng)有力保障,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精神的具體化。具體措施包括:一是要強(qiáng)化執(zhí)法監(jiān)督和審查制度。對征地過程中被征地農(nóng)民的權(quán)益保障狀況進(jìn)行監(jiān)督和審查,一旦行政行為違法可以予以撤銷,在程序上保證被征地農(nóng)民免受侵犯的可能。二是對被征地農(nóng)民權(quán)益的侵犯可鼓勵(lì)提起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實(shí)現(xiàn)救濟(jì)。如認(rèn)為征地補(bǔ)償爭議是政府與相對人關(guān)于行政補(bǔ)償?shù)臓幾h,屬于行政爭議,應(yīng)當(dāng)通過行政訴訟解決[11]。如認(rèn)為補(bǔ)償糾紛與具體行政行為糾紛性質(zhì)不同,類似于民事糾紛,應(yīng)采用民事訴訟救濟(jì)的方式[12]。可以根據(jù)糾紛的內(nèi)容進(jìn)行相應(yīng)處理。三是國家應(yīng)當(dāng)為被征地農(nóng)民盡可能的提供法律援助。由于被征地農(nóng)民大多數(shù)文化程度不高,經(jīng)濟(jì)能力有限,很容易出現(xiàn)農(nóng)民要么放棄司法救濟(jì),要么采取過激或者非理性的思維方式進(jìn)行解決,不利于社會(huì)的和諧和穩(wěn)定。我國的法律援助機(jī)構(gòu)應(yīng)專門對土地征收過程中的糾紛進(jìn)行法律援助,這樣不但保證了被征地農(nóng)民的司法權(quán),也有利于社會(huì)的穩(wěn)定。當(dāng)前土地確權(quán)糾紛、經(jīng)濟(jì)利益糾紛事實(shí)上正是各地法律援助機(jī)構(gòu)的主要事項(xiàng)之一,只是政府的財(cái)政支持和組織支持還應(yīng)加強(qiáng)。
(六)注重土地權(quán)益的保障功能,進(jìn)一步完善社會(huì)保障
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已經(jīng)明確了農(nóng)民依法應(yīng)享有的社會(huì)保障權(quán),這也是農(nóng)民生活和生存的一道屏障。2014年7月30日,武漢督察局在《例行督察意見書》中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指出被征地農(nóng)民社會(huì)保障制度和社會(huì)保障費(fèi)用落實(shí)不到位的問題,并提出相關(guān)整改意見。經(jīng)湖北省人民政府同意,定于2014年9月20日至2015年6月30日在全省開展被征地農(nóng)民社會(huì)保障問題集中自查整改工作。以自查整改社會(huì)保障資金不到位問題、制定完善被征地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險(xiǎn)實(shí)施辦法作為主要任務(wù),分自查清理、整改糾正、完善制度三個(gè)階段開展。通知要求各地要以此次集中自查整改工作為契機(jī),在整改落實(shí)的基礎(chǔ)上,建立其被征地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險(xiǎn)補(bǔ)償機(jī)制,實(shí)行預(yù)存款制度,確保“先保后征”,規(guī)范被征地農(nóng)民參加養(yǎng)老保險(xiǎn)辦法,維護(hù)好被征地農(nóng)民的合法權(quán)益[13]。
目前我國并沒有一部社會(huì)保障法對被征地農(nóng)民的社會(huì)保障作出規(guī)定,只是一些零散的社會(huì)保障條例,也甚少提及被征地農(nóng)民的社會(huì)保障[14]。因此,首先應(yīng)由國家出臺一部社會(huì)保障法,對社會(huì)保障法的目的、基本原則、社會(huì)保障種類、資金管理、法律責(zé)任、適用范圍等做出概括性規(guī)定,以此作為被征地農(nóng)民社會(huì)保障的立法依據(jù)。其次,國家要出臺對被征地農(nóng)民再就業(yè)政策,比如對被征地農(nóng)民免費(fèi)的技術(shù)培訓(xùn)、資金貸款等,支持被征地農(nóng)民再就業(yè)。再者,國家要關(guān)心被征地農(nóng)民的社會(huì)保障問題。設(shè)立被征地農(nóng)民失業(yè)保障金、再就業(yè)扶助金、養(yǎng)老補(bǔ)助金、醫(yī)療保險(xiǎn)等,制定切實(shí)可行的計(jì)劃,切實(shí)做好被征地農(nóng)民的社會(huì)保障工作。并盡快將被征地農(nóng)民納入社會(huì)保障體系,確保被征地農(nóng)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yuǎn)生計(jì)有保障,并建立配套的實(shí)施機(jī)制。
[1][4]郄建榮:《省級政府1738個(gè)項(xiàng)目存在非法批地》,2014-03-22 http://www.mlr.gov.cn/xwdt/mtsy/qtmt/201403/t20140322_1308617.htm
[2]國家土地總督察辦公室:《2014年土地督察約談9個(gè)地市的情況》,《國家土地督察公告第9號》2014-09-26。
[3]鐘云華:《刑事社會(huì)抗拒風(fēng)險(xiǎn)化解研究》,《湖北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年第2期。
[5]江平:《完善保護(hù)私人財(cái)產(chǎn)法律制度應(yīng)遵循的原則》,《人民日報(bào)》2003年1月29日。
[6]梁慧星:《談憲法修正案對征收和征用的規(guī)定》,《新華文摘》2005年第1期。
[7]國家土地總督察辦公室:《2014年土地督察約談9個(gè)地市的情況》,《國家土地督察公告第9號》,2014年9月26日。
[8][10]柴強(qiáng):《各國(地區(qū))土地制度與政策》,北京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8頁。
[9]李珍貴:《美國土地征用制度》,《中國土地》2001年第4期。
[11]程潔:《土地征用糾紛的司法審查權(quán)》,《法學(xué)研究》2004年第2期。
[12]郭潔:《土地征用補(bǔ)償法律問題探析》,《當(dāng)代法學(xué)》2002年第8期。
[13]國家土地督察武漢局:《湖北省積極落實(shí)例行督察關(guān)于全省集中自查的普遍性問題整改要求》,國土資源部網(wǎng)站,2014-09-29。
[14]吳傳毅:《法治中國的時(shí)間維度解構(gòu)》,《湖北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