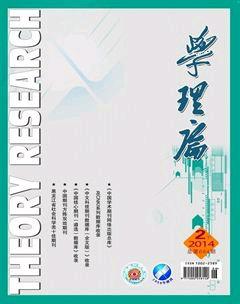孔墨之爭淺析
來曉維
摘 要:儒家和墨家作為先秦時期的顯學,為當世留下了智慧的結晶。然而兩者雖都是積極入世之學,但在“救世”之策的選擇上卻是南轅北轍。主要通過比較兩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和墨子的出身背景和生平經歷,分析了二者思想在宗教觀念、道德觀念、政治觀念和認識論四方面的不同發展。
關鍵詞:仁愛;兼愛;儒墨之爭;名實之辯
中圖分類號:B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6-0016-02
先秦時期,周朝分崩離析,諸子百家爭鳴。而最為當世所推行的便是儒家、墨家和道家。相比道家思想的虛妄無為,消極入世,孔墨兩家都偏向于積極入世。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王桐齡就做出了“孔墨重實際,老派崇虛想;孔墨主力行,老派主無為;孔墨貴人事,老派貴出世;孔墨主勉強,老派明自然;孔墨主干涉,老派主放任”[1]1的論斷。儒、墨兩家有如許相似之處,所以我們熟知儒、道兩家在出世入世態度上的迥然不同,卻極少關注儒、墨兩家思想的內在沖突,即在“如何積極入世”的方式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引發了兩家在宗教觀念、道德觀念、政治觀念和認識論上的諸多爭論。然而,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取得正統地位之后,墨學逐漸被湮沒,儒墨之爭從此沒了下文。但兩家學說在“治世”、“救世”之策上的迥異,卻依然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
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為春秋時期宋國沒落貴族的后代,“可說是在奴隸制趨于崩潰時期從貴族中分離出來的士階層代表,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2]57。孔子早年從政,后又周游列國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晚年回鄉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出身貴族世家,又參與政事,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孔子的思想其實代表的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利益,他主張恢復周禮,重整社會等級秩序。
而墨家學說的創始人墨子則是“一位由手工業工匠而上升的士”[3]2,相比孔子對周禮的推崇,他更向往夏禹時期的社會。他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后來發現“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于是“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他更多地從平民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代表的是當時小生產者和手工業者的利益[3]3。
兩者都出生于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弱肉強食的時代,正是兩者在身世背景和生平經歷上的不同,導致了二者在宗教觀念、道德觀念、政治觀念和認識論上的不同。
一、宗教觀念上的區別
在展開儒墨兩家在宗教觀念上的差異分析前,我們首先要說明,儒家和墨家的宗教思想與我們尋常所知的宗教是有所不同的。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猶太教所建立的是一個遠離現世社會的彼岸世界,而儒墨兩家的宗教思想卻是基于現世社會的。但是,儒、墨兩家對于天命和鬼神的態度卻是不同的。
(一)對于天命的觀念
在天命方面,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也許與他周游列國卻終不受信用的坎坷經歷有關,在他看來,貧富貴賤、死生禍福都由天命所決定,是不可抗拒的,無法人為改變。這種天命論繼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天命觀念傳統,但孔子也并非完全是聽天由命,而是對以往的天命思想做了一定的升華。一方面,孔子保留了“天”的神秘性,以及對于“天”和“天命”的信仰和敬畏,抱有“天道遠,人道邇”的態度;另一方面,他不因為承認了“天命”的不可違抗而放棄主觀努力。“他所重視的是人們是否盡了自己的責任,真正做出了努力;只要盡到了責任,努力去做了,盡管沒有得到成功,也是可以于心安然的”[4]6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修正了“天”作為上古宗教迷信的形象,而將其與個人的內在道德修養相結合,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沒落的奴隸制。
墨家對于儒家的“天命論”持批判態度,并提出了質問,“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非命中》)這集中體現了墨子“非命”的思想。相比孔子生死由天的說法,墨子強調人力,指出人必須通過耕田織布等勞動才能夠生活,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墨子還確立了“三表法”對其“非命”思想進行了論證,無論從實踐經驗還是從歷史事實來看,若失去了人的作為,都不會是現在的結果。這是奴隸制瓦解過程中人類思想的一大進步。然而在其“天志”的學說中,墨子又肯定了天的意志,用它來解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認為“天志”是天下萬事萬物的規矩,是區分是非善惡的標準。從天體運行、季節變化,到國家制度的建立和王公侯爵的設立,都是天的意志,這就又回到了宗教迷信的層面。
(二)對于鬼神的觀念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孔子很少提及鬼神,他所關心的只是現實的世界和人生,而對于是否有鬼神、對于死后是否有另一個世界,他都不予考慮,不去討論[4]61。“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這些都表明了孔子對于鬼神的態度,即要對鬼神敬而遠之,專心致力于人道。
相反,墨子的“明鬼”思想肯定了鬼神的意志。他引用了中國有史以來“見鬼之形,聞鬼之聲”的諸多記載,來證明鬼神確實存在而非虛妄。但墨子對鬼神意志的肯定,也并非是上古野蠻時代對于鬼神的絕對信仰,而是將它作為檢驗人心、改良社會的一種方法,算是以古代的迷信思想來為世俗之人說法。
二、道德觀念上的區別
(一)對于仁愛的觀念
儒墨兩家都講“仁愛”、“愛人”,都以“利人濟世”為己任,但在方式上卻有所區別。
“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在他看來,“仁”是君子所必備的品德。何謂“仁”?“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也就是說,一個人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使之符合禮的規范才算是具備了“仁”的品德。又何謂“禮的規范”?孔子以為,就是周禮,即禮所制定的政治秩序。因此,儒家講“仁愛”,其實是有親疏尊卑之分的,這種“仁愛”,是有差等的,因人而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從此句可看出,孔子認為只有貴族才具有“仁”的品德,而普通的百姓不可能具備這一品德。這也從旁佐證了儒家的“仁愛”是有等級之分的這一觀點。“仁者愛人”,既然普通百姓都不具備“仁”的品德,又如何去愛人呢?所以,只有上位者才能以“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去愛人,且這種“愛”是以自我為中心而向外推廣的,根據遠近親屬而有所區別。
孔子時時強調等級秩序,是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去看待“仁愛”的,墨子則立足于整個社會,試圖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認為要“兼以易別”,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即愛不應有親疏、厚薄的差別,而應該要做到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要“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使彼此的利益兼而為一。墨子以為,只要能普遍實行“愛人若愛其身”,那就能達到一切“和調”[2]70。“仁”在墨子看來并非是對周禮的恢復,也不是出于主觀動機的忠恕之道,而是以利人、利國為具體內容的,更注重行為所產生的實際效果。相比儒家鮮明的貴族立場,墨子所提出的“兼愛”思想更能反映出平民百姓想要消除上下貴賤等級之分的愿望。
(二)對于義利的觀念
比較儒墨兩家思想,最明顯的區別便是儒家常說“仁義”,而墨家常說“愛利”。在上述對“仁愛”的分析中我們可知兩家都講愛人,只是在是否要分等級這一問題上有所分歧。而在義利問題上,儒家重“義”,而墨家重“利”。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可見,在孔子看來,“義”與“利”是相互對立的,認為太重功利便無法達到仁義的境界。他將“利”看作是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而將“義”看作是君子才能達到的一種主觀精神境界。而墨子卻將“義”與“利”統一起來,他所謂的仁人義士絕不像儒家那樣脫離實際利益而空講仁愛,而是具體實行“義”的行為[3]37。在墨子看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才是“義”,是實際有利于國家百姓人民的行動所體現出來的。
三、政治觀念上的區別
(一)對于治國的觀念
在治國理念上,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即以“德治”來統領政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可見孔子反對用法治刑罰的力量來統攝百姓,而希望由道德的教化使百姓具備羞恥之心,自覺從善。如何實現道德的教化?就要通過“禮”,用一系列的禮制標準來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以達到以德治國的目的。其實在孔子整個的思想中,我們都能明顯看他的政治立場,他始終都是從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而墨子在治國方針上主張“尚賢”,即崇尚德才兼備的人。“國有賢良之示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他認為選賢任能才是治理好國家的最根本要素,好的國君應該以鼓勵、選拔和任用賢能之士為己任。但是墨子認為的賢者的才能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而獲取的,且不分出身的貴賤、血緣關系的親疏。這與孔子所講的天生具備仁德才能的君子是全然不同的。這也反映出墨家所代表的平民階層要求平等、提高自己的社會政治地位、參與國家管理的強烈愿望。
(二)對于軍事的觀念
在對于戰爭的態度上,孔墨二者都是不贊成的,但是出發點卻有所不同,儒家從道德方面考慮,而墨家從實際利益考慮。
孔子曾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足見他對于軍事戰爭的反對態度。儒家反戰,主要因為其“不仁”。這在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揚中能見其端,“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殺人以求之乎?”(《孟子·盡心下》)由此可見孔孟都認為戰爭非仁者所為。
而墨家反戰,主要因為其“不利”。首先,戰爭太過勞民傷財,荒廢農時,對對戰雙方來說,于國于民都只有壞處沒有益處;其次,在戰爭中雖有少數戰勝者得利,但就整個社會來說,卻是更多人利益的受損。因此墨子也反對戰爭,這在其“非攻”的思想中都有所體現。
四、認識論上的區別——名實之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論語·子路》)這體現了孔子的正名思想,“政者,正也。”(《論語·顏淵》),他認為要解決春秋時代“禮樂崩壞”的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復周禮的權威,而周禮的主要內容即“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等級制、分封制和世襲制”[5]17。據此,孔子提出了正名的具體內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即每個人身在其位,就應該具備這一身份的人所應有的品行,并得到相應的對待。孔子的正名思想主要是從政治角度出發來考慮的,他想通過周禮所規定的等級名分,來糾正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從而挽救依然崩壞了社會秩序。
墨子則將“名實”關系作為一個哲學問題討論。他認為“名”只是一個概念或者說名稱,若只知道概念或名稱,而不懂得從實際上對事物進行選擇區分,就不能夠形成真正的知識。而對于“名”與“實”如何做到相符的問題,墨子確立了“三表法”作為客觀標準,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歷史上的圣王經驗為依據;二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考察人們的直接經驗;三是“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付諸實施,看其是否真對國家、人民和百姓有利。可見墨子認為只有實際經驗才能使名實統一,也體現了身為小生產者階級注重實用性的特點。
五、結語
總的來說,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因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場的不同而產生了很大的差異,而漢代以后儒家思想的盛行以及墨家思想的堙沒,也與其各自所服務的階層脫離不了關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都在那個分崩離析的時代,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社會的問題,這份精神值得后世的我們學習。
參考文獻:
[1]王桐齡.儒墨之異同[M].上海:上海書店,1992.
[2]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
[3]孫中原.墨學通論[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4]錢遜.先秦儒學[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5]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中國哲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