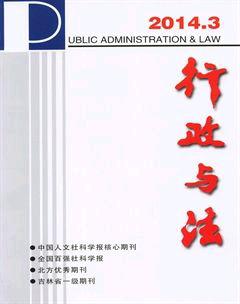“非行政許可”的內涵和性質分析
摘 要:非行政許可的內涵和性質是正確界定非行政許可在實踐中嚴格規范其運行的基礎性問題。行政審批問題具有的復雜性以及行政機關認識能力存在的局限性是導致“非行政許可”內涵難以界定的主要原因。從行政許可的特征及其與非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的關系入手在邏輯上分析可知:非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準予從事除“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或根據其他機關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申請,準予其從事一定的活動。非行政許可中的外部行政行為具有驗證性和確認性,內部行政行為具有權力和職能的分配性。
關 鍵 詞:非行政許可;行政許可;行政審批;行政權力
中圖分類號:D922.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4)03-0083-06
收稿日期:2013-11-26
作者簡介:王禎軍(1973—),男,遼寧大連人,法學博士,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人員,大連行政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憲法、行政法。
一、問題的提出
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以下簡稱《行政許可法》)在定義了“行政許可”的同時,還明確規定該法只適用于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而“有關行政機關對其他機關或者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的人事、財務、外事等事項的審批,不適用本法”,說明《行政許可法》并不調整所有行政審批關系,在行政許可之外仍有其他行政審批存在。依據《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需要,國務院對所屬各部門的行政審批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對“其他行政審批項目”①進行了嚴格審核和充分論證,通過《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的通知》(國辦發[2004]62號)(以下簡稱《通知》)明確了“其他行政審批項目”不屬于行政許可,并用“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一詞替代了“其他行政審批項目”。自此,“非行政許可”作為一個描述“不屬于行政許可的其他行政審批項目”的“規范術語”②而出現。③然而,由于《通知》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加之在國家層面一直沒有專門規制“非行政許可”的法律,非行政許可在實踐中存在設定主體混亂、認定標準不一、項目類別不清、名稱不同和使用不規范等諸多問題。
轉變政府職能是規范行政權力行使的重要途徑。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職能轉變的突破口與抓手。[1]規范和清理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自然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不解決非行政許可存在的問題,不僅影響非行政許可自身功能的有效發揮,并且會使其演變成為消蝕《行政許可法》實施成效的力量,阻礙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在與非行政許可相關的問題中,非行政許可的內涵和性質無疑是正確界定非行政許可在實踐中嚴格規范其運行的基礎性問題。實際上,除行政主體主觀上的原因外,非行政許可的內涵難以界定、性質難以把握也是客觀上導致非行政許可在實踐運行中出現各種問題的主要原因。
二、“非行政許可”內涵難以界定的主要原因
2001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實施意見》(簡稱《實施意見》)。同年12月,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在《關于貫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五項原則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簡稱《幾個問題》)中指出,“《實施意見》所稱行政審批,是指行政審批機關(包括有行政審批權的其他組織)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提出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認可其資格資質、確認特定民事關系或者特定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行為。”“行政審批是行政審批機關作為行政主體對相對人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因此,行政機關對其內部有關人事、財務、外事等事項的審批、決定不屬于《實施意見》所要求清理和處理的行政審批項目范圍”。[2]行政許可法草案基本上沿用了《幾個問題》中的定義。[3]至于《行政許可法》第2條對“行政許可”的定義中未包含“認可其資格資質、確認特定民事關系或者特定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行為”表述的原因,是一些委員和法學專家認為上述表述已包含在“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中,故不需要重復規定。[4](p251)因此可以說,在《行政許可法》頒布之前,《實施意見》所指“行政審批”就是在其之后頒布實施的《行政許可法》所調整的“行政許可”。兩個概念的一致性排除了“非行政許可”存在的制度空間。然而,兩年后《行政許可法》的頒布和國務院出臺的《通知》以及隨后相繼出臺的規范性文件擴大了行政審批的范圍,提出了“非行政許可”的概念,雖然在規范層面確立了行政許可、非行政許可在邏輯上與行政審批的種屬關系,①但也導致了實踐中非行政許可的內涵難以界定的困境,主要是因為:
(一)行政審批問題具有復雜性
在我國,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但無論是在宏觀調控還是市場監管方面,政府的社會管理依然承受著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而政府職能尚未完全轉變、配套制度跟不上來的壓力。在某些領域,如果所有行政審批都像行政許可那樣設定,“就會在較大程度上限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力,減少了它們所運用的行政管理手段和方法,從而影響職能發揮和工作效率,從總體上看是不利于行政管理的。”[5]可以說,非行政許可的產生完全是為了迎合我國現階段社會組織發展不健全,政府管理需要更大的自由裁量權的現實需要。這種在《行政許可法》的嚴格規范下,實踐部門為實現自身權力擴張而另辟蹊徑的做法自然容易引發學界的爭議。因此,相比于傳統行政法理論關注的“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學界對“非行政許可”的關注顯然要少得多。②這種情況必然造成非行政許可制度在建立和運行中缺乏必要的理論論證和指導,并且由于其本身被賦予了將不屬于行政許可的行政審批集一身的“口袋”功能,增加了行政主體在行政審批上的自由裁量權,也加劇了“非行政許可”內涵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現實中一方面表現為行政主體對“非行政許可”內涵界定的“一廂情愿”。例如,從有關方面的意見和國務院的規范性文件中都表達出非行政許可是內部行政行為的意愿,似乎要使之與行政許可保持界限上的經緯分明,但這種愿望中的清晰界分與現實中的務實態度形成雙重標準。事實上,《通知》所羅列一些“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或者屬于行政許可,或者屬于其它的外部行政行為,在實踐中形成了為“處于有效實施監管的現實需要,通過‘非行政許可審批的概念,為一些法律依據位階過低的行政許可繼續存在提供‘依據”[6]的現象。另一方面,“非行政許可”內涵的不確定性也導致不同行政主體對非行政許可內涵界定的相互矛盾。例如,《深圳市非行政許可審批和登記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非行政許可審批和登記包括:行政機關對其他行政機關或者其管理的事業單位的人事、財務、外事等事項的審批(行政機關內部審批);而《大連市非行政許可審批管理辦法》第3條則明確將上述行政機關內部審批事項排除在管理辦法之外。此外,“非行政許可”內涵的界定不可避免地取決于“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的內涵的明確。然而,一方面,在“在行政法上,‘行政許可無論在內涵還是在外延上都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爭議頗多的概念”,[7]盡管《行政許可法》界定了行政許可的內涵,它畢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單行法典的形式專門而統一地規范行政許可行為的法律。由于沒有其他國家現行的經驗可供借鑒,再加上立法技術本身的局限,使得“它只能在現有實踐和研究的基礎上作非常概括性的原則規定,不能為各類具體情況提供詳盡的答案,具體判斷仍需要由許可的設定機關來確定。”[8]例如,《行政許可法》用第12條“可以設定行政許可的事項”與第13條“可以不設定行政許可的事項”分別來界定行政許可的事項范圍,最終造成的結果使界限依然模糊不清。因為“可以設定的事項”意味著“可以不設定”;而“可以不設定的事項”又意味著“可以設定”。另一方面,政府社會管理工作的紛繁復雜客觀上加劇了“行政審批”內涵的復雜性,這就必然導致先界定“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的內涵,再界定“非行政許可”內涵的設想在實踐中很難實現。
(二)行政機關認識能力存在局限性
因理論界對非行政許可的存在尚存在爭議,“非行政許可審批”迄今為止并沒有成為一個正式的和被理論界普遍認可的法學概念,也沒有成為在國家層面獲得法律、行政法規認可的法律概念。但是,國務院的規范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規章卻不失“著意”地為其留足了繁衍空間,形成了“非行政許可”的內涵更多依靠實施機關界定的局面。如前所述,從《行政許可法》頒布之初,實務界普遍認為行政許可就是所說的“行政審批,是行政機關依法對社會、經濟事務實行事前監督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①到有關方面的意見和國務院《通知》都推翻了《幾個問題》將內部審批事項排除在行政審批項目之外的規定,將內部審批事項歸入到非行政許可項目中,這些變化充分表明:由于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持,對于完全產生于我國當前行政管理現實需要的“非行政許可”這一新鮮事物,行政主體本身需要經歷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這也在客觀上造成了對“非行政許可”內涵認識上的不同。另外,行政審批制度的目的是要規范行政許可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的設定和實施,約束行政主體的權力。由于非行政許可往往使行政機關享有恣意裁量的余地,可以規避行政許可的公正、統一使用,保護行政主體的既得利益和特殊利益,行政主體在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設定上的受益者地位決定了他很難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客觀、準確地界定非行政許可的內涵。例如,《行政許可法》明確排除了國務院部門規章有設定行政許可的權力,同時,《行政許可法》第l7條明確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地方性法規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章外,其他規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設定行政許可。國務院以《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簡稱《行政許可決定》)的方式將在《行政許可法》實施之前由法律、行政法規之外的規范性文件所設定的500項行政許可保留下來。[9]不可否認,一些審批項目的保留確實是一些行政管理部門履行行政管理職能所必需,但畢竟在數量上,“以一個決定的形式一次性設定幾百項行政許可,實屬罕見”,[10]而隨后國務院陸續出臺的取消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均涉及到《行政許可決定》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的結果也表明,一些行政審批項目之所以在當時得到保留,難免是出于一些行政部門的利益考慮而非現實需要。相應地,現實中出現 “《行政許可法》在嚴格規定了許可的項目后,一些部門為了逃避該法的約束而千方百計地將許可項目改頭換面以保留部門的許可利益。……不少部門想方設法將原來的‘許可項目轉為‘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以規避《行政許可法》的約束”的現象也很好理解。[11]應當說,在缺乏國家層面的法律、行政法規規范的情況下,行政主體與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設定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決定了行政主體很難客觀、準確地界定非行政許可的內涵。
三、“非行政許可”內涵的邏輯分析
“非行政許可”的內涵是其本質屬性的總和,是“非行政許可”概念的重要內容,決定著“非行政許可”外延的大小。單純從“非行政許可”的構詞分析,“非行政許可”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是一種“非行政的許可”,即,一種不屬于行政法調整的許可行為;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不屬于行政許可”。由于人類個體認識能力的差異以及對概念的使用目的不盡相同,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同一概念可能會具有不同的含義。分析事物的內涵首先必須正確確定概念所存在的語言環境。因此,作為在行政法(行政審批)語境下的“非行政許可”只能理解為是一種“不屬于行政許可”的行政審批。如前所述,“非行政許可”的內涵與“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的內涵有著必然的聯系。具體而言,如果單純從非行政許可自身的特征確定其內涵,它的內涵應是“行政審批”去除“行政許可”后的剩余的所有行政審批的本質屬性的總合。但是從行政法上看,“如果以審批的主體和審批的形式作為界定行政審批行為標準的話,那么行政審批在行政法上就不是單純的一類行政行為,而是一個包括了行政許可行為在內的諸多行政行為的結合體,”[12]這就注定了非行政許可必定是從這一結合體中去除行政許可后余下的各類行政行為的結合體。由于非行政許可并不屬于單一的行政行為,對其內涵的界定,難以從其自身的特征出發分析歸納其屬性,只能結合非行政許可與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的關系,從行政許可的屬性入手對非行政許可的內涵進行邏輯判斷。
盡管“行政許可”的內涵在行政法學上仍存爭議,[13]但從《行政許可法》明確將其定義是“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來看,“依申請”,“申請方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外部行政行為)、“準予從事特定活動”是行政許可必須具備的三個屬性。由于行政審批是一種依申請的行為,可以說,在行政審批中凡是沒有同時具備上述三項屬性的行政審批就是非行政許可。因此,從排列組合上看,非行政許可包含以下幾種情況:
[屬性
行政許可\&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準予從事特定活動\&行政許可\&√\&√\&非行政許可\&√\&×\&×\&√\&×\&×\&]
在行政審批語境下,根據《行政許可法》第3條第2款的規定可知,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相對立的申請主體是“其他機關或者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特定活動”的范圍就是《行政許可法》第12條規定的內容。①因此,非行政許可就應當是行政機關:⒈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準予從事除“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如暫住證核發、車輛進京通行證核發等;⒉根據其他機關或者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申請,準予其從事一定活動的行為(包括“特定活動”及其以外的活動),如廣播電臺、電視臺開辦群眾參與的廣播電視直播節目審批、國家正式開展的體育競賽項目立項審批、中央國家機關所屬事業單位依照公務員制度管理審批、中央國家機關行政用房建設項目審批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非行政許可的內涵遠比有關方面的意見和國務院《通知》中表述的“主要是政府的內部管理事項”寬泛。國務院《通知》所保留的211項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根本不限于行政機關內部管理事項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②非行政許可所具有的寬泛的內涵是在行政審批內行政許可之外允許“非行政許可”產生的客觀存在。
四、“非行政許可”的性質
非行政許可是包含不同種類行政行為的結合體,其性質也表現為不同種類行政行為所具有的不同性質,主要表現為:
(一)驗證性和確認性
在行政法上,雖然“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都有平等擁有的機會,但在事實上,只有符合法定條件和標準的公民才能享有行政法上的權利。之所以會出現通過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予以保護的行政法上的權利,主要是由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政府保障權利實現能力的有限性決定的。”[14](p41)依據法治行政原則,行政法上的權利主要應當由議會制定的法律來加以規定。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依據申請,通過行政主體的行政許可使行政相對方依法獲得行政法上的權利。“從形式上看,未經行政主體的許可,行政相對方不具有從事某種活動的資格或者不得實施某種行為,而行政許可則賦予了行政相對方相應的資格和權利,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行政許可具有賦權性;另從實質上分析,行政相對方之所以不具有某種權利和資格,這是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結果,而在沒有法律、法規的限制之前,這些事項是公民已經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行政許可又具有解禁性。可以說,行政許可的性質并不單一,具有雙重性。”[15](p81)行政許可和非行政許可同屬于行政審批,并且相互之間呈互補關系,非行政許可中的外部行政行為,即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準予從事除“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必定不是鑒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政府保障權利實現能力的有限性,而是國家一般限制或禁止的活動。①也就是說,非行政許可中的外部行政行為不是建立在普遍限制和禁止基礎上的解禁行為。對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從事的“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行政主體進行的不應當是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申請的事先審核,而只能是對行政相對人從事 “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的事實、關系或資格的驗證和確認。非行政許可具有的驗證性和確認性使之和行政許可相比,由于不用受到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政府保障權利實現能力的有限性的影響,在外延上更廣泛;并且,由于非行政許可更能夠適應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區呈現出的個性化、民族性、區域性等差異化特點,②其設定和實施更為靈活,行政機關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③正因為如此,非行政許可較之行政許可在實踐中更容易被濫用,也決定了從社會管理職能角度來說,非行政許可是“在市場機制健全、社會自治力較強的情況下,政府根據國情和民意,可以選擇自己行使或者讓渡給市場和社會行使的職能。”[16]
(二)分配性
從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上看,“行政機關根據其他機關或者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申請,準予其從事一定活動”的非行政許可應當屬于一種內部行政行為。有學者也指出,“行政許可是一種外部行政行為,它建立在行政主體與社會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外部相對人)之間的關系上;而行政審批有部分屬于外部行政行為(這部分可能與行政許可重合),也有部分屬于內部行政行為,如行政機關的內部審批關系,而內部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許可。”[17](p247)通過本文關于非行政許可的內涵得出的結論:行政審批既包含屬于外部行政行為的行政許可,也包含同樣屬于外部行政行為的“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準予從事除‘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的非行政許可,還包含屬于內部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根據其他機關或者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申請,準予其從事一定活動”的非行政許可正好契合了學者的觀點。另外,從“非行政許可”一詞產生之日起,有關方面的意見和國務院《通知》都強調其“主要是政府的內部管理事項,不屬于行政許可”,并且在《通知》保留的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和一些地方設定的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中④確實包含了一些政府的內部管理事項。根據有關內部行政行為的事務管理標準說,行政機關內部管理事務的行為是內部行政行為。從政府管理職能上說,屬于內部行政行為的非行政許可體現的是政府的自我管理,實質上是政府管理職能的內部協調與分配。從行政權力角度說,屬于內部行政行為的非行政許可體現行政主體內部的權限分配,與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直接影響的外部行政行為不同,同時,諸如國務院《通知》保留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全國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總量、本科生招生總量及部分地區分部門招生計劃”、“企業基本養老保險事項”等許多非行政許可的審批也與法律效果只及于行政機關內部的傳統內部行政行為不同,它可能會對行政相對人的權益產生間接的影響。正因如此,無論從完善政府管理職能還是從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利益上說,都不應使這種屬于內部行政行為的行政審批游離于制度調整之外,而應將其嚴格規范,這既有利于政府職能分工、權力分配的規范性,也有助于對行政相對人權益的保護。
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是簡政放權,簡政放權的核心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是規范行政許可和非行政許可。非行政許可在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說明,規范非行政許可不僅關系其自身功能的發揮,也關系行政許可制度的順利實施乃至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順利開展。明確非行政許可的內涵和性質是規范非行政許可的前提。結合非行政許可與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的關系,從行政許可的特征及其與非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的關系入手,在邏輯上分析可知:非行政許可是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準予從事除“特定活動”以外的活動,或根據其他機關或者對其直接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申請,準予其從事一定活動。非行政許可中的外部行政行為具有驗證性和確認性,內部行政行為具有權力和職能的分配性。從完善社會管理的意義上說,對于非行政許可寬泛的內涵,人為地將其縮小,只能造成理論與實踐的不統一,規定與現實的矛盾,滋生和加劇非行政許可制度實施中的亂象。解決非行政許可制度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的前提是要在理論上正確把握非行政許可的內涵和性質,合理確定非行政許可的外延,在此基礎上,充分考慮包含《行政許可法》第13條在內的各種因素,結合實踐的需要,嚴格規范非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
【參考文獻】
[1]李克強.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職能轉變的突破口與抓手[EB/OL].http://news.china.com.cn,2013-05-15.
[2]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關于貫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五項原則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M].2001.
[3][6]周怡萍.非行政許可審批內涵芻議[J].人大研究,2010,(10).
[4]喬曉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及解釋[M].中國致公出版社,2003.
[5][16]朱鴻偉,杜婭萍.非行政許可審批的合理性[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1).
[7][13]王克穩.我國行政審批與行政許可關系的重新梳理與規范[A].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問題——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6年年會論文集[C].
[8][11]楊建生.行政許可法實施中的問題、原因及對策[J].理論探索,2007,(01).
[9][10]沈福俊.國務院決定行政許可設定權:問題與規制[J].社會科學,2012,(05).
[12]王克穩.我國行政審批與行政許可關系的重新梳理與規范[J].中國法學,2007,(04):60.
[14]莫紀宏.國際人權公約與中國[M].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15]皮純協,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教程[M].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
[17]胡建淼.行政法學[M].法律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徐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