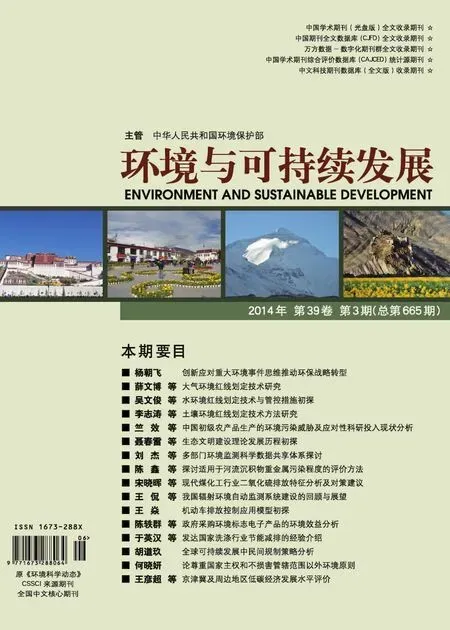區域特色農產品綠色發展現狀及對策—以臨安市山核桃為例
(浙江農林大學法政學院,杭州 311300)
“綠色農業產品的開發和生產要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以全程質量控制和管理為基本指導思想,其目的是通過生產綠色農業產品,提高食品質量安全水平,保護、改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通過消費綠色農業產品,增進人們的身體健康,以達到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賦予新的內涵的目的,創造新的‘增長點’。”山核桃產業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我國林業生態環境惡化造成了每年數百億的經濟損失,”因此生態發展迫在眉睫。島石鎮、龍崗鎮、清涼峰鎮是臨安市山核桃的主產區,本文以這幾個地區的山核桃綠色發展為例,進一步探討區域特色農產品該如何實現綠色發展。
1 生產、加工環節存在的環境問題
1.1 林種結構單一化
“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保護森林、發展林業若干問題的決定’,從而圍繞山權林權,開始了以‘穩定山林權,劃定自留山和確定林業生產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林權改革,廣大農戶獲得了自主經營的山林。”據調查資料顯示,龍崗鎮全鎮在70、80年代依林業局的要求在山上大面積種植用材林,例如松木、杉木等。到1983年分田到戶后,有40%的用材林轉為經濟林,而轉為灌木、喬木等闊葉林的很少。目前,龍崗鎮2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幾乎沒有闊葉林。龍崗鎮不同村的林種結構區別較大,有的村80%以上都是山核桃林,有的村山核桃林占總林地面積的50%左右,也有個別村山核桃只占總林地面積的20%左右,但是整個鎮總體是以經濟林—山核桃林、竹林為主,除了經濟林之外,還有部分的生態公益林,包括用材林、闊葉林等。
結構良好的森林植被可以減少水土流失量的90%以上。由于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大量的森林樹種都被山核桃樹替代了。此外,為了便于山核桃的采摘和拾果,山核桃樹下很少有灌木,從而造成了林種結構的單一化。而且這些地區除了山核桃林之外就是大量的竹林,而竹子本身涵養水源的功能就比山核桃樹差,導致在雨量較大的時候,林地土壤來不及吸收水分,呈現一種飽和狀態,產生坡面徑流,造成水土流失。同時,山核桃在秋冬季節會有落葉過程,竹葉對雨水的截留功能比較欠缺,這幾個地區的灌木、喬木林所占比例小,從而大大減小了土壤的攔蓄量,難以將地表徑流轉化成地下徑流,極大地降低了水源的涵養能力。除了水源涵養能力差,林種結構單一化也會帶來生態系統脆弱的問題。
1.2 農業投入品的濫用
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山核桃的品質問題、蟲害問題,影響水土保持導致農村面源污染。山川村、桃花溪村、順溪村這幾個村在山核桃種植過程中都普遍存在農藥、化肥的不科學使用問題。化肥的大量使用,會產生一些新的病菌,導致蟲害問題更加嚴重。“常見蟲害有山核桃天社蛾、山核桃蚜蟲、胡桃豹夜蛾、天牛類,近年還出現一些新的蟲害,如山核桃花蕾蛆等。”另一方面,草甘膦之類的農藥、復合肥等多類品種化肥的濫用也引起了生態的變化,污染了周邊的環境。
施肥雖然可以帶來較高的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但是不同品種肥料的大量使用也帶來了危害,例如產生病菌導致病蟲害的大量產生,影響山核桃本身的品質。由于農村沒有明確的排污口,主要借助降雨或排水將地表存留的有機物、肥料、農藥等帶入水體,容易引起水體污。此外,種植業、畜牧業的集約化程度不斷提高,客觀上帶來了化肥、農藥等農用外部投入品使用量的增長以及畜禽糞便、秸稈等農業廢棄物的增加。同時,由于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長期滯后,日益增多的農村生活垃圾、生活廢水不能得到及時、有效處理。這些問題都給農村生態、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
1.3 加工過程存在問題
臨安市山核桃加工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山核桃主產區,而且每年的加工時間都集中9、10月份,由于加工的量比較大,加工企業集中,盡管大部分企業都配備了污水處理設施,還是避免不了對周邊的水、空氣造成污染,出現環境問題。另一方面,由于市場對山核桃的需求量大,消費者對山核桃的口感要求提升,導致企業在加工山核桃時過量,甚至違法使用添加劑,從而引起食品安全問題。
2 引起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2.1 農業政策制定不完善
在農產品的綠色發展中,政策引導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關于農資補貼與農業補貼的政策在環境保護功能上相背離。在對山核桃的生產管理中,林農能夠輕易獲得不同種類的化肥、農藥,在利益的驅使下,農藥、化肥的濫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環境污染。除此之外,缺乏明確的獎勵機制、懲罰機制、評估監督機制。對符合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農資要進行補貼,但對于違背生態理念、造成環境污染的農業行為也要進行懲罰。
此外,考慮到經濟效益,臨安市山核桃主產區的林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面積種植山核桃樹,放棄了用材林的種植。地方政府出于經濟增長等因素,鼓勵大面積種植經濟林,從而使得這些地區的林種結構出現單一化,在干旱、降雨季節無法達到涵養水源的目的。
2.2 利益相關者法律意識淡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更加看重經濟效益。為了獲取高額的利潤,不惜采取種種手段(超量噴灑農藥、濫用化肥、違法使用添加劑等),從而導致嚴重的農產品質量問題。生產者法律意識淡薄主要表現在不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有的甚至在利潤驅使下故意違法違規。例如農民在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過程中不按照《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農藥管理條例》、《農藥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的規定,沒有做到科學、合理、適量地使用農藥,出現亂用、濫用違禁藥品的現象,造成農產品農藥殘留。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民本身的法律意識不強,在農村地區法律的普及程度不高,再加上農民的文化程度低,不懂法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守法的尷尬局面。當然,造成這些問題并非全是不懂法,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知法犯法,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大多數人選擇了僥幸。如在山核桃的生產過程中,林農明知化肥和農藥的大量使用會導致周圍環境的污染,但是由于農村的環境污染防治工作做得不夠到位,在污染發生時難以確定具體的責任人,相關環保部門的執法力度薄弱,從而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環境問題。在這種守法難、執法不嚴的氛圍下,農產品的生產環境得不到安全保障。
此外,大部分消費者在受到農產品質量侵害后,選擇了忍氣吞聲;部分消費者想找相關責任人卻不知究竟找誰;有些消費者選擇向行政主管部門投訴,但在久投無果后也就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在于大量的消費者不知、不善于利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2.3 相關法律、制度的缺位
目前我國相關農產品的法律法規存在與市場經濟發展現狀不相適應的地方。現行的《產品質量法》是將初級農產品以及僅經初步加工的農產品排除在外的,法律規制的漏洞更是增加了農產品生產環節管理的難度。另外,“農產品與食品質量安全的法律體系松散,抽象而難以具體操作,原則而不夠規范”。如《農藥管理條例》的核心內容局限于農藥在生產、經營和使用方面的管理。對于已經登記的農藥品種投入使用以后對生態環境是否造成污染,對人體是否造成危害,以及現有的對生態環境和人體造成污染和危害的農藥品種如何進行有效監督管理則很少涉及。
農產品的綠色發展不僅包含對環境資源的保護,也涉及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問題。但是在我國《民法》、《刑法》、《環境保護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法律中缺乏關于農業生產造成環境污染的具體民事、刑事、行政責任,如《環境保護法》僅第四十四條間接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礦產、漁業、野生動物、等資源的破壞的,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承擔法律責任。”同時,還缺乏產地環境保護生態補償制度、農業生產環境污染責任追究制度等。
3 促進區域特色農產品綠色發展的對策
3.1 調整農業補貼政策
通過制訂與國情相吻合的農業環境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和農業生態環境質量最低標準指標體系來提高農業生態補貼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十分必要。優化我國農業補貼結構,在補貼的同時不能與生態循環、環境保護的理念相違背,停止對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等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廠商補貼并提高稅率,各地區政府應該提倡少用化肥、農藥和除草劑,鼓勵農民多用農家肥料、生物農藥和機械(或人工)除草。
除了調整農資補貼政策,地方政府應采取相應的措施,出臺改變山核桃林布局的政府補貼政策。由于山核桃樹的葉子在冬天時會全部凋零,如果山核桃種植面積廣,一到冬天就會造成一種荒山景象。如何把“荒山”變成“綠地”?主要做法就是在山核桃林中種植油菜、黑麥草、油茶等,在山腰種植適當寬度的灌木林作為水土保濕帶,而種子的購買、播種和灌木林種植都應該由當地政府資助。
3.2 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立法體系
農產品質量的保證是其綠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立法還未形成科學的體系,系統性和完整性均顯不夠。”我國有針對性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專門立法主要是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及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法律效力略顯不足。自2006年《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出臺后,與其相配套的實施條例始終未出臺。且該法實施后僅頒布了1部相關行政法規,新頒布8部行政規章。同時,有些法律條款已多年未進行修改,當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過程出現不同的安全問題時(例如上文提到的山核桃生產過程中過量使用農業投入品問題,加工過程中違法使用添加劑問題等),原有的法律法規就適應不了變化的新情況。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立法體系至少要包括農產品質量監管法與農產品質量責任法兩方面內容,以免陷入執法難與責任不明的尷尬境地,這樣不僅能事先預防,事后補救,也能夠明確生產者的生產標準要求和違反該標準所應承擔的責任。
3.3 確立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相關制度
3.3.1 確立產地環境保護補償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等均對生態補償提出了要求,“生態補償的實質就是通過一定的政策實現生態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農戶在進行農業生產時遵循優質、高效、安全的原則,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采用清潔生產技術,確保農產品生態安全,實現循環利用的生產模式。國家則可以在測土配方施肥、發展綠色農產品、建設生態農業等方面實行重點補償。
3.3.2 確立產地環境污染責任追究制度
“農業產地環境的好壞是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優劣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國農產品產地污染包括產地環境污染源: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氣污染等;產地環境污染物:農藥、化肥、農用殘膜、畜禽排泄物、重金屬等。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多、地廣、分散,農民為了追求高產、便利容易導致環境污染,農戶間缺乏相互監督且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的執法力度弱,使得產地環境污染的責任更難以追究。因此,針對農產品產地環境污染的現狀,筆者認為應建立村民代表監督制度,根據村落的大小和農業生產規模的不同,每村由村民推薦或者選舉1—5名村民作為環境監督代表對該村的農業生產進行監督,并將具體的生產情況實時記錄在檔案中,每月或數月在村中公開并向鄉鎮農業主管機關備案登記。對于造成農產品產地環境污染的生產者或其他企事業單位、個人,根據主觀意識的不同:區分故意、重大過失、一般過失和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害的不同:污染面積大小、修復難度、經濟損失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參考文獻:
[1]黃鸝.綠色農業發展簡論[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4:146.
[2]梁和英.林業生態建設與發展的對策[J].綠色科技,2011,7:171.
[3]呂秋菊.山核桃產業的發展過程、動因及展望[J].浙江農林大學學報,2012,2:99.
[4]胡麗華.山核桃病蟲害的生態防治技術[J].現代農業科技,2010,12:168.
[5]陳彥彥.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制度研究[M].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8,7:118.
[6]劉慧萍.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規制及保障機制構建研究[M].中國農業出版社,2013,6:91.
[7]蘇芳.生態補償方式對農戶生計策略的影響[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3,2:58.
[8]宋啟道.農業產地環境污染與農產品質量安全探討[J].農業環境與發展,2008,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