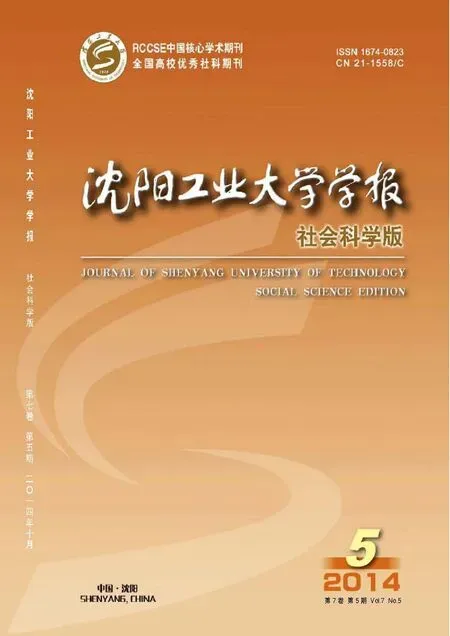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理論來源新析*
葉冬娜
(福建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福州 350013)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理論來源新析*
葉冬娜
(福建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福州 350013)
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思想有其深刻而豐富的思想理論來源,其主要來源于達爾文的進化論、李比希的農業化學思想、摩爾根的人類學、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尤其是在對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及費爾巴哈人本學舊唯物主義自然觀多重吸收與改造的基礎上,創造性地變革了自身的生態思想體系。
馬克思; 恩格斯; 生態思想; 辯證法; 進化論; 唯物主義; 唯心主義; 人類學; 人口論
對于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備生態思想體系這一問題,西方及國內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總的說來,國內學術界大都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論體系中蘊涵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并對其生態思想進行了努力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大多數西方學者往往否認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思想,如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本·阿格爾就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屬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問題的論述,而對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并沒有留下理論的空間,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論述對于今天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完全失效。這是因為阿格爾沒能很好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理論來源。學術界也存在相同的問題,相較于對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理論來源的研究,學術界關注更多的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文本的挖掘,造成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思想不能被科學正確地理解并應用于指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中。
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思想是在承襲和擴展達爾文的進化論、李比希的農業化學思想,批判和反思摩爾根的人類學、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揚棄和創新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費爾巴哈的人本學舊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礎上,完成對自身生態思想的理論構建的。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李比希的農業化學思想的承襲和擴展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第一次以全新的進化論思想顛覆了傳統的神學目的理論和簡單的物種不可變理論,建立了科學的生物學基礎。他的進化論思想的中心問題,一是自然界的生物通過繁衍和變異帶來的進化問題,二是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動力引起的生物進化問題。
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強調生物界所有物種的動態可變過程,堅持生物進化的自然選擇根源,掀開了長期籠罩人們思想的關于自然領域內所有物種都是根據某種目的機械地復制出來的、萬事萬物不可逾越的神秘面紗。1866年,德國思想家恩斯特·海克爾在《普通有機體形態學》一書中,依據達爾文物種進化和自然選擇的觀點創造性地發明了“生態學”一詞,將生態學的研究等同于對各種有機物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初步形成了生態學的思維方式。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與自然界、社會歷史發展與自然歷史發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它們都統一于人類勞動的實踐活動。對自然歷史的考察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個是自然相對于人而言的生成過程,另一個是人類改造自然的勞動過程。探求當代生態危機的解決路徑,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需要研究被人類的勞動實踐所覆蓋的自然領域,同時也要探索人類社會領域的自然同化,即通過人類的勞動實踐活動來改造社會的各個領域尤其是生產領域的反生態性,實現人與自然在勞動基礎上的和諧共存,拋棄建立在異化勞動基礎上的人與自然的異化關系。
德國農業化學家李比希于1840年出版《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上的應用》一書,通過分析植物生長過程中土壤的營養物質所起的重要作用,表達了他的理性農業思想。該著作關注了19世紀歐洲和北美資本主義社會土壤貧瘠的根源,探討了土壤肥力和土壤化學的聯系,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反生態農業制度與城市污染問題,指出人類和動物的生活生產排泄物不能有效地匯集與返回土地造成了土壤肥力的日益枯竭,而從根本上解決土壤貧瘠問題,需要確立以歸還為準則的理性農業。馬克思恩格斯在李比希理性農業思想的影響下,創造性地提出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斷裂”的觀點。“物質變換”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40年代,德國生理學家最初用該概念顯示人類身體內部和呼吸相關的物質變換。此后,李比希將其概念普遍化并且在1842年出版的《動物化學》一書中將其應用于“生機論唯物主義”分析方法。從這時起,“物質變換”這一概念便開始被廣泛地運用于考察生物化學過程中有機體和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受到李比希物質變換概念的分析方法啟發,不僅在生態學意義上使用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及能量交換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將其進一步應用于更為廣泛的社會意義上,描述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及社會條件下再生產出來的扭曲的彼此依存的異化關系及需求。從馬克思恩格斯“物質變換”概念的生態學及社會學兩種意義上可以看出,他們所闡述的“物質變換斷裂”觀點既揭露了人類與自然互相對立的生態矛盾,又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社會制度中所存在的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導致的自然異化現象。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認為建立在資本主義城鄉敵對分工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不可持續性,造成人和土地之間出現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對此,馬克思恩格斯開始洞察到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與工業的生產對土地的剝削,導致土壤肥力下降,使工人日益走向貧困。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離不開土地的給養,人類的食物供給需要土地的培育,人類生產的初級資料來源于土地上的農業作物。土地一旦失去活力,哪怕是一小部分的掠奪也會對人類造成不小的影響。正如馬克思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3]579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的“物質變換斷裂”理論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可持續性同后代人需求之間的矛盾問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傳給后代。”[4]878資本主義私有制忽略了自然的使用價值,而一味地尋求實現交換價值即利潤的最大化,導致了資本對土地的占有,破壞了代際公平,使得后代人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然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強調的不僅是自然對財富的貢獻,而且肯定了人類勞動讓自然界重獲新生。因此,在李比希農業化學思想的影響下,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思想不僅具有生態學的意義,而且具有社會學的意義,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通過勞動而進行的物質和能量變換的生態關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制度及生產方式條件下被異化的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和因此而引發的關于人的自由的探索。
馬克思恩格斯在其基礎上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城鄉敵對分工與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可持續性,認為這勢必招致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關系的斷裂。他們指出,人與自然之間合理的物質變換過程不僅應當表現在人類生存與發展所耗費的自然資源以維持自然物質循環的形式有效返回自然界,并且必須提供勞動者自身自然即身心健康所必備的物質保障。“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就破壞了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5]579
馬克思恩格斯在李比希農業化學思想的基礎上,闡述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下人與土地的物質變換是以雙重破壞的形式呈現出來的,既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又破壞了人們的健康。因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未來的理想社會必須建立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反生態本性的基礎上,通過采取消滅城鄉敵對分工、實行合理的人口分布、主張工業和農業的緊密聯系、復原與改良土地的營養物質、應用科學技術與工業手段等具體措施,合理地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二、馬克思恩格斯對摩爾根的人類學、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批判和反思
馬克思恩格斯對摩爾根的人類學理論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尤為重視。馬克思在1881—1882年研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并對其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理論的唯物主義歷史學研究方法表示了高度的贊賞;同時,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稱贊摩爾根的偉大功勞不僅是在于“他在主要特點上發現和恢復了我們成文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團體中找到了一把解開希臘、羅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6]2-3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所闡釋的人類的“生存技術”,運用唯物主義歷史學的方法將人類社會劃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發展階段,由此意識到隱藏在摩爾根所闡述的“生存問題”背后的深刻含義,即對待此問題所采用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的相互聯系。正如摩爾根所言,對生存技術的關注從人類與自然協同進化的意義方面而言包含著深刻的生態學寓意,人類歷史是通過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人口的再生產兩種“生存技術”的轉變表現出來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的這兩種生存技術不能離開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這兩個環境,人類在這兩個環境中開展著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人口的再生產這兩種“生存技術”的生產。一方面,人類是大自然的產物,是在自然界中不斷進化發展著的;另一方面,“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7]56人是自然環境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并通過這兩種“生存技術”的生產活動形成了人與自然環境及人與社會環境的雙重制約關系,同時也在這兩種“生存技術”的生產活動中深化與促進這兩種關系的進展與變動。不管是通過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進行個人生命的繁衍,還是通過人類自身人口的再生產手段實現他人生命的再造,都會即刻呈現出雙重關系:一個是自然關系,另一個則是社會關系。這兩個環境通過“兩種生存技術”的實踐活動成為相互融合、有機統一的動態系統,將人與自然及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和諧地統一起來。這種統一的標準及價值尺度不論是過分夸張“兩個環境”的意義,抑或過度夸大“兩種生存技術”的實踐意義都是片面的,它們應該是通過諸種要素之間所存在的客觀基礎性與實踐能動性的實際效果而顯現出來的。
此外,馬克思恩格斯對摩爾根有關“人類已能夠達成對食物的完全控制”的論斷進行了批判,認為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矛盾將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生態矛盾一直持續下去,甚至比資本主義更為持久,除非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讓人們普遍意識到人類與自然之間共同發展的和諧關系。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起源和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也為他們的唯物主義原則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馬爾薩斯1789年出版的《人口論》的基礎上進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人口理論。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資本的掠奪性及存在人口過剩的事實;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對馬爾薩斯人口論所主張的通過采取貧窮、災難、疾病等積極抑制人口的手段及不婚不育、禁止結婚等預防抑制人口的手段,對人類進行簡單、粗暴、嚴酷、卑鄙的反生態的人口管控,進行了強烈的指責。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首先是“非歷史的”單純的數量關系,同時也是永恒的絕對抽象物,不隨任何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并且普遍適用于一切時間地點。其次,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將人口過剩視為所有犯罪和貧窮的源頭,把生活資料等同于就業手段,混淆了就業手段方面的人口過剩與生活物質資料方面的人口過剩,從而未能真正揭示資本主義人口過剩的癥結。最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無限發展,過度強調自然資源的有限性。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口數量的增減歸根結底決定于社會歷史的前提和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條件下人口過剩取決于過剩的財富、資本和地產,并非馬爾薩斯人口理論所宣稱的人口過剩是由絕對的生活資料的匱乏所導致的,因此,人口過剩在不同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上是相對的。在駁斥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過程中,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人口的形成狀況及生存處境,說明了在人口城市化遷移過程中所導致的人與自然環境的異化,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的定義。“不享有任何特權的無產階級集所有罪惡于一身,它生活在一種極端貧困的狀態。”[8]11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以自動機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著作用,用它們的輪子碾壓著工人。”[2]428人口過剩實為資本對人口的掠奪,是資本主義社會追求剩余價值的必然結果,并非馬爾薩斯宣稱的自然法則所導致的。恩格斯認為:“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只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9]466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進一步清晰地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日益擴大規模生產促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5]727-728可見,人口過剩是社會歷史的概念,不存在永恒不變的人口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口過剩是資本家過多地投資生產機器、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降低勞動力的價格,造成工人失業,形成了大量工人產業后備軍的相對人口過剩。
就解決人口過剩的方法路徑,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過“兩種生產”統一的理論來協調人口過剩與生活資料之間的矛盾。而“兩種生產”又受到勞動發展階段及家庭發展階段的雙重制約,所以人口的生產與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辯證統一的關系。解決人口過剩一方面可以運用科學技術的進步來逐漸地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物質生活資料;另一方面則可以實施道德教育,讓群眾自覺控制生育,從而保持人口數量與生活資料的動態平衡。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將人類文明發展與自然極限統一起來,并且強調自然極限不僅來源于馬爾薩斯所謂的自然極限要素,而且來源于社會及技術的具體的歷史因素。人類與自然資源的矛盾解決必須結合對自然、科學技術、社會等多元因素的考察,不能只考慮單一的因素。
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價值理念,首先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物質前提下的,把物質層面生產力的發展提升至人類精神解放的層面,使人的內在尺度與外在尺度相統合,能夠在人與自然的勞動生產實踐中自覺認識及運用自然規律,感受自然的美,從而向人類創造自然美的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靠近。其次,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產主義構想需要建立在承認物質的歷史環境制約的前提下,正確認識自然規律去更多地改造自然界,而不是被動地適應自然,從而透出在自然生態關懷基礎上對于人類全面發展的終極關懷,真正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解放戰略。
三、馬克思恩格斯對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費爾巴哈的人本學舊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揚棄和變革
作為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把自然界理解為“絕對精神”外化的產物,人也只是自我確證的手段,人與自然都只不過是“絕對精神”自我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和環節,這便是黑格爾對待人與自然的基本態度。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意義在于他肯定了人的思維與活動結果的無限性,將對象性、現實真正的人看作自我勞動的能動發展過程,不僅肯定了作為一切運動與生命力根源的矛盾,而且承認了矛盾存在的必然趨勢。他把整個自然界看作各個階段矛盾的對立及其相互克服,從而實現從一個階段產生另一個階段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將整個自然界描繪為永恒發展與所有運動的統一。
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歷史局限性進行了批評,認為黑格爾唯心主義體系中的人與自然是抽象的絕對精神的自我喪失。針對黑格爾“頭足顛倒”的自然觀,馬克思恩格斯尖銳地批評道:人類作為自然的對象物,之所以只能設定自然對象物,是因為人類來源于自然界,需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保留了黑格爾哲學方法的辯證的革命部分。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首次將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用普遍適用的形式表達了出來。”[2]316可以說,“現在,整個自然界是作為至少在大的基本輪廓上已得到解釋和理解的種種聯系和種種過程的體系而展現在我們面前。”[2]306正是通過對黑格爾辯證法“合理內核”的汲取與對唯心主義體系的批判,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才成為永恒流動的,并且成為與人類的精神能動性相關的存在物。只有通過人類改造的“人化自然”才是直接與人類存在物相適宜的存在,變成人的物質及精神產品。
費爾巴哈的人本學舊唯物主義自然觀在一定意義上是在與黑格爾的人和自然觀的斗爭中產生的。他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肯定“感性的人”以及“感性的自然界”,認為人是大自然的產物,大自然是人的感性生活的基礎,確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然而,費爾巴哈眼中的自然界與人僅僅是“感性直觀”的存在物,因此他不能正確地理解處于社會實踐中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僅僅提出了“人是環境的產物”,卻忽視了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也同樣作用于環境。費爾巴哈不能正確理解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感性的基礎,祈求通過設立愛的宗教實踐來改變社會的不合理現狀,最后在歷史觀中也如同黑格爾一樣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沼。最終,他們都僅僅在表面上抓住了人與自然,但在現實的人與自然面前卻無能為力。
馬克思恩格斯則立足于歷史的、現實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以人的現實的感性實踐活動為基礎,把人類主體與自然客體相聯系,克服了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費爾巴哈的人本學舊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缺陷,為馬克思恩格斯從科學的實踐出發來反觀自然、實現對其生態思想的革命性變革提供了可能。
四、結 語
總體說來,雖然過去歷史上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生態思想成果,但已經不能被用來有力地揭示新的社會歷史時期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馬克思恩格斯基于科學的實踐觀,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李比希的農業化學思想進行了承襲和擴展,對摩爾根的人類學、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進行了批判和反思,尤其是揚棄和變革了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費爾巴哈的人本學舊唯物主義自然觀,從而在多重吸收與改造的基礎上完成了對自身生態思想體系的合理變革。
[1]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 [M].郭忠華,潘華凌,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NewanalysisontheoreticalsourcesofecologicalthoughtsofMarxandEngels
YE Dong-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13, China)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 have its profound and rich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They mainly originate from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Liebig’s agricultural chemical thoughts, Morgan’s anthropology, Malthus’s population theory, especially the mutiple absorption and reform of Hegel’s objective idealist dialectics and Feuerbach’s old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al of humanism, based on which their own system of ecological thoughts is reformed innovatively.
Marx; Engels; ecological thoughts; dialectics; evolution theory; materialism; idealism; anthropology; population theory
2014-05-07
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3B224)。
基金項目: 葉冬娜(1988-),女,福建福州人,碩士生,主要從事文化哲學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4-07-18 13∶24在中國知網優先數字出版。 網絡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718.1324.003.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5.13
B0-0
A
1674-0823(2014)05-0461-06
(責任編輯:郭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