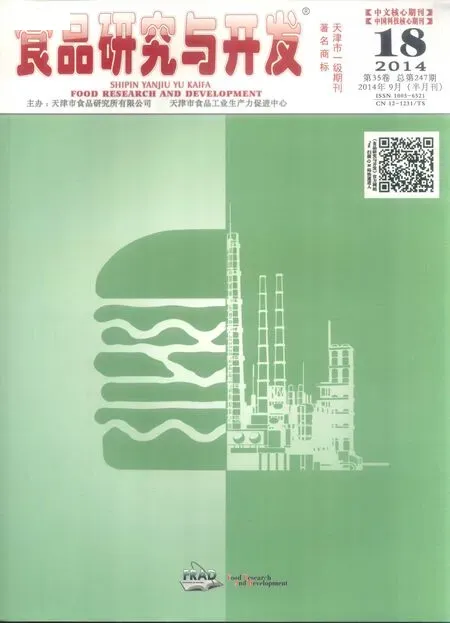論縱向監管理念對食品安全法草案民事責任立法的影響
戈含鋒
(天津科技大學法政學院,天津300222)
論縱向監管理念對食品安全法草案民事責任立法的影響
戈含鋒
(天津科技大學法政學院,天津300222)
分析了縱向監管理念在民事立法中的表現及不足,指出隨著新型食品安全問題發展,縱向理念在民事立法上的局限日益顯露,新的修改應該突破過度強化懲罰的傳統思路,深入立法理念的反思,如此才能保證未來食品安全法草案的現實成效。
食品安全;縱向監管;懲罰性賠償
食品安全的規制思路大致有兩種,一是縱向強化,即倚重權力運作,強化縱向監管與懲罰,體現在民事領域,即強調制裁性民事責任對食品安全的保障;二是權利制衡的思維,即主要依靠市場和平權性法規,通過對當事人權益的平等保障實現對食品安全的促進。長期以來,我國食品領域立法,包括以平權制衡為特點的民事責任規制領域都主要側重前一思路。2014年5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的《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中,這一問題依然存在。本文指出,隨著現代化食品安全問題的發展和食品風險的深化,更為技術化的復雜責任制度構建亟待建立,傳統強化縱向監管,尤其民事領域中簡單側重懲罰的特征從根本上不足以應對現代化條件下食品問題的復雜化調整要求。在當前立法中,應該減輕縱向監管對以平權為特征的民事責任領域的過度影響,反思民事責任理念定位,這將直接制約未來食品安全法草案的現實成效。
1 風險社會下食品安全問題的發展
分析食品安全問題,應當首先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基本的了解。隨著當下社會向后工業時代的發展,風險的存在日益成為社會的一個本質特征。
由德國學者貝克1986年在其《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對科技高度發達但存滿危機的現代社會予以深刻界定。此后許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初露端倪,不同于傳統社會的社會特征進行界定與描述,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學者吉登斯從全球化角度入手對現代社會多維特征進行分析,指出現代社會已經轉化為風險社會,風險強度空前加劇,風險環境也空前擴張,就風險強度而言,“我稱之為風險強度的東西肯定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環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核戰爭的可能性、生態災難,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經濟交流的崩潰,以及其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勾畫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險前景。”[1]伴隨科技的發達以及人類活動交往的便捷和擴展,風險從傳統時代的偶然成為風險社會的必然,風險來源更為復雜廣泛,這一狀況必然也波及到食品領域,現代新型食品問題相較傳統時期日益呈現出如下特點。
1.1 表現形式及解決更為復雜,需要社會科學領域多種手段,包括法律的綜合性運用
現代工業化模式的食品生產中,食品生產從原料到加工,再到包裝運輸,以及商業流通導致跨時空消費,流程和環節遠遠多于傳統生產,食品安全風險可能在任何一個流程和環節產生,問題影響波及面也更大,根源確認更為艱難,也更易引致社會更大范圍的恐慌。在性質上常常超出了傳統社會單純法律“案件”僅局限于當事人的范疇。
在政府決策行為上,伴隨著當前社會的另一個基本特征——信息時代的進入,現代食品事件中政府的介入更需技巧與謹慎,以避免食品問題的進一步升級。例如我國農業部轉基因方針與農業部機關幼兒園選擇的沖突,可以形象說明這一特點。2010年10月農業部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陳萌山在農業部介紹當前農業生產形勢的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農業部要“積極穩妥地推進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但幾乎同時,農業部機關幼兒園在公布專為自己食用的食物原料清單時,卻有“食用油采用非轉基因油”等推介語。這一對外和對己雙重標準的做法引起了廣泛質疑,甚至農業部的信任危機。總之,現代食品安全事件解決需要更多綜合性手段的采取,政府本身也不僅是問題的解決者,也可能成為爭議本身的當事人。
1.2 牽涉人數、地區往往規模更大,基于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的傳統縱向監管不足全面應對
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該事件受害者涉及范圍相當廣泛,跨度隨著現代商品物流深入甘肅、陜西、寧夏、湖南、湖北、山東、安徽、江西、江蘇等多個省份地區,甚至致害方的確認也一度相當復雜,當時有研究者指出,“從食品安全的角度講,包裝是否導致污染,工廠作業環境是否污染,或者在奶源環節甚至飼料就已添加違禁物,都還需要認真調查。”[2]無論是河北,還是事件首發地甘肅的行政部門,地域難題、生產領域監管主體等等都成為其首要難題。
1.3 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增加,責任程度,甚至責任人的確定都成為待解決的前提性問題
典型如湖南鎘超標大米事件,其產生原因在于我國工業化早期礦山企業的無序化排污進而重金屬的長期積累,盡管其引發的恐慌和波及范圍相當廣泛,但卻面臨無法確定責任人的尷尬,甚至無法作為一個法律事件而被追究和處理。食品安全事件后果、危害、影響結果與途徑、受害者范圍等等的不確定,以及諸多食源性疾病可能在短期內難以看出或者治愈,危害延續跨越時空等諸多特征,都使得責任的確定都成為一個前提性難題,強化制裁與懲罰本身即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因此,在現代食品安全事件的責任確定中,簡單地強化政府監管,強化當事人責任難以有效解決前述問題,現代食品問題的發展對政府的管理和決策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強化縱向監管在我國食品安全立法中的體現
需要指出,縱向監管理念作為一種管理方式,本身與依靠市場和民事權利制衡的思維并無優劣之分,其在當下作為一種手段的不足,根本原因在于食品安全問題超出了簡單強化縱向監管,強化懲罰就可以解決的范圍。但是,我國當前食品安全基本法及后續草案對這一趨勢及手段的不足仍缺乏足夠警惕和反思。
2.1 《食品安全法》中的縱向監管問題
草案提出前,我國食品安全立法層面的縱向強化在監管主體及監管手段兩方面具有相當代表性。
2.1.1 監管主體設置問題
監管主體設置傾向于構建權力集中型的行政監管機構,對現有機構的優化及合作,以及細節性的實踐和操作性規則重視不夠。這既表現在中央層面,也體現在行政部門的執法側重層面。中央層面由國務院組建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對食品安全進行統一監管,強化了食品安全監管的權力集中模式。實際操作和更細節的構建上雖然規定了衛生行政部門承擔綜合協調職責,負責大部分的食品安全管理事務,但衛生行政部門與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等處于同級地位無法保證其綜合協調的權威性。
在部門層次執法機構設置上同樣具有前述趨向。
進入風險社會,國家面對的公共性事件日益增多,計算機安全,恐怖暴力、核威脅等等,按照此種“出現問題——構設新監管機構”的常規思路,難以想象我們的政府機構將擴大到何種程度。
2.1.2 監管手段問題
監管手段的采取中,強化行政與刑事懲罰始終是執政層偏好的方式。
以最直接體現食品安全立法理念的《食品安全法》為例,其中15條責任規定中體現縱向監管的就達13條,民事責任卻僅有2條,且即使這一領域,也包含一條民事領域相對鮮見,體現了國家權力積極介入態勢的懲罰性規定——“十倍賠償”。
《食品安全法》頒布不久,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門又聯合公布了《關于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通知》,要求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加大對食品安全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甚至要求法院“罪當判死刑要堅決判處死刑”,體現了相當濃厚的重刑思維和權力運作理路,在基本立法理念上與食品安全法異曲同工。但現實效果我們已經知道并不符合政策制定者們的預期。
2.2 《食品安全法》草案的修改側重
2014年5月14日通過的修訂草案重點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對生產、銷售、餐飲服務等各環節實施最嚴格的全過程管理,強化生產經營者主體責任,完善追溯制度。二是建立最嚴格的監管處罰制度。對違法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構成犯罪的,依法嚴肅追究刑事責任。加重對地方政府負責人和監管人員的問責。三是健全風險監測、評估和食品安全標準等制度,增設責任約談、風險分級管理等要求。四是建立有獎舉報和責任保險制度,發揮消費者、行業協會、媒體等監督作用,形成社會共治格局[3]。
從修訂內容重點來看,強化縱向權力規制仍然居于主導地位,對公眾社會力量的關注仍然不足。草案四方面修訂重點中體現縱向監管理念的就占據1/2。盡管社會共同治理格局的提出體現了對社會力量的關注,但這一層次之下的具體制度構建仍然存在對政府權力的過度倚重和對社會力量的猶疑,以有獎舉報為例,食品消費者僅處于信息提供者的地位,啟動、監督和追責的主導性流程仍然在于監管主體一方,最終仍然有賴于權力機關的積極配合。
當然,草案提出的更全面制度構設,如追溯制度、風險監測、評估和食品安全標準,有獎舉報和責任保險等體現了政府管理技術的提升和對食品安全問題深入認識,但其整體構建是一個長期復雜的行政介入過程,在短期內真正產生現實效果和容易被采納的,仍然主要是草案的強化制裁內容。
總之,在草案所有的修改與制度構設中,對社會力量的應有關注與此前并無太大增加。早在《食品安全法》制定之初,關于該法就不乏對其內在監管理念局限的評論,進而對其效果的悲觀預期[4]。當前草案中對縱向監管的過分倚重仍然是存在的一個問題[4]。
3 縱向監管在民事責任立法中的過度運用:論懲罰性賠償的問題與限度
傳統強化縱向監管思路下,食品安全民事責任規制中對懲罰措施的強調成為民事立法的一貫趨勢。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雙倍賠償,到食品領域專有的十倍賠償,再到當下草案的審議,盡管在現實中已經產生了相當多爭議,民事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在立法上卻始終未受到認真的審視。本文將基于十倍賠償探討縱向監管在民事領域過度運用的局限及問題。
3.1 十倍賠償分類
從法經濟學角度以是否有損害結果,也就是受害者追究違法者責任時是否有“成本”上的要求,可以將懲罰性賠償分為兩種:有損害情形下的懲罰性賠償和沒有損害結果,僅因法律強制規定而使所謂“受害者”獲得懲罰性賠償。前種情形下,受害者獲得這一懲罰收益是有成本的,而后一種則無成本。這正是我們食品安全法中十倍賠償的問題所在。
3.2 十倍賠償的社會問題
在零成本而有巨大收益可能的制度性保障下,獲利甚至投機的社會現實就不可避免。隨著《消費者保護法》雙倍賠償的出臺和《食品安全法》十倍賠償的推進,我們看到,一種制度性逐利手段和主體——打假以及職業打假人甚至打假公司不斷涌現甚至幾成產業,同時也產生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
有研究指出,由于打假人和打假公司之打假主要目的是試圖依據法規提供的制度空間獲利,而非實際利益受損后的補足和維權,在這一根本動機和相關制度支持下,其行為往往依據利益需要游走在合法與非法的邊緣,打假時大多分工明確,踩點、購買、談判明確分工,在解決方式上多不愿意走司法訴訟程序而堅持私了。有些“打假”行為甚至不乏對商家吹毛求疵的惡意勒索,敲詐勒索,干擾到了市場秩序。不同于行政執法,根本動因在于獲利的打假普遍缺乏行政執法嚴格的規范性和合法性,涉嫌投機甚至違法并不鮮見。
在打假對象的選擇上,打假者的選擇大多并不符合消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真正預期。基于對利益的關注和投入產出的衡量,現實中職業打假者選擇的多是低成本,容易確定和查找問題的食品問題,比如外觀和標識等等。而對于需要消費才能真實感知商品內在品質和問題,如假酒和包裝標識毫無問題的三鹿奶粉等等,打假人并無真正消費者的感同身受,根本起不到監督和打假的作用。有實務界律師就指出,大多數打假案件中,商品本身并不存在假冒和偽劣的問題,僅僅是在標識上出現瑕疵便被一些“打假專業公司”提出高價索賠[4]。
4 小結
在我國嚴峻的食品安全形勢下,懲罰性賠償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問題與弊端同樣值得關注,其根源即體現為縱向監管強化在民事領域的過度運用,在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復雜化的當下,簡單地強化縱向監管并不足以全面應對當下食品安全問題的復雜性與根源多樣性,這是當前我國食品草案修改亟需注意的一個方面。
[1]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
[2]劉京京.河北公安稱問題奶粉非產銷環節摻假[J].財經,2008(9):15
[3]汪紅.食品安全法4年來首次修改[N].法制晚報,2014(6):19
[4]蒲曉磊.知假買假:從爭議到支持[N].法治周末,2014,9(1)
About the Influence of Vertical Regulation Principle on the Legislation of Civil Liability in Food Safety Law Draft
GEHan-feng
(Schoolof Law,Tianjin UniversityofScience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222,China)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with the developmentofmodern food safety problems,traditionmeans has been under threat froMvarious aspects.We discus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forMto food safe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awbacks the vertical regulation faced in the new situation,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and give somesuggestions for future.
food safety;vertical regulation;punitive damages
10.3969/j.issn.1005-6521.2014.18.058
2014-09-18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3YJC820020)。
戈含鋒(1976—),女(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學、立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