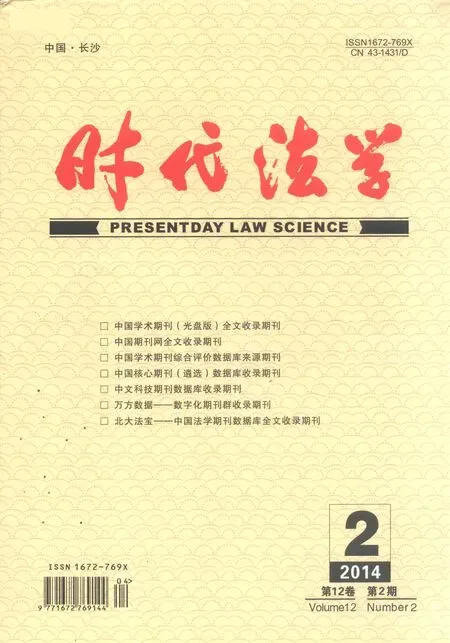中國本土法治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評《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
彭中禮
中國本土法治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評《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
彭中禮
法治是人類文明共同智慧的成果,所以當前世界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通過法治來治國理政。但是法治的發展卻沒有共通性的普遍真理,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基于其自身特色的法治實現道路。每當我們捧起孟德斯鳩的那本傳世名著《論法的精神》之時,其字里行間所流露出來的無不是對特定民族法律特色的概括,當然也是對實現法治不可能存在普遍真理的詮釋。孟氏的這一觀點又被后人進一步深化,如薩維尼便認為法律都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不注重本國本民族習性特點的法律移植是違背民族精神的。我想,這些哲人們所敘說的不僅僅只是法律,還有關于法治發展的進路。也就是說,任何國家都可以選擇法治作為治國方略,但對法治發展道路的選擇應當各有不同,每個國家都應當根據本國的特色來走自己的路。同樣,中國的法治發展有中國的現實國情,中國的法治發展也有中國自己的語境,我們可以選擇法治,但是我們不能盲目地走別人走過的路,特別是當考慮到我們的試錯成本太高之時,我們就應當珍惜我們的機會:根據當下中國的具體國情來選擇我們的法治發展道路。正因為如此,蔣先福教授的新作《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尤其值得大家欣賞。
評述蔣先福教授的這部新作,必須從農民工說起。我們知道,改革開放的春風滋潤了偉大的共和國,給中國發展帶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在共和國的偉大發展之中,有那么一群人,背著鼓鼓的行囊,穿越神州大地,尋覓新的生活。因為制度的原因,這群人被稱為“農民工”(民工)。顧名思義,他們被制度賦予了“農民”的稱號,但是卻在城市干著與農業生產活動無關的事業,所以實際上是“工人”的身份。鑒于歷史的負擔和制度的束縛,我們的部分法律制度卻暫時沒能容納和接收他們。對此,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國家都會在制度上付諸改革行動,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學者在思想上都會付諸理論深思。幸運的是,我們的國家并沒有拋棄他們,我們的學者也沒有忘記他們。我們的國家站在民生保障的立場,正在逐步改變舊有的制度,為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我們的學者也基于學術良知的立場,給出了較多的深刻研究,推陳出新了諸多良策。可以說,蔣先福教授的《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一書堪稱這方面的代表。該書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從法學理論層面將農民工的流動與法治的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相關性研究不再局限于農民工問題本身,而是將視野擴大到了“中國”這一宏觀層面,擺脫了就事論事的思考路向。具體地說,該書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跳出“農民工”來看待“農民工”。學術研究的最大特點就在于“片面深刻”,但這也構成了學術研究的最大弱點,古人說的“相輔相成”一點也不為過。如果過于關注某個問題的某一點,或許真能做到“深刻”,但是我們認為這種深刻也是一種不具有廣度的深刻,甚至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嫌疑,因而是不可取的。任何真正的學問不僅要思考深刻,但更要思考真實。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的農民工問題研究就存有弊端。雖然單純的政治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或者人類學研究盡管可以看到農民工的某些問題,但是局限于觀念的制約而無法整體認知農民工問題的真實走向。但是,讓我感動的是,該書的作者敏銳地發現了我們沒看到的問題:農民工問題是一個時代問題,更是一個法治問題。作者從古老的移民與法治的關系源流史開始考察,建構了有深度的理論基礎和事實基礎,又回到了中國的農民工現實,史料真實,理論可靠,結論深刻。
第二,站在“世界”來看待“農民工”。作者通過學術考證指出,人類歷史的重大發展,往往與移民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有一些國家法治文明昌盛,也是因為移民的重要作用。比如,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一書中,以十分詳實的資料證明了歐洲近代從領主制下流動出來的自由民推動了城市自治、市民社會和商業貿易的興起,這不僅標志著封建經濟結構分解的開始,而且使具有商業精神的由自由民組成的新興市民階級代表著一種進步的、革命的社會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推動了近代法治化的歐洲從漫長黑暗的中世紀脫胎而出*蔣先福.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第一章.。而且,從世界上其他國家來看,移民對法治的發展也具有相應的促進作用。所以,該書基于人類社會法治發展的宏觀大勢,邏輯地再現了我國農民工也正在創造改變歷史的奇跡。正是億萬農民工通過務工移民的親身實踐,在不經意間成就了中國法治發展的新局面。
第三,回到“中國”來看待“農民工”。從時空范圍來看,農民工問題是當代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但卻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敗相銜接。中國需要什么,中國能做什么,中國存在什么,與改革開放相關,更與農民工相關。馬克思經典作家們曾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締造者,因為是人民的實踐創造了歷史。就中國現代化這一特定時空而言,農民工雖然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締造者,卻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重要實踐者。農民工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推動著共和國的現代化,推動著中國法治的現代化進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或許看到了農民工的時代價值和中國意義,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的是農民工對中國法治發展的積極影響。在建設法治中國的話語背景下,中國法治發展要建立起強大的主體自信度,就必須正視農民工作為中國人民中的一員所做出的實踐貢獻。農民工的行為沒有彩排,沒有預演,真實可靠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徑,預示著當代中國法治的現實走向。所以,看待農民工與法治的關系問題,必須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來。
不管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農民工都充當了一種英雄的角色,盡管有點悲劇和無數屈辱,但是那種壯烈色彩卻不容抹殺。特別是當各種節日來臨之際,你看著那些背著行囊急匆匆行走的人們之時,請不要誤以為他們是文字詩人,他們沒有用筆記下他們自身的訴求和吶喊;但請記住他們是行動的詩人,他們的腳印踏出了新格局、新景象、新天地!總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歷史如斯進程就在農民工的各種流動之中完成了,法治也因此出現了實質性的變化。正如作者在本書中所提到的那樣,在農村,當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離開鄉村之后,使得鄉村的原有社會秩序發生了慢性解體,宗族勢力開始式微,宗法權威慢慢下降,宗族結構日益解體,村落習俗日趨衰落,甚至舊有的糾紛解決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計劃經濟時代為農村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規都面臨挑戰,基于土地的制度束縛不得不讓我們重新思考農民的未來。而在城市,當大量農民工進城之后,以戶口為標志的身份制度不斷受到批評,保護市民利益的法律制度開始瓦解。于是,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發現了農民工基于公平正義的要求有著訴求權利的合法性——來自道德的和憲法上的。雖然我們舊有的法律制度本身就將農民的身份給定位了,但是歷史又在不經意之間以改革開放的形式給了農民工一個“天大”的機會來改變這些制度,也給了我們國家以“地大”的機會來修正舊有的制度。不斷變革的制度,特別是忽視了身份差別的制度,因為契約文明的參與,不斷迎向法治的理想。
當然,從農民工的視角來考察中國的法治發展,不僅有許多理論問題需要廓清,而且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實證。該書側重說理,條分縷析,令人折服。但如果能夠輔之以實證資料印證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之間的互動,可能內容更為充實。此外,因為我國務工移民的持續發展,如何加快城鄉一體化法律體系建設,這既是務工移民與法治發展論題的應有之義,也是我國面臨的當務之急,但該書對這方面的前瞻性討論尚屬薄弱。雖然該書存有上述不足,但瑕不掩瑜,筆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該書作為探尋我國本土化法治發展道路的拓荒之作,必將為讀者帶來開卷有益的樂趣。
2014-02-20
彭中禮,男,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湖南行政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