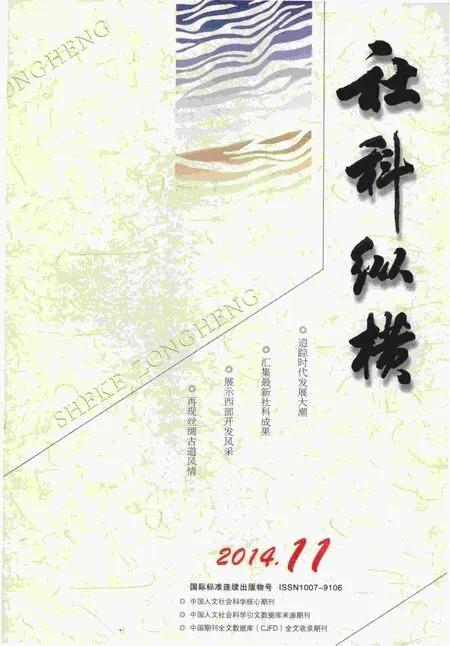民國(guó)初年的法律與革命——以姚榮澤案為例
鄧學(xué)文 黃珍德
(1.廣州城建職業(yè)學(xué)院 廣東 廣州 510925;2.華南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廣東 廣州 510631)
發(fā)生在民國(guó)初年的姚榮澤案是中國(guó)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圍繞該案件的審理,當(dāng)時(shí)首任司法總長(zhǎng)伍廷芳和以陳其美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展開了激烈的爭(zhēng)論,孫中山也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guān)注。案件的最終結(jié)局促使革命陣營(yíng)進(jìn)一步發(fā)生分化。鑒于學(xué)術(shù)界已有成果對(duì)此關(guān)注不夠①,本文試圖以姚榮澤案的發(fā)生和審理為歷史透視點(diǎn),通過分析伍廷芳和陳其美圍繞該案件的不同態(tài)度和案件的歷史演變,探討民國(guó)初年法律與革命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一、姚榮澤案的發(fā)生
姚榮澤案又稱周實(shí)、阮式案,是指1911年11月清朝江蘇山陽知縣姚榮澤慘殺辛亥革命志士、南社社員周實(shí)、阮式的案件。武昌起義后,阮式和周實(shí)聯(lián)合其他江蘇革命分子積極活動(dòng),召集山陽縣各校學(xué)生和旅滬旅寧回淮學(xué)生,組成學(xué)生隊(duì),被推為正副隊(duì)長(zhǎng),奪取城守營(yíng)槍支自用。[1]11月12日,宣布山陽獨(dú)立。14日,山陽縣召開光復(fù)大會(huì),清朝山陽知縣姚榮澤沒有出席,被認(rèn)為有意抵拒革命。阮式在會(huì)上怒斥姚榮澤不明大勢(shì),“避不到會(huì),即為反對(duì)光復(fù)之行為”[2](P158)。會(huì)后,周實(shí)和阮式積極籌建山陽軍政分府,并出于政權(quán)順利過渡和社會(huì)穩(wěn)定的考慮,要求姚榮澤擔(dān)任新政權(quán)的民法長(zhǎng)。姚榮澤表面上贊成光復(fù),實(shí)際暗持兩端態(tài)度,伺機(jī)而動(dòng)。他盡管不得已任司法長(zhǎng),但對(duì)周實(shí)、阮式等革命分子早已懷恨在心。光復(fù)大會(huì)第二天,姚榮澤來到山陽團(tuán)練局,阮式當(dāng)眾質(zhì)問他為什么不參加光復(fù)大會(huì),并指出他對(duì)革命不堅(jiān)定,持觀望態(tài)度,還當(dāng)面盤查山陽縣征收的糧賦情況。姚榮澤惶懼無以對(duì),阮式持雙管手槍,指姚胸口,要求交出漕銀,姚答應(yīng)三天內(nèi)交出,但暗地里勾結(jié)地方劣紳設(shè)計(jì)暗殺革命黨人。[3](P18)11月17日午后,周實(shí)被姚榮澤以議事為名設(shè)計(jì)誘入山陽學(xué)宮。周實(shí)一到那里,即被當(dāng)場(chǎng)槍殺身亡。姚榮澤又命人搜捕阮式,將其押到學(xué)宮剖胸而死。28日,又命人將周父抓入監(jiān)牢。不久,鎮(zhèn)江軍分政府支隊(duì)進(jìn)駐淮安,追究周實(shí)、阮式慘案,姚榮澤自知罪孽深重,逃到南通,庇護(hù)于通州民軍司令張?jiān)垺?/p>
1912年南京臨時(shí)政府成立后,南社柳亞子、朱少屏、蔡治民等人積極活動(dòng),要求嚴(yán)懲姚榮澤,為周、阮昭雪復(fù)仇。滬軍都督陳其美(亦為南社社員)對(duì)此全力支持。2月6日,他向臨時(shí)大總統(tǒng)孫中山、司法總長(zhǎng)伍廷芳、次長(zhǎng)呂志伊電請(qǐng)昭雪周、阮冤獄,詳細(xì)敘述了周實(shí)、阮式謀求山陽光復(fù)和慘被姚榮澤殺害的經(jīng)過,歷數(shù)姚榮澤的罪行,要求將姚榮澤拘拿到上海審訊,為革命志士報(bào)仇。孫中山關(guān)注周實(shí)和阮式被姚榮澤慘殺一案,最初指令由江蘇都督莊蘊(yùn)寬處理,后來因?yàn)橹軐?shí)和阮式二人的家屬及南社等團(tuán)體的告發(fā)以及陳其美的要求,便同意改在上海審訊。2月9日,孫中山令莊蘊(yùn)寬將周實(shí)和阮式一案移交滬軍都督辦理,稱:周阮一案“既然指證有人,即是非無難立白,復(fù)據(jù)近日各報(bào)揭載姚榮澤罪狀,輿論所在,亦非無因,該案系在滬軍都督處告發(fā),且顧振黃等亦已到滬侯質(zhì)”,應(yīng)將全案改歸滬軍都督徹查訊辦,以便迅速了結(jié),要求莊蘊(yùn)寬立即將全案的案卷移交滬軍都督辦理。[4](P71)
在孫中山的支持下,陳其美幾經(jīng)交涉,終于在南通拘捕了姚榮澤,經(jīng)蘇州押到上海審理。
二、司法獨(dú)立的論爭(zhēng)
姚榮澤案是民國(guó)成立后第一宗大案要案,時(shí)任南京臨時(shí)政府司法總長(zhǎng)的伍廷芳對(duì)其十分關(guān)注,要求審理姚榮澤案必須堅(jiān)持司法獨(dú)立的原則,即司法權(quán)必須與立法權(quán)、行政權(quán)分離,司法權(quán)只能由司法機(jī)關(guān)行使,行政長(zhǎng)官不得行使司法權(quán),也不得干預(yù)司法。伍廷芳設(shè)想,首先應(yīng)該讓自己主持的司法部在審理姚榮澤案時(shí)獨(dú)立地行使全部職權(quán),因此明確指出:“姚榮澤一案,既按照文明辦法審理,則須組織臨時(shí)之裁判所,所有裁判所之支配,應(yīng)由敝部(司法部)直接主任。應(yīng)派某人為裁判官、某人為陪審員,其權(quán)原屬敝部。”[5](P55)然而,伍廷芳的這個(gè)主張?jiān)獾疥惼涿赖姆磳?duì)。
起初陳其美想要以軍法處置姚榮澤,以為革命志士報(bào)仇雪恨,結(jié)果遭到多方反對(duì)。皖南同鄉(xiāng)會(huì)致函陳其美,反對(duì)以軍法處置姚榮澤,指出陳其美“身為都督,表率群倫”,進(jìn)入共和時(shí)代,“不可有離法逞臆之行”。[6]伍廷芳同樣堅(jiān)決反對(duì),堅(jiān)持由司法部組織一個(gè)臨時(shí)裁判所進(jìn)行審判。伍廷芳在給孫中山的電函中指出:“民國(guó)方新,對(duì)于一切訴訟應(yīng)采文明辦法,況此案(姚案)情節(jié)重大,尤須審慎周詳以示尊重法律之意。”伍廷芳還進(jìn)一步提出了審判姚案的具體方法:“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員承審,另選通達(dá)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為陪審員,并準(zhǔn)兩造聘請(qǐng)辯護(hù)士到堂辯護(hù),審訊時(shí)任人旁聽。”[7](P501)孫中山贊同伍廷芳的意見,認(rèn)為如此審判姚榮澤案“極善”,要求遵照辦理。[4](P109)鑒于此,陳其美不得不放棄以軍法處置姚榮澤的想法,同意由司法部組織一個(gè)臨時(shí)裁判所進(jìn)行審判。盡管如此,陳其美盡量爭(zhēng)取使審判姚榮澤案的法律程序有利于革命利益。
首先,陳其美力圖在裁判官的任命上占主導(dǎo)地位。為了使姚榮澤案在審判時(shí)做出對(duì)其有利的判決,他于1912年2月29日單方面委任“(滬軍都督府)軍法司長(zhǎng)蔡寅為臨時(shí)庭長(zhǎng),日本法律學(xué)士金泯瀾二人為民國(guó)代表”。[5](P55)伍廷芳反對(duì)陳其美的安排,以為臨時(shí)庭長(zhǎng)的人選配置是司法部的事情。但鑒于姚榮澤案的特殊性,伍廷芳允許陳其美派人出任裁判官,不過不能擔(dān)任庭長(zhǎng)。為此,伍廷芳初步擬定了一個(gè)審判方案,即組織一個(gè)臨時(shí)裁判所,由司法部委派陳貽范為所長(zhǎng),丁榕,蔡寅為副所長(zhǎng),設(shè)三個(gè)或五個(gè)陪審員,臨時(shí)配定,凡裁判所制度,先由律師將全案理由提起,再由裁判官詢問原告及各人證,原告和被告律師反復(fù)盤問原告。接著再審被告,其審問的方法與原告同。最后由原告和被告雙方律師各將案由復(fù)述結(jié)束。最后由裁判官將雙方曲直宣讀。至于判決之權(quán),則全屬于陪審員。只有陪審員才能確定被告是否有罪,除此之外判決不能加入任何其他詞句。如果有人對(duì)于裁判官及律師審問時(shí)有可疑之點(diǎn),可以用簡(jiǎn)單概括的話詢問被告及各人證。[7](P502-503)
對(duì)上述方案,陳其美沒有異議,但仍然堅(jiān)持由滬軍都督府委派的蔡寅出任庭長(zhǎng),堅(jiān)持認(rèn)為姚榮澤案與一般刑事案件不同,它近乎反革命案件,必須有革命黨方面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伍廷芳不得不作出讓步,提出了一個(gè)折中的辦法,那就是不設(shè)正副所長(zhǎng),統(tǒng)一叫裁判官,在規(guī)定位置時(shí),陳貽范居中,蔡寅居左,丁榕居右。在伍廷芳的反復(fù)要求之下,陳其美最后同意了這種安排。至此關(guān)于裁判官的人選之爭(zhēng)告一段落。
不久,伍廷芳和陳其美對(duì)于陪審員的人選問題又發(fā)生了分歧。由于伍廷芳認(rèn)為在司法審判中陪審員的地位最重要,“至判決之權(quán),則全屬于陪審員”,“惟陪審員只能為有罪無罪之判決不能加入他詞”,因此對(duì)于陪審員的選擇十分慎重。早在1912年2月18日伍廷芳給臨時(shí)大總統(tǒng)孫中山的電函中指出,應(yīng)選“通達(dá)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為陪審員”[7](P501)。孫中山也表示贊同。但陳其美卻要求指定滬軍都督府的丁榕為陪審員,遭到伍廷芳的強(qiáng)烈反對(duì)。3月2日,伍廷芳向陳其美指出,組織裁判所的權(quán)力歸司法部,派誰為陪審員也是司法部的事[7](P502-503)。3月11日,他又向陳其美詳細(xì)地解釋了選陪審員的方法:“按文明國(guó)通例,須舉地方公正紳士二、三十人,將其邀請(qǐng)到堂,即將其人姓名置一筒內(nèi),作拈鬮辦法,由筒內(nèi)拈出七人或五人,隨同秉公裁判。如數(shù)人中有與原被告夙有嫌怨或于此案抱有成見者,原被告可不承認(rèn),再由筒內(nèi)拈出他人充補(bǔ),亦須原被(告)承認(rèn)方可。”[7](P505)陳其美接受了此建議,同意“會(huì)同司法總長(zhǎng)所派陪審各員秉公訊辦”,以“拈鬮辦法”產(chǎn)生陪審員,不過他要求滬軍都督府派出與司法部所派陪審員候選人數(shù)目相當(dāng)?shù)呐銓弳T候選人。[5](P79-80)3月19日,由陳其美、伍廷芳各推薦了20位知名人士作陪審員候選人,再根據(jù)公正和回避的原則,從中選取7人出庭。
陳其美為了使姚榮澤案的審理便于革命黨方面,符合革命利益,想通過控制姚榮澤案裁判官和陪審員人選,達(dá)到鎮(zhèn)壓反革命的目的,雖然干預(yù)了司法審判,違背了民主法制的精神。但這樣也可以說是代表革命派一方的民意。而伍廷芳在審理姚榮澤案的裁判官和陪審員人選問題上雖然有所妥協(xié),但總的來講堅(jiān)持了原則,基本上掌握姚榮澤案審理的主導(dǎo)權(quán),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由于陳其美插手而導(dǎo)致的司法審判不能獨(dú)立。
三、文明審判的論爭(zhēng)
早在2月18日,伍廷芳給孫中山的電函中就提出姚榮澤的審理“應(yīng)采文明辦法”,“以示尊重法律之意”[7](P501)。那什么是文明辦法呢?就是由司法部組織一個(gè)臨時(shí)正當(dāng)?shù)牟门兴以试S原被告聘請(qǐng)律師到庭辯護(hù),進(jìn)行公開審判。采取這種“文明方法”的原因,伍廷芳的解釋是:“民國(guó)初立,吾國(guó)人一舉一動(dòng),皆為萬國(guó)人士所注視。況辦理此等重大案件,稍不合文明規(guī)則,則必起外人之譏評(píng),故不得不格外注意。免蹈前時(shí)濫用法權(quán)之覆轍,致失友邦信重新國(guó)之感情。凡此非為姚榮澤一人計(jì),為民國(guó)之前途計(jì)也”[7](P502-503)。
伍廷芳關(guān)于文明審判姚榮澤案的主張又為陳其美所反對(duì),尤其是圍繞著姚榮澤能否聘用外國(guó)律師的問題,二人發(fā)生了激烈的爭(zhēng)辯。姚榮澤要求聘用外國(guó)律師為自己辯護(hù),伍廷芳贊同。陳其美反對(duì)姚榮澤聘用外國(guó)律師的要求,反對(duì)的理由之一是維護(hù)中國(guó)的法權(quán)。他認(rèn)為,此案關(guān)系雙方都是華人,不是華洋交涉案件,且裁判地點(diǎn)亦在華界之內(nèi),與外人絕不相干。[5](P60-61)他提出,文明各國(guó)采用相互主義,我國(guó)律師不能在外國(guó)法庭上辯護(hù),那么我國(guó)法庭也不允許外國(guó)律師到庭辯護(hù)。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了。且“華人有崇拜外國(guó)人之習(xí)慣性,依賴一生,則情奪勢(shì)絀,莫敢爭(zhēng)衡”。因此,應(yīng)該拒絕外國(guó)律師到庭辯護(hù)和外人到庭作證。不僅如此,陳其美還指出,“我國(guó)尚未頒行定律,外國(guó)律師到庭時(shí),仍不免應(yīng)用該國(guó)法律,”將會(huì)“惹起紛爭(zhēng),釀成交涉”。[5](P75)因此陳其美向伍廷芳提議,姚榮澤案審理中對(duì)于姚榮澤要求聘用外國(guó)律師一節(jié)“務(wù)祈嚴(yán)詞拒絕,以保法權(quán)。”[5](P68)
陳其美上述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duì)的。由于民國(guó)新近成立,法制建設(shè)很不完善,許多法律規(guī)章尚未厘定,如聘用外國(guó)律師,他們就會(huì)在法庭上沿用其所在國(guó)的法律進(jìn)行辯護(hù),不利于中國(guó)將來的法律自主。對(duì)此,伍廷芳沒有否認(rèn),但對(duì)于陳其美提出聘用外國(guó)律師不利于維護(hù)中國(guó)法權(quán)的看法,伍廷芳則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說:“法治完全之國(guó),決無一領(lǐng)土之內(nèi),而有他種法權(quán),參與于其中。今租界之內(nèi),尚有他國(guó)法庭,實(shí)為吾國(guó)之大辱。”若不從根本上解決,而斤斤計(jì)較于能否聘用外國(guó)律師,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何況此前閘北裁判所審訊喬大一案,已經(jīng)聘用外國(guó)律師了。[7](P507)不僅如此,他甚至認(rèn)為允許聘用外國(guó)律師有利于中國(guó)收回治外法權(quán)。他說,中國(guó)“法律腐敗,審判糊涂,已非一日”,因此從一通商開始,外國(guó)人就攫取了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原因固然是與當(dāng)時(shí)訂約的人不懂世界形勢(shì)有關(guān),但實(shí)際上中國(guó)法律及審判方法敗壞是“主要禍根”。所以,伍廷芳提出,中國(guó)現(xiàn)在想要收回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必須在收回之先,將“法律及審判方法實(shí)地改良,示以采用大同主義之鐵證,使各國(guó)報(bào)紙表揚(yáng)而贊美之,隨即編撰完美之法律”,然后與外人談判,這樣收回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才有希望。[7](P506)所以,他認(rèn)為不僅應(yīng)該允許姚榮澤聘用外國(guó)律師,而且應(yīng)該允許外國(guó)人到法庭作證。
其實(shí),陳其美如此堅(jiān)決地反對(duì)姚榮澤聘用外國(guó)律師,主要是擔(dān)心姚榮澤聘用外國(guó)律師不利于革命利益。如前所述,他那么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人的“崇拜外人”的心理,就是擔(dān)心一旦允許外國(guó)律師到法庭上為姚榮澤作證,原告方在氣勢(shì)上就被壓倒,從而使審判“節(jié)外生枝”,甚至導(dǎo)致姚榮澤逍遙法外,不能為革命志士昭雪報(bào)仇。所以他強(qiáng)調(diào):“外人極注意此案,果能來庭觀審,已是昭示文明氣象,何必定要加入案內(nèi)耶?”[5](P74)對(duì)此,伍廷芳也不認(rèn)同。他致函陳其美,指出“大凡依賴之性,生于學(xué)識(shí),設(shè)使學(xué)識(shí)相同,則旗鼓相當(dāng),各思建樹,何至依賴他人?”假使莫敢爭(zhēng)衡,必定是“其才其理不及他人,然后為他人之才之理所勝,”這是被“優(yōu)勝劣敗之公例所淘汰”,并不是情奪勢(shì)絀。至于“以崇拜外人為華人之習(xí)慣性,此不過為懵無智識(shí)者言之耳,若稍有智識(shí)者,決不自承。況法庭之上,斷案之權(quán),在陪審員;依據(jù)法律為適法之裁判,在裁判官;盤詰駁難之權(quán),在律師。”難道因?yàn)楹ε峦鈬?guó)人,因?yàn)槌绨萃鈬?guó)人,就不敢與外國(guó)律師爭(zhēng)衡嗎?伍廷芳還認(rèn)為,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律師辯案,不能使用恐嚇的言論,而且無論哪國(guó)律師都只能按照案件曲折問難,雙方人證只有“答其所問之權(quán),而無反詰駁難之權(quán),既無所謂爭(zhēng)衡,何以見其崇拜?”[7](P508)
堅(jiān)持文明審判姚榮澤案,是伍廷芳在審理姚榮澤案問題上堅(jiān)持的又一理念。在伍廷芳看來,文明審判就是說明中國(guó)司法改良已經(jīng)取得了巨大成績(jī),就能向世界證明中國(guó)已經(jīng)開始“法良政美”,進(jìn)入文明國(guó)家之列,從而改變1907海牙國(guó)際會(huì)議將中國(guó)列為“不文明國(guó)家”的決議,甚至可能因此收回治外法權(quán)。所以,他以為新生的民國(guó)要借已引起中外矚目的姚榮澤案的審判來證明這一點(diǎn),為此他那么強(qiáng)調(diào)文明審判和收回治外法權(quán)之間的聯(lián)系,多次提到姚榮澤案審理的示范意義和對(duì)“外人”的影響,允許姚榮澤聘用外國(guó)律師和外國(guó)人到法庭作證。實(shí)際上,在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guó),伍廷芳的這種法律觀念是對(duì)帝國(guó)主義抱有幻想,列強(qiáng)并未因此取消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不過,伍廷芳文明審判的主張,對(duì)于近代中國(guó)司法改良確實(shí)不無意義。他所申言的“中國(guó)改良律例,慎重法庭,自是切要之問題”,已經(jīng)提出了改革中國(guó)傳統(tǒng)司法審判嚴(yán)重弊病的一條出路。例如在1912年3月29日,下關(guān)海軍部侯毅向陳其美和伍廷芳發(fā)函電,因?yàn)楫?dāng)時(shí)有一起陳大復(fù)殺人案比較復(fù)雜,他就建議:“似宜援周阮案由上海特開法庭傳集人證徹底訊究”。[8]
四、分歧的焦點(diǎn)和雙方的妥協(xié)
在西方國(guó)家多年的法律教育和生活,使伍廷芳崇敬近代資本主義法律無以復(fù)加。他深信,健全法制、司法獨(dú)立、尊崇法律是一個(gè)國(guó)家強(qiáng)盛的根本條件,是實(shí)現(xiàn)民權(quán)的基本前提。因此,他多次指出:“中國(guó)政治欲有所進(jìn)步,須先從司法一門入手”,改良審判,司法獨(dú)立。[7](P595)但在晚清社會(huì),伍廷芳“惜其時(shí)處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不能發(fā)展所能,以行平生志愿,抱憾良多”。[7](P517)因此,當(dāng)辛亥革命爆發(fā)和中華民國(guó)成立后,年屆古稀的伍廷芳滿心歡喜,挺身而出,出任臨時(shí)政府司法總長(zhǎng)。深諳西方法律的他久欲將其施于中國(guó)而不果,以為民國(guó)的成立為他許多法律思想付諸實(shí)踐提供了機(jī)會(huì)。以法治國(guó),法律至上是伍廷芳對(duì)于中華民國(guó)法律實(shí)踐的最高追求目標(biāo)。當(dāng)姚榮澤案發(fā)生后,伍廷芳就把對(duì)它的審理看成了施展才干、實(shí)踐法治理想的舞臺(tái)。由此不難理解,在同陳其美的論爭(zhēng)中,伍廷芳那么強(qiáng)調(diào)司法獨(dú)立、文明審判,始終堅(jiān)持自己的法治信念。
如果說伍廷芳視法律為生命,陳其美則以革命成功為最高的追求。他從1906年參加中國(guó)同盟會(huì)以來,在孫中山的旗幟下,不屈不撓,投身于資產(chǎn)階級(jí)的反清武裝革命,為中華民國(guó)的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孫中山曾經(jīng)這樣評(píng)價(jià)陳其美,說:“光復(fù)以前奔走革命,垂十余載,其間慷慨持義,聯(lián)綴豪俊,秘密勇進(jìn),數(shù)詢數(shù)瀕危殆,凡舊同志類能稱述。辛亥之秋,鄂師既舉,各省尚多遲回觀望,陳君冒諸險(xiǎn)艱[難],卒創(chuàng)義于滬上,爾時(shí)大江震動(dòng),紛紛反正者,滬軍控制咽喉,有以促之也。其后金陵負(fù)固,各省義師云集環(huán)攻,而餉械所資,率取給于滬軍,陳君措應(yīng)裕如,士無匱乏。此其于民國(guó)之功,固已偉矣。”[9](P388)在陳其美的心目中,革命至高無上,其他一切都為革命服務(wù)。他插手和解決姚榮澤案的動(dòng)機(jī)是至誠的,那就是替死去的革命同志報(bào)仇昭雪。正如他在2月6日的電文中所指出:“吾輩之所以革命者,無非平其不平。今民國(guó)方新,豈容此民賊漢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報(bào)其私仇,殺我同志?其美不能不為人昭雪,雖粉身碎骨,有所不辭。”[5](P50)
伍廷芳和陳其美盡管在法律和革命孰主孰次的問題上互相對(duì)立,但他們立論的基礎(chǔ)都是維護(hù)民國(guó),都以民國(guó)成立為立論前提,為自己辯護(hù)。伍廷芳認(rèn)為“民國(guó)方新”,正要以其法治原則行為處事,保衛(wèi)民權(quán),與以前的專制政權(quán)相區(qū)別,如果一開始就破壞法律,任意妄行,那必將對(duì)民國(guó)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姚榮澤應(yīng)當(dāng)交由司法機(jī)關(guān)依法處置;在審理上就必須堅(jiān)持司法獨(dú)立、文明審判的原則。伍廷芳以為這樣才能反映革命的意義,凸現(xiàn)民國(guó)之所以進(jìn)步的地方。陳其美則屢屢強(qiáng)調(diào)“民國(guó)初立”、“民國(guó)新立”,秩序未靖,革命遠(yuǎn)未成功,因此為了替革命同志報(bào)仇,他插手姚榮澤的審理。在陳其美那里,革命利益至上,為了正義事業(yè),為了革命的利益,即便違犯了法律又有何妨;而伍廷芳言必稱獨(dú)立,事必尊法律,實(shí)為不顧客觀實(shí)際的“迂腐”。
不管怎樣,正是相同的立論前提和基礎(chǔ),創(chuàng)造了他們妥協(xié)的條件。伍廷芳始終堅(jiān)持嚴(yán)格按照法律程序進(jìn)行審判,但他意識(shí)到姚榮澤案發(fā)生在革命還沒有成功的時(shí)期,涉及到對(duì)革命者的保護(hù)和對(duì)反革命分子的鎮(zhèn)壓,涉及到革命利益的保障。并且當(dāng)時(shí)普遍贊同法律至上的新聞媒體具體到姚榮澤案上也是一片反對(duì)伍廷芳的聲音,以為陳其美有權(quán)參與案件的審理。如1912年2月1日,《申報(bào)》發(fā)表旅滬淮安學(xué)團(tuán)致江蘇都督莊蘊(yùn)寬的電文,指出“周阮慘案,非訊不明,毋任謊言搪塞,致埋奇冤,務(wù)請(qǐng)飭通解滬”。[10]幾天后,《申報(bào)》再刊登該團(tuán)體聲明,聲稱滬軍都督陳其美對(duì)此“光復(fù)巨案”,理所當(dāng)然“有公判之權(quán)。”[11]在此情況下,伍廷芳不得不妥協(xié),允許陳其美派人出任裁判官和選派部分陪審員,接受滬軍都督府參與案件審理的全過程。
1912年3月23日,姚榮澤案在上海市政廳公開審理。該案組成了臨時(shí)裁判所,三人中只規(guī)定了座位(陳貽范中、蔡寅左、丁榕右)。按照既定程序,林行規(guī)、許繼祥為原告律師。以后,由民國(guó)滬軍都督府和司法部共同組織的臨時(shí)裁判所又先后兩次開庭審訊姚榮澤案。三次審判程序完全按照伍廷芳擬訂的程序進(jìn)行。[12]在法庭上,原告證人與被告對(duì)于案情有著不同看法,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對(duì)于案件的處理也有不同意見。在原告證人看來,姚榮澤故意殺害周實(shí)和阮式。他們認(rèn)為,周、阮的被殺,是姚榮澤對(duì)周、阮宣布山陽光復(fù)、成立軍分政府、揭發(fā)他反對(duì)革命以及控告他虧空公款,懷恨在心所致。而被告姚榮澤卻辯解說,殺周、阮并非是其本意,是地方紳士的主意。顯然姚榮澤的辯解十分牽強(qiáng)。最后主審法官當(dāng)庭宣判姚榮澤死刑。
應(yīng)該說,審判和最后的裁決對(duì)于伍廷芳和陳其美而言是皆大歡喜。審判程序基本上是按照伍廷芳司法獨(dú)立的原則進(jìn)行的,判決處姚榮澤死刑,又維護(hù)了革命的利益。
但是,作為中國(guó)近代史上重要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辛亥革命時(shí)期政治關(guān)系復(fù)雜,歷史風(fēng)云瞬息萬變。姚榮澤案宣判的前后,袁世凱已經(jīng)奪取了革命的勝利果實(shí),立憲派勢(shì)力日升,不斷侵蝕革命黨人的利益。姚榮澤案因此就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法庭宣布姚榮澤死刑后,“特假五分鐘準(zhǔn)姚犯發(fā)言”。在這短短五分鐘的發(fā)言中,姚榮澤強(qiáng)調(diào)“此案系紳團(tuán)逼迫,非出己意,哀求輕減”。陪審員研究后認(rèn)為“本案發(fā)生在光復(fù)未定、秩序擾亂之際,與平靜之時(shí)不同”,姚榮澤確是罪有應(yīng)得,但“情尚可原”,因此“經(jīng)共表同情,各無異言,并由承審官認(rèn)可,得由陪審員稟請(qǐng)大總統(tǒng)恩施輕減”。第二天陪審員內(nèi)部發(fā)生分歧,七人中有三人反對(duì)前議對(duì)姚榮澤“恩施輕減”,其余四人仍然贊同,向伍廷芳匯報(bào)此事,“力主輕減”。當(dāng)時(shí)伍廷芳已辭去司法總長(zhǎng)職務(wù),拒絕向袁世凱請(qǐng)求“恩減”姚榮澤,最后由通商交涉使溫宗堯代為傳達(dá)。4月11日,溫宗堯代呈袁總統(tǒng)文請(qǐng)求“恩減”。[5](P80)4月13日,袁世凱發(fā)布大總統(tǒng)令稱:“據(jù)前司法總長(zhǎng)伍廷芳及陪審員胡貽范等四員,先后電陳本案發(fā)生在秩序擾亂之際,與平靖之時(shí)不同,該犯雖罪有應(yīng)得,實(shí)情尚可原等語”,“依臨時(shí)約法第四十條特赦姚榮澤,免其執(zhí)行死刑。”[13]姚榮澤最終還是逃過一死。
姚榮澤案從一個(gè)面相反映民國(guó)初年革命與法律的問題。雖然專制政體已經(jīng)推翻,中華民國(guó)已經(jīng)建立,但卻沒有引起包括法律觀念在內(nèi)的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的徹底革命。辛亥革命的目標(biāo)是要建立一個(gè)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共和國(guó)家,這個(gè)國(guó)家尊重民權(quán),強(qiáng)調(diào)法治。然而,即使作為中華民國(guó)的締造者之一,陳其美不斷干涉司法,藐視法律,以手中的權(quán)力膽敢挑戰(zhàn)法律,其背后卻是追求革命利益的高尚為目標(biāo)。伍廷芳堅(jiān)持法律至上,要求全體國(guó)民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革命所創(chuàng)造的法律,其本身也是在維護(hù)革命成果,然而卻遭到陳其美的批評(píng)、諷刺甚至謾罵,受到眾多革命黨人的攻訐,最終還落個(gè)“破壞法律”的罵名。伍廷芳因此與革命黨人的關(guān)系趨于緊張,一度疏遠(yuǎn)。這從一個(gè)側(cè)面說明辛亥革命時(shí)期法律與革命之間并不和諧,而是充滿矛盾和沖突,表明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歷史狀況的復(fù)雜性和多向性。
注釋:
①學(xué)術(shù)界對(duì)姚榮澤案關(guān)注不多,僅有數(shù)篇論文論及其發(fā)生和審判的經(jīng)過,如華友根:《民國(guó)元年姚榮澤案及其紛爭(zhēng)述略》,《政治與法律》1989年第6期;楊大春:《論辛亥革命時(shí)期中國(guó)刑事審判制度的革新——以姚榮澤案為例》,《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1年第4期;李學(xué)智:《民國(guó)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等。
[1]姚榮澤案審判記[N].民立報(bào),1912-03-24.
[2]柳無忌、殷安如.南社人物傳[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2.
[3]柴德賡等.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七冊(c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guó)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2.
[5]沈云龍.伍先生(秩庸)公牘[C].臺(tái)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祥.
[6]皖南同鄉(xiāng)會(huì)致滬都督書[N].民立報(bào),1912-02-11.
[7]丁賢俊,喻作鳳.伍廷芳集:下冊(cè)[C].北京:中華書局,1993.
[8]下關(guān)海軍部侯毅電[N].申報(bào),1912-05-03.
[9]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guó)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3卷[C].北京:中華書局,1984.
[10]旅滬淮安學(xué)團(tuán)去電[N].申報(bào),1912-02-01.
[11]旅滬淮安學(xué)團(tuán)顧振黃等質(zhì)問旅滬皖南同鄉(xiāng)會(huì)書[N].申報(bào),1912-02-07.
[12]姚榮澤案審判之程序[N].民立報(bào),1912-03-28.
[13]大總統(tǒng)令[N].申報(bào),1912-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