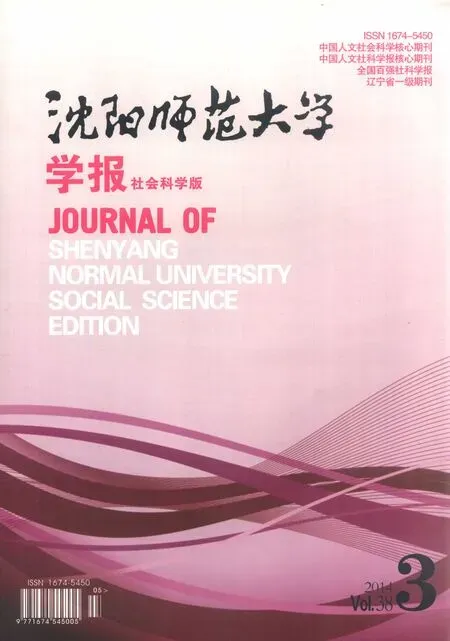群體事件的網絡參與者分析
陳秀云
(沈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隨著網絡的發展,當下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發展及演變往往和網絡聯系在一起,網絡成為群體事件的傳播、聯絡和聚集的工具與手段,同時,也為群體事件輿論的形成創造著條件。群體事件的網絡參與者除了與現實參與者重合的人群之外,還包括與群體事件有著較大空間距離的無法現實參與的支持者、與群體事件誘因無關的泄憤者、公共知識分子等評論者,群體事件的網絡參與者通過網絡言論共同營造著關于群體事件的輿論,通過對群體性事件網絡參與者的構成、參與動機及作用進行分析,對有針對性地處置群體性事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網絡化的群體事件現實參與者
群體事件的參與者個體特征并不明顯,而是以“群”的聲勢引發社會關注,這個群越大越能顯示其力量,而力量感,正是每一個參與者最需要的東西,如果分散開來,這個“群”中的大部分個體可能在現實中永遠不會惹人注目,其聲音也很難為上層聽到,因此,“群體”形式的出現,恰是弱小者借以表達自我,引發注意的一種手段,而“聲勢”則是群體事件參與者所樂見的,因為聲勢越大,對其中的任何人而言,其安全感,力量感和解決問題的希望可能越大,因此,通過種種方式營造聲勢,也成為現實群體事件參與者一種下意識的追求。
互聯網不僅是一種快捷的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種可以瞬時獲得信息全球覆蓋的信息擴散工具。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事件因上網得到解決,特別是一些弱勢者的聲音被聽到,利益被捍衛,貪官被揭發等都向人們顯示了網絡的強大力量。而現實群體事件的暴發,大多是由于特定群體主要是社會弱勢者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譬如,屢屢發生的血拆誘發的群體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即便一些涉及環境問題的群體事件,如已在中國廈門、大連等多地發生的“PX事件”,也是普通市民與作為管理者的政府及財大氣粗的企業的對峙。這些事件的現實參與者,如果不是以“群”的面貌出現,恐怕永遠不會引起注意,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交往的實質就是形成超個人的社會組合。”[1]因此,無論是群體事件的組織、溝通還是擴大聲勢的需求,都使群體事件的參與者自覺地開始實現網絡化。群體事件參與者對于力量的渴望,使他們自發地在積極參與現實事件的同時,也要在互聯網上延伸群體的力量,因此就有了借助于網絡組織、發動、溝通的群體事件。這時網上網下相呼應,虛擬與現實相溝通,讓人很難分清兩者的界限。而群體事件的聲勢由此壯大,相關人員的聲音得以在全球之內廣為傳播。
但是,與現實群體事件參與者不同的是,網絡化之后,由于失去了現實的輿論場,上網常常在私密空間中進行,因此,這類人失去了處于群體中的相互約束,如果說現實群體事件的參與者作為“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向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一種集體心理”[2],群體心理之下,他們可能失去理智,出現過激行為,如打、砸、燒等暴力事件的出現都與群體心理有關。但是,現實群體事件參與者網絡化后,他們失去了外在強大的群體壓力,也缺乏強制性的彼此約束,因此,更容易進入相對理性的世界。特別是網絡空間的開放性,使他們隨時有可能接觸到與自己觀點、意見不一致,甚至相反的觀點,這些都將成為澆滅他們心頭怒火的冷水,而這種接觸是在不易覺察中進行的,因此,他們更容易受到影響。
對于管理者而言,針對現實群體事件參與者的網絡化,最佳的方式是通過話語引導,而不是強力介入,因為強力介入使本來處于虛擬空間的事件轉化為可使現實情緒火上澆油的新事件。不易覺察的話語滲透和引導,既包括宣傳部門的相關人員巧妙的網絡宣傳,也包括與商業網站及傳統媒體網站積極溝通,及時傳播正面的聲音,這樣,使正面的聲音無所不在,網絡化的現實參與者在獲得充分信息的同時,通過自覺的網絡交流,進一步認清事實真相,對相關管理者重樹信心,為解決問題創造條件。
二、群體事件的網絡圍觀者
群體事件暴發之后,相關事件的信息會通過種種渠道得到迅速傳播。群體事件矛盾沖突明顯,利益訴求往往具有代表性,此群體的現實行動容易引起彼群體的同情與類比,而互聯網提供了一個無需現實行動卻又能夠表達個人看法的一個特殊參與方式,那就是網絡圍觀。這些人在網絡上關于群體事件的言論主要是對于強勢者的批評與質疑,而且這些質疑之聲往往顯得并不十分理智,分析少而情緒多,還有很多言論直接從個體的實際體驗出發,顯然圍觀人群之所以對群體事件關注就在于現實參與者的境遇與自己相似,他們才感同身受。網絡圍觀者主體大多是與群體性事件主體一樣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
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為弱勢群體成為網絡圍觀者創造了條件。從中國網民的構成上來看,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已達到5.91億,而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除了學生之外,還有個體戶和自由職業者、企業職工、一般職員和無業下崗和失業人員[3]。網絡占比最高的人群已不再是網絡最初出現時的社會精英階層,而是處于社會的邊緣、與主流社會存在著較大距離的弱勢階層,中國互聯網日益大眾化,同時網絡資費的減少,計算機的普及,為上述群體上網提供了硬件條件,而上網技術門檻的降低,又使上網的文化水平要求降低,個體戶、無業和失業者又是有著較多個人時間的人群,互聯網已從精英空間轉而變為大眾空間,群體事件發生后網絡上的大眾圍觀正契合了中國網民的基本構成,他們成為網民的主體也在情理之中。
無業者、失業者及一般職員等群體的人生活不寬裕,生存壓力大,抗風險能力低下,遇到困難時,解決困難的途徑少,面對強勢社會階層時,他們往往顯得勢單力孤,容易與群體事件主體產生共鳴。再加上無業下崗和失業人員及自由職業者等弱勢者都不屬于特定組織,沒有相應的組織紀律約束,日常生活中缺乏相應的規范,其言行缺乏特定的標準,遇有群體性事件發生,網絡參與的可能大,言論顧忌少,沒有底線意識,也缺乏長久的公共利益考量,往往沒有明確的參與動機,只是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憑著興趣、道義甚至憤激等情緒參與其中,成為缺乏建設性的網絡泄憤者。托克維爾在論及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過一句一針見血的名言“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4],參照托克維爾的思路我們會發現,對于網絡圍觀者而言,參與群體性事件的網絡討論,雖然大多表現出一種“義憤”的情緒,但實質上是借以表達個人對于社會不公的不滿,特別是對于那些通過非正常手段占有較多社會資源的權貴的憤怒,由于身處邊緣,他們找不到其他更好表達自己的途徑,而群體事件為他們提供一個契機,這也是促使他們自發形成群體事件網絡圍觀群體的重要原因。
網絡圍觀者由于沒有明確的動機和訴求,對于群體性事件的網絡參與往往是一時興起,三言兩語參與過后就可能轉向其他事件,不會真正留心事件的進程,只是滿足于個人情緒的發泄,一些網絡群體性事件新聞后面會出現一些與新聞內容相距甚遠的評論原因就在于此,一些人也許只是看了新聞標題,便尋到“興奮點”,隨手發了帖子,至于自己的評價是否公正、客觀,倒不是這類人群所要考慮的事。圍觀者參與的最大后果是使“群體性怨恨”在網絡空間中得到放大。這種“群體性怨恨”雖然大多出于弱勢者的無意識發泄,但卻在形成群體事件輿論場中起著重要作用,它進一步強化群體事件中的對立情緒,既突出了現實參與者的弱勢身份,又夸張了強弱之間的矛盾,對于管理者來說,當發現網絡上此起彼伏的抱怨、不滿聲浪之時,也容易失去理智,對事態做出超乎尋常的嚴重判斷,可能采取一些過激的管控行動,這時圍觀者的“群體性怨恨”成為使現實群體事件升級的催化劑。
對于群體事件的圍觀者,由于人數眾多,身份復雜,很難一一加以查證,也沒有必要一一查證其身份。但是,對圍觀言論應該加以話語分析,對其利益訴求要明了,以便于在現實中改進工作,對于那些憤激的言辭應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免的態度,不要過度反饋,采取同樣不理智的行為來應付圍觀者。因為群體事件圍觀往往是暫時的,這種網絡弱勢力量的群聚,與那種組織化很強的社會行動有巨大差異:那就是這些弱勢者由于缺乏共同的領導、信仰等粘合劑,由于身份的匿名性,彼此之間也很難相互了解與溝通,因此,他們很難達成共識,即便達成某種默契,這種關系也相當脆弱,網絡上一言不和就一拍兩散的現象并不少見,群體事件的網絡圍觀也是這樣,由于圍觀者與事件沒有直接聯系,缺乏固定的支撐因素,普通圍觀者對于群體事件的注意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新事件的出現而淡化和轉移,很難堅持對于類似事件的持續關注和熱情。這也使群體性事件的網絡圍觀帶有匯聚快消散也快的特點。如果相關部門不適當地干預這類圍觀,或許會誘發圍觀者新的興趣點,從而強化事件的影響。因此,面對網絡上的圍觀者,相關部門也許靜觀其變比盲目行動要有利得多。
三、群體事件中的網絡公共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作用的發揮依賴于“公共領域”,互聯網出現之后,在無比寬闊的網絡空間中,幾乎讓人看到了“公共領域”出現的可能性,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在網絡上對公共事件的參與中逐漸為世人所熟悉。群體事件發生之后,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充滿智慧與理性,客觀與平衡,與參與者和圍觀者過于情緒化的聲音顯得迥然不同,正是這種聲音更容易為群體事件的解決提供建設性的思路,應該引起各方面的重視。
公共知識分子之所以在群體事件中能夠秉持公心,拋開私利,與其特定的身份密切相關。從社會地位上看,作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網絡世界的先行者,對于網絡的作用與功能的熟稔,使他們清楚地知道網絡上言論傳播與擴散的迅速性與廣泛性,其輿論影響力往往非某一特定人群可以隨意控制,哪怕是發言者自己,一旦言論上網,其影響將不依個人意志而轉移,因此,他們不會任憑情緒泛濫去鼓動群體事件的輿論風浪;同時,他們與群體事件參與者和管理者都保持著一定距離,大多數底層抗爭的群體事件與他們并無直接的利益關系,他們不會像群體事件參與群體那樣由于身處其中而容易失去理智;他們與管理者也不同,管理者作為群體事件的抗爭對象,被迫陷入一個強烈沖突的場域中,雖然管理職責要求他們保持理智,但作為具體的人,他們也很難擺脫情緒的控制和本能的自我保護反應,這樣,也容易使他們在執行自身職責的時候受到情緒左右,而公共知識分子卻可以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去觀察和思考事件本身。他們基于對于公共事務的關心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慮,能夠“就事論事”地積極參與這類事件的討論,有時還會參與這類事件的處理過程,成為該事件輿論傳播中的“意見領袖”。正如傳播學對于“意見領袖”的定義一樣,他們“領袖”地位的形成不是由于其外在的權力和地位,而是由于較高的政治覺悟、文化程度、思想深度和相關專業知識水平,使其對事態的分析,顯得公正客觀、目光遠大、利國利民,讓人不得不信服,從而自覺地跟從其后。在一些群體事件中那些起相當作用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多數是這樣的人,譬如在沈陽商鋪歇業事件中,向有關部門提出緊急提案的遼寧省政協委員莊廷偉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提案,就是完全出于對于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心,與私利毫無關系。正是在他的推動之下,才使該事件引起各方關注,使之在較短的時間之內得到妥善解決,顯然在這一事件中,莊廷偉是一個深度參與者,成為一個特定事件的意見領袖。
對管理者而言,應該認識到公共知識分子對于解決群體事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處置群體事件的時候,應該關注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包括他們的博客、微博等,對他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應該加以理性的評判,不能因為他們可能與自身的思路不完全一致就求全責備,也不能因為他們的立場可能與群體事件參與者相一致就把他們與群體事件現實參與者完全劃等號,更不能對他們的“意見領袖”地位心存顧忌,甚至是妒忌,進而對之進行打壓。而是應該對之加以尊重和理解,以寬廣的胸懷去面對他們的批評,以真正服務于公共事業的心理解他們對于國家前途的憂慮,使自己的方針政策得到公共知識分子的理解,這樣,使由于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具體的群體事件停留在事件本身的層面,保持在人民內部的層面,而不是故意升級事態,把公共知識分子推到自己的反面。
網絡化的現實參與者、圍觀者和公共知識分子構成了群體事件網絡參與者的主體,他們以不同的參與方式共同營造的群體事件網絡輿論,進而影響整個群體事件的方向,既可能促進事件的合理解決,也可能激化矛盾,關鍵在于網絡參與者是否能夠向著共同的目標——化解矛盾,平衡利益,解決問題的方向而努力,是否能夠對于事件進行理智的判斷與分析,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去理解事件的發生發展的規律,而這些,都有待于相關群體包括管理者群體和群體事件參與者群體在內的不同群體的整體政治素質、文化素養及社會公德水平的提高。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曾經富有預言性地指出“不管未來的社會依據什么路線加以組織,它都必須考慮到一種新的力量、一股最終仍會存在下來的現代的至高無上的力量,即群體的力量。”“我們要進入的時代,千真萬確將是一個群體的時代。”[5]盡管他從精英的視角對群體充滿偏見,但是,他卻清晰地看到了群體對于社會變革具有的巨大力量,當下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種種社會矛盾的突出,使原有的觀念受到嚴重挑戰,網絡上不同群體的話語沖突明顯,要想使社會保持和諧,必須關注群體的變化與發展,正如任繼愈先生所言“現代社會的進步,要靠群體認識的提高,群體認識的覺悟。一個哲學家啟發一個時代的歷史已經過去,以后,時代發展的大趨勢是,一個覺悟了的群體來推動社會。”[6]當我們對群體事件的網絡參與者進行分析的時候,目標是讓我們對于這些群體事件相關者有更多的理解,同時以平等溝通的態度去面對他們的利益訴求,理解他們就是理解我們的社會,理解社會和諧之真義。
[1]韓民青.人類的組合:從個體、群體到整體[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246.
[2]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16.
[3]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13-07-17)[2013-10-16]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rdxx/201307/W020130717431425500791.pdf.
[4]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02.
[5]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6.
[6]任繼愈.任繼愈對話集——覺悟了的群體才能推動社會[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112.
【責任編輯 王鳳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