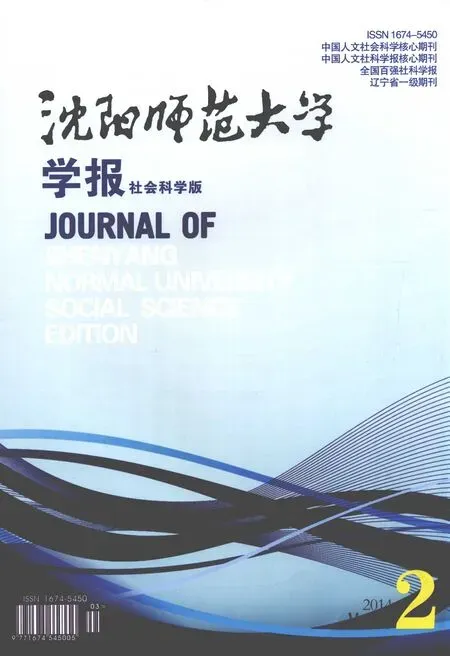略論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
楊 梅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00)
古希臘文化已經離我們相當遙遠,但它仍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成就對現代人進行著警示與提醒。這種啟發是多方面的,對當代人類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這句名言催生著人類思想的萌發及視野的擴展,亞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夠提出這個命題,與其所生存的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拋開有關這個命題的爭議,探究亞里士多德提出該命題的原因,找出該命題與中國傳統制度的相似性,對中國當今的法理學研究有著重大意義。
一、城邦:古希臘人權利意識產生的基石
城邦(英語:City-state)亦稱“古代城市國家”,音譯“波里斯”。古代國家的一種組織形式,通常是由一個城市和附近的農村構成,領土面積狹小,居民人數有限。歷史上的城邦通常是大文化圈的一部份,公元前8世紀左右,古希臘城邦陸續形成[1]。城邦的起源一方面與希臘半島的地理環境有關。另一方面是海外殖民。海外殖民城市是希臘城邦的發源地。公元前十三世紀,古希臘受到亞蓋亞人的入侵,這些移居海外的希臘人為了防衛當地人民的報復,不得不筑城聚居,這些筑城聚居的地方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進而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國家。城邦便出現了。這種城邦在學術上又被稱為海外殖民城邦。在海外殖民城邦中,貴族階級的統治取代了王權制度而存在。在海外殖民城邦的影響下,雅典、斯巴達等希臘本土國家也逐漸城邦化了。
城邦的中心所在地是城市,城市是城邦經濟活動的中心。以希臘為代表的希臘城邦商品經濟非常發達。杜蘭認為,“愛琴海之土壤甚為貧瘠,幾乎所有地區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極簡單之農作亦甚困難,令人極為沮喪。僅有冒險性行業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欖與葡萄,促成愛琴海之文明。”“因為土地貧瘠,海岸及港口眾多,遂誘使愛琴海人民從事貿易。因為人民堅定勇敢,富于發明創造,遂使其贏得愛琴海的市場,通過這個商業帝國,雅典在伯利克利時期獲得權利并達到文化的最高峰。”[2]古希臘各城邦借用便利的航海條件,發展海上貿易,同時帶動了各城邦內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繁榮則促進的希臘民主政治的發展。這些都是古希臘人權利意識產生的物質基礎。
城邦的特點是規模小,人數少。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曾期望在一個城邦之中,“每個公民目力所及就能看到所有的人”[3];現實之中,即便是全盛時期,斯巴達的公民人口不超過1萬人,到了公元前5世紀,則只有6 000人[4],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前,雅典公民人數也只有4萬左右。[5]這種“小國寡民”的格局,為實行直接民主,城邦成員行使自己的權利提供了可能。因此古希臘人認為政治就是城邦的公共事務,關心城邦事務,將城邦事務視為自己的事務,這是公民的一種獨特的政治心態。因而,在古希臘人的眼里,參與討論城邦的事務不僅僅是一項權利,更是一項義務。“在城邦中有效充分地采取行動表達意見,在希臘人眼中就是善行,而善行恰恰是人道主義的核心內容。培育人的善行,就稱為城邦教育的相關內容。希臘人道主義是在城邦內運作的價值取向和教化方式。”[6]在希臘各城邦中,參與公民大會,擔任各種公職稱為人民對城邦應盡的義務。那么,在古希臘人的意識形態中,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種觀念呢?這是因為,由于城邦規模小,公民個人利益與城邦的命運密切相關。城邦繁榮強大了,公民就能爭取自由和獨立。“因而,致力于城邦與公民生活之間的和諧統一便成了每個公民的基本信念及價值追求。”[7]從外部環境看,無論是古希臘城邦之間的爭斗還是強大的波斯帝國的威脅,都使得古希臘人不得不正視自己的命運,在危機意識之下積極投身于與城邦發展和生存有關的公共事務之中。
如果我們把先賢亞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句話放到古希臘城邦政治經濟背景下分析,那么它又有怎樣的意義呢?
二、“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
亞里士多德“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句話又該怎樣理解呢?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初的社會組織是家庭,家庭為滿足人的日常需要而存在,當人們的需求擴大,若干家庭聯合為村落,以滿足人們日益增加的需要。最后,若干村落組成國家,滿足人們的所有需要,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創造人的機制和男女的自認本性使得家庭作為一個基本單位而具有自然的根本,因而由家庭發展而來的城邦在本質上也是自然的。而從家庭到城邦的這一過程中,貫穿著人對美好生活和幸福追求的天性。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幸福包含著一種利他主義的道德準則:“善人為他的朋友和國家盡其所能,在必要的時候甚至獻出生命。”結合當時的城邦政治背景來考慮,幸福就是參加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城邦之于希臘人就如同共和國之于羅馬人,它首先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抵制個體生命無益性的保證,它是一個使希臘人擺脫生命的無益性,專為凡人的相對長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話)保留的空間。”[8]這樣人具有天生的政治性就不難理解了。
古希臘特殊的社會環境催生出亞里士多德這樣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同時,城邦所享有的權利令當代中國的一些學者羨慕不已。但是考究古希臘人的生活環境,他們所享有并行使的權利與當今中國學者所提倡的權利在涵義上并不相同,因為前者在內容或者說意義上還包含有義務的一個方面。
三、“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對當代法治實踐的意義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是在城邦制度高度發達繁榮這樣一個背景下提出的。從表面上看,古希臘各城邦的公民參與城邦事務是在履行自己的權利,而實質上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是他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城邦與個人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則促使每一個人必須這么做。這一命題雖然久遠,但對當代中國的法理學研究及法治實踐仍有這重大的借鑒意義。
中國的歷史與古希臘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由農耕社會譜寫的中國歷史強調公民對國家所應盡的義務。古代中國的各種規定、規則中也是強調了臣民的義務,有學者將其稱為“義務本位”。以張文顯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在將西方的法治思想引入中國的同時,也大力倡導在中國推行“權利本位”主義,并在“義務本位”與“權利本位”之間,強調“權利本位”的優越性,主張中國以往立法的指導思想是“義務”。而如果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則要拋棄以前的思想,構建一個以“權利”為基礎的社會。
由此,筆者想到了民國時期一位著名的學者,當今社會將其定義為法社會學家—吳經熊。他用一種哲學、宗教的思想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法律資源,從而得出的結果是東方法律哲學思想與西方法律哲學思想存在深層次的可通約性,既內在的一致性。他的這一思想給當代中國構建法學理論研究體系帶來的啟示是我們在進行研究時,必須在法學理論研究方法與研究視野中保持一種較高的姿態和一種包容的心態,用一顆寬容而又熾熱的心來觀察和考量這個世界上所存在的諸多不同類型的法律文化,通過發現他們之間某種屬性,而達到一種完美的統一[9]。如果用上述方法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古代的“義務本位”文化與古希臘的權利文化在內涵上存在著一定的統一性。西方的歷史上并不是只強調權利而忽視義務,同樣,中國的歷史也并不是只強調義務而忽視權利,只是二者的側重點不同。這種差異是由不同的歷史文化引起的—古希臘的文化可以被稱為“海洋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則可被稱為“農耕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不能拋開中國的歷史,當代一些法學家所提出的“權利本位”并沒有可以生長的歷史土壤,其可行性值得研究。
總的來看,導致古希臘和古代中國對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側重點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民意表達與反饋機制是否通暢、有效。在古希臘,由于處在“小國寡民”的形勢之下,普通民眾與國家的執政者有著充分的溝通空間,民意能夠很迅速、順暢地傳達給執政者。而且,經過與貴族、獨裁者等群體的不懈斗爭,尤其是在像雅典這樣的發達城邦之中,普通民眾通過貝殼放逐法、信任投票制、卸任檢察制等監督機制,形成了對執政者的有效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執政者也無法營造專制所需的距離感與神秘感,必須接受與平民在“同一屋檐下”議事的局面,也必須及時對民意作出回應,無論是其支持還是反對也好。從現在尚存的古希臘遺跡看,眾多公共聚會場所的斷壁殘垣依然提醒著我們古希臘人曾經有過的那段歷史。
這種情況下,古希臘人的民意能夠非常迅速地傳達給執政者,而執政者也需要及時將其意見反饋給民眾,倘若不符合民意,雙方進一步的協商、溝通也能順暢地展開。這樣一種通暢、有效的表達與反饋機制,是維系民眾參政積極性和監督執政者行使權力的強有力保障。民意表達與反饋機制運轉越順暢,民眾越能感受到自己的聲音受到重視,參政積極性也就越高,對執政者的監督和制約作用也就越能發揮出來。反之,當民意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回應,甚至打壓,那即便最初普通民眾對參政帶有濃厚的興趣,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磨殆盡。
而在古代中國,之所以會出現“輕權利、重義務”的情況,與民意表達與反饋機制的失靈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普通民眾雖然沒有近代以來的“權利意識”,但對自己切身利益的關心從來沒有漠視過,當其認為自己利益受到損害時,依然希望通過不同渠道尋求救濟。雖然中國古代歷代執政者向來主張“息訟”思想,極力增加民眾訴訟的成本,但在地方上,由地方宗族領袖、鄉紳等主導的民間調解制度的充分運行,實際上也說明了民眾對于自身利益關注的情況。
然而,為什么在中國古代,普通民眾對于自身利益的關注沒能像古希臘那樣上升到政治層面的高度,既有現實的經濟、環境因素,又有執政者和民眾自身的因素。首先,從經濟、環境因素來看,自秦代開始,中國就是一個擁有數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至少為數千萬的超級大國,以當時的交通運輸條件,從國境的最北端走向最南端,經年累月并不夸張,要全國民眾像古希臘城邦那樣聚集在一處參政議政,顯然并不現實,因而,古希臘式的“政治動物”在中國古代缺乏生存空間。
其次,從執政者和民眾自身的因素看,前者為了維系中央集權尤其是皇權獨大的地位,有意與民眾保持距離,依靠強大的軍隊和官僚集團,在民眾心目中營造出超出想象的權威感和神秘感,使得民眾望而生畏,而執政者也努力向民眾灌輸“三綱五常”的思想,使得其在民眾面前總是高高在上,民眾對其往往只能俯首聽命。這種刻意營造出的不平等的氛圍,也使得民眾難以像古希臘人那樣能夠挺起腰板,正常地與執政者交流。而后者在執政者的威壓之下,本身就對政治話題不敢抑或不愿發生興趣,清末民國時,見諸于大大小小茶館墻壁之上的“莫談國是”,就是很好的例證,而民眾在對待政治問題時,本身也會做出一番付出和收益上的權衡,當他們認為自己的政治訴求無法得到滿足,甚至會遭到官方威脅和打壓時,基于對自己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量,他們不會輕易越過“雷池”,只有在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實在難以維系生存時,他們才會以最為激烈的手段作出反應。遺憾的是,那個時候,民眾與執政者之間已經失去了和平、冷靜交流和協商的時機。表現在中國歷史中,那就是一個王朝的官民矛盾往往集中爆發于其末世,最終在一場激烈的農民戰爭中迎來改朝換代。
如今,要想中國人提高參政議政的興趣,為了自己和國家、民族的利益認真對待政治話題,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我們需要借鑒古希臘的經驗,也需要從我國古代的社會發展中吸取經驗和教訓。現在看來,隨著改革開放和法治改革的進行,當下,普通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經非常高漲,即便是在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經過了數十年的摸索,人們已經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利益與集體、國家的利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只有更大層面的利益得到協調和實現,屬于自己的利益才有更好實現的可能性。以現在的村級換屆選舉為例,盡管仍存在著“賄選當選”的情況,但越來越多的民眾對于選出能代表自己和集體利益的領導干部更加重視,而不是再看重那點蠅頭小利,相對于過去,這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而從物質條件看,生活條件的提高、交通的便利、網絡的發達,使得民眾參政議政有了更充分的物質基礎,近年來,“網絡反腐”的屢屢奏效也說明了這一點。
四、結語
2000多年前,古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熱衷于民主政治,盡管他們的民主存在不少缺陷,但為后世民主政治的發展開創了先河。2000多年后,當中國人在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時,仍有值得從古希臘學習的地方。要想使中國人改變過去的習慣,對參政議政發揮出應有的熱情和積極性,就要從多方面營造出便利的條件,尤其是建立起一個暢通、有效的民意反饋機制,使得普通民眾能夠看到的參政議政給自己帶來的現實好處,這樣,“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的斷言才會在中國實現。
[1]《法學詞典》編輯委員會.法學詞典[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
[2]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希臘的生活(上冊)[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3]顧準.顧準文稿.[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544.
[4]羅多德.希羅多德歷史[M].王一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41.
[5]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12.
[6]杜麗艷.人性的曙光[M].北京:華夏人民出版社,2005.
[7]張艷.城邦:古希臘人文精神的基石[J].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8]漢娜,阿倫特.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G]//文化與公共性[M].北京:北京三聯書社,2005.
[9]姬小康,吳經熊.法律哲學思想研究[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4).
【責任編輯 曹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