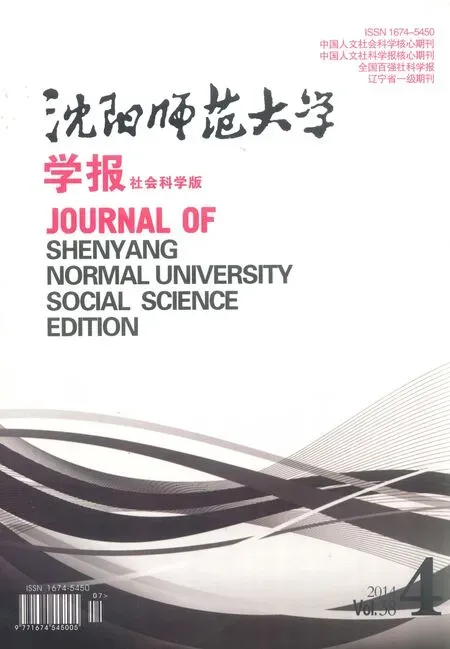生態思想視角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初探
郭秀偉,趙廣發
(遼寧中醫藥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沈陽 110040)
【學術熱點·生態文明建設專題研究】
生態思想視角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初探
郭秀偉,趙廣發
(遼寧中醫藥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沈陽 110040)
生態批評理論雖然起源于西方,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孕育著樸素的生態思想。在中華文明發出黎明曙光的時代就產生了原始的天命觀,隨后道家、儒家、法家和釋家都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自己的論述,從而產生了中華文化中最初的生態思想和倫理價值觀。這些傳統文化的精髓對我們今天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解決我們面臨的生態問題有著巨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生態思想;道家;儒家;佛家
在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愈發受到學界重視的今天,許多人言生態必稱西方,要以西方的生態思想和生態批評理論來指導我們對生態文學的研究,但殊不知在淵源的中華文化中早有古代先賢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生態主義的解析。道家、儒家、法家和釋家從不同的角度對人與宇宙,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闡述,從而產生了中國古代最初的生態思想。
一、生態思想
生態思想的定義可能有多種多樣,但是所有的定義都有一個核心內涵,那就是人們都認為生態思想是一個哲學概念,是人們世界觀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所體現的是人們對周圍生態環境內部結構的一種認知,以及建立在這種認知基礎之上的對人與周圍環境和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思辨考察和整體把握。生態思想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存在著一種永恒性。人與自然的矛盾自古有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永恒話題。生態思想的核心問題是從新確立人與自然的關系,調整人類的行為從而預防或解決所面臨的人與自然的矛盾。
生態思想也蘊含在浩瀚淵博的中華傳統文化當中,中國古代的智者以敏銳目光和哲學的思辨考察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中國的生態思想史揭開了最初的篇章。
二、儒家的生態思想
兩千年來,儒家文化對中華文明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農業文明的一種產物,儒家思想一向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它提倡“忠恕”和“仁愛”。
《論語·里仁》篇云:“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指點曾參說他的道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曾子豁然頓悟,說他明白了。孔子出門,其它的門人問曾子孔子的話是什么意思,曾子立刻回答道夫子的學說僅僅體現的是忠恕之道。孔門師徒的這一段對話雖然簡潔但主旨明朗,即孔子的學說圍繞一個基本思想展開,這個基本思想就是忠恕之道,換而言之,孔子學說的核心內容就是忠恕之道。而在《禮記·中庸》篇中還有記載:“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這段記載說明“忠恕”的含義就是“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之道應用在人際關系上就是要由己推人,將心比心,換位思考。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要擺脫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時常地捫心自問,我們善待自然了嗎?我們善待動物了嗎?恕的實質是嚴于律己,不貽害他人,而恕的思想則要求我們在對待物的態度上也要做到由己推人,以悲天憫人之心,以眾生平等的姿態對待我們的自然和生態,做到《中庸》上所說的那樣:“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把人與自然的發展變化看做是相輔相成的和諧運動。[2]
儒家思想的另外一個核心就是“仁愛”,它也包含著深刻的生態倫理觀。仁是儒家傳統的道德精華,也是孔子倫理道德體系的最高原則。程顥《識仁篇》中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由此而知,仁是一種至誠無妄、與物無對的修養境界,是最高的道德范疇。孔子仁愛思想內涵豐富,基本內涵包括愛人、孝悌、忠、恕、恭、寬、信、敏、惠、禮等。仁的思想當中蘊含著一種博愛的胸襟,一種民胞物與的情懷。《論語顏淵》篇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韓愈《原道》言:“博愛之謂仁。”韓愈一生以承載道統為己任,而以博愛為基點的仁正是道統的思想內核。張載《西銘》中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意味著達到對自我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照與覺知,由此而能“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一人”。這種“成于中,形于外”的“博愛”情懷恰如日光一般永久地普照大地、澤被萬物。
除了對生態思想進行哲學上的思辨之外,儒家思想還對生態倫理做了具體的規范。孔子曾經說過“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這種闡述提出了“時禁”的觀點,強調人對于自然的利用要以其時,循其令。孔子還強調“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在數量上對漁獵進行限制。孟子也說過:“不違農時,谷不可勝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意思是說如果兵役徭役不妨礙農業生產的季節,糧食便會吃不完;如果細密的漁網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魚,魚鱉就會吃不光;如果按一定的季節入山砍伐樹木,木材就會用不盡。糧食與魚鱉之類的水產吃不完,木材用不盡。《荀子、王制》也記載“五谷不食,果實不熟不現于市;木不中伐,不先于市;禽獸不中殺,不現于市”。他自己也曾說過:“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故山林不童而百姓余材也。”以上三位儒家大師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前衛思想觀念。作為人類發展的全新攻略,可持續發展為人類持續生存開辟了嶄新的途徑。雖然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空前發展,但人類發展卻似乎陷入嚴重困境,可持續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當之無愧是人類最高瞻遠矚、最科學文明、最前衛進步的發展觀,堪稱人類發展觀最史無前例的偉大變革。
三、道家的生態思想
道家經典和道家先賢也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其生態思想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人應與萬物平等相對,和諧共處。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種論述表明,人和萬物是平等的。“道”是老子學說的核心思想,他認為“道”是包括人在內的宇宙自然萬物的本體,也是他們發展運行的規律。人與萬物統一于“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應該遵循天道的運行法則,而天道的運行則崇尚“自然”,不應有人為干涉的痕跡。人要與天道合一就要遵循其自然本性來生活。莊子把這一學說進一步發展,提出了“物無貴賤”的理論。他指出:“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3]在莊子看來,世間萬物雖有差別,它們在自然體系中位置各不相同,但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并無高低貴賤之分。人與自然是統一的,即所謂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4]。
第二,人與世間萬物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宇宙萬物,自然生態各系統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呢?老子認為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整個大自然就是一張巨大的由萬物構成的有著相應相求、相依相存關系的生態之網。這張大網有可能稀疏,但卻沒有一環缺失。人也是這張大網中的一環,而絕不是處于這張網的中心位置。人與這張大網中的各個環節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產生著各種各樣的聯系。另外,自然之網的各個環節的相互作用和平衡方式遵循“損有余而益不足”的原則。自然生態間的作用過程,多余時減少些,不夠時補足些。“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自然的法則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由此可以得到生態之平衡。[5]人類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類不能光對自然索取而不給予她回饋。
第三,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應遵循適可而止的原則。老子認為,人類不僅要了解自然、尊重自然,更要保護自然,而保護自然的關鍵在于了解自然生態中萬物所擁有的那個“度”。人類對于自然的利用不應是殺雞取卵、涸澤而漁的方式。人類對自然的利用應該有著長遠的眼光,遵循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老子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世界上最大的禍患莫過于不知足,最大的過錯莫過于貪得無厭,只有認識到事物的度,知止知足的滿足才是世界上最長久的滿足。老子還說:“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癡迷于某物必然會導致巨大的奢靡浪費;囤積居奇,欲斂天下之財為己有注定會帶來太多的損失。所以知道知足就不會帶來屈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招致危險,這樣就可以保持長久。老子認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人類應該克制自己的欲望,要做到“知足”,在向自然索取的時候應該做到“知止”,這樣就不會帶來危險。
四、佛教的生態思想
佛教雖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傳入中國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并且在佛教典籍保存方面中國做的比印度還要好。作為東方文明智慧的結晶,佛教當中也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佛教的緣起論認為,任何事物不可能永恒、孤立地存在,必須依靠因緣條件的和合才能產生并且存在,一旦必須的因緣條件消失,該事物也就化為烏有。“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因果定律,稱之為“緣起”。佛教認為人與自然萬物共存于同一個生存環境,彼此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根據佛教推崇的輪回思想,人又與其他有生命的物體有著或親密或疏遠的親緣關系。佛教經常借用《華嚴經》中帝釋天的因陀羅網來比喻生態系統相互交織、錯綜復雜的關系。因陀羅網由無數璀璨耀眼的寶珠串聯而成,每一顆晶瑩剔透的寶珠都映襯出其他寶珠的光影,寶珠之間互相映襯,彼此的影子相互交疊,重重疊疊,紛繁蕪雜。華嚴學者慣用此例闡述一與一切的關系——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與一切,相映相含,彼此交融,重重無盡。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緣起論最能體現人與所生活其中、所依賴的自然及其各種物種之間的相互依存、共生互動的關系了。
佛教的“無情有性”主張是當前佛教生態倫理的重要內容,并對西方的一些生態倫理學家產生重大影響。所謂“無情有性”是指沒有情識的山河大地、花草木石等無情物都是清凈佛性的體現,無情有性,故而亦可成佛,甚至無情也可講法,如蘇軾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凈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在生態危機日趨嚴重的今天,佛教的這一理念得到一致的認可和推崇,它承認沒有情識的山川大地、花草木石有著不依指人類的自身價值,人沒有理由自認高于或是優越于它們,這對西方的大地倫理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佛教的各宗都認為世間萬物不論有情無情都身具佛性,正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佛教的慈悲心就要求人們以慈悲之心對待世間萬物,“掃地怕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照燈”,關愛生命,善待自然。
結語
今天,我們生活在由工業化和信息化相互交織的時空當中,面臨日趨嚴重的生態問題:全球變暖、污染嚴重、霧霾肆虐。種種生態污染問題要求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社會發展之路。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從古代的傳統文化中汲取樸素的生態智慧,學習他們善待萬物的情懷,領悟他們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以全新的姿態走向生態文明。
[1]孔子.論語[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
[2]苗澤華,孫增輝.我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及啟示[J].商業時代,2009(12):123-124.
[3]莊子·秋水
[4]莊子·齊物論
[5]陳銘彬.老子生態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J].學術時代,2006 (10):36-38.
【責任編輯 曹 萌】
I109
A
1674-5450(2014)04-0013-03
2014-02-15
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L13DWW013)
郭秀偉,女,遼寧綏中人,遼寧中醫藥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