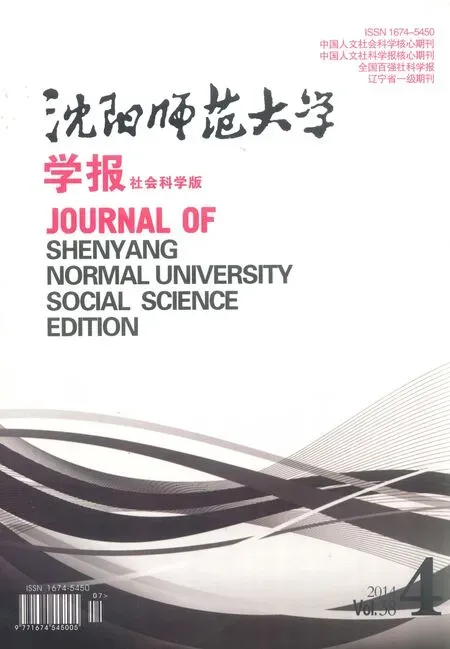郭象美學:中國美學從“無”到“空”的關捩
李小茜
(天津社會科學院 文學所,天津 310012)
郭象美學:中國美學從“無”到“空”的關捩
李小茜
(天津社會科學院 文學所,天津 310012)
禪宗美學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美學與藝術的發展,它迥異于老莊以道見器、器道合一的兩極思維,承接了郭象玄學開辟的經驗世界,強調以單刀直入的體悟切入佛性。首先,郭象玄學的崇“有”、重“感”將莊子式大氣磅礴的自然孤立成一個個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片段,其本體論的建構方式與禪宗美學最為相似;其次,郭象玄學的“自性”說,認為萬物圓融自足,世界的意義在其本身,與禪宗美學闡發的“真即實”的觀念相通;再次,“妙悟”指向郭象截斷時間義之上的絕對永恒,將心與象融入了不確定的空靈境界。所以說,郭象玄學作為魏晉玄學的集大成者,上乘老莊、下啟佛禪,承擔著中國美學從“無”到“空”的過渡。
獨化;“心”本體;真;妙悟
一、一元本體論的歷史演進
始約漢代,佛經傳入中國,本土文化與佛教文化出現了此消彼長的交融過程。及至魏晉,在儒道釋共相發展的條件下,帶有中國特色的禪宗出現了。縱觀中國哲學史本體論的歷史演進,禪宗“心”本體迥異于老莊的兩極思維模式,承接著郭象玄學開辟的經驗世界,它們共通的一元本體論思維為中國美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與方向。
《周易》的世界中存在著“象”與“道”的二元結構。“道”作為老子哲學中的專有名詞,意在表示宇宙的實體與動力。“無”作為天地的本始,“有”作為萬物的根源,都不過是“道”的指稱,表明“道”由無形質落實向有形質的運動過程。莊子用“螻蟻”“屎溺”之類的具體異象來闡釋“道”無所不在的道理,但仍然擺脫不了它將“道”置于物眾形的地位。孔子也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們的哲學充滿了悖論,其本體論從未解開“道生物”,抑或“物生物”的死結。
兩晉是中國哲學發展中的一段激烈變革時期。“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晉書·王衍傳》)這概括了王弼玄學的旨要,也表明王弼開始瓦解了漢代經緯哲學的宇宙圖式。王弼主張以“無”為本,其“有”“無”體用的結構模式仍是道家思想的具體延伸。及至后來的“六家七宗”關于世界意義的評判上,依然沒有擺脫有無對立的模式。如支遁的即色宗,他說:“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雖色而空。知不自知,雖知而寂。”色是存在的,但沒有自性,所以說它是空的。支氏認為色沒有自性,也沒有本體,自然沒有超出色空二分的觀點。心無宗的代表僧肇說:“心無者,無心于萬物,萬物未嘗無。”他的觀點沒有突破有無之分的界限。其他的“本無宗”“識含宗”“幻化宗”“緣會宗”等均沒有跳出以往哲學二元論的基本思路。雖然中國哲學一直強調“天人合一”,但是我們看到哲學家們一直是在區分天人之別的基礎上,努力地將之會歸為一。
郭象“獨化”論消解了形而上的本體,將萬事萬物的發生歸之于自身。郭氏說:“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莊子·齊物論注》)“無”并不是王弼貴“無”論中的“無”,它指向絕對的空無;“有”則是裴崇“有”說中的作為本體之“有”。郭氏認為“有”之自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條件使然,從根本上取消了主宰的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少學者認為郭象才是“徹底的自然主義”,或者可以說是“徹底的現象主義”。郭象徹底突破以往現象本體的二元對立,為中國傳統思維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認知路徑。中國美學史中,郭象首先用哲學的語言肯定了物之美。“物”之美雖然在道家美學中始終沒有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卻成就了爾后中國美學的轉向。張節末教授說:“郭象的自然觀將莊子式的大氣磅礴的自然轉化為個體的、片段的自然現象,因此眾多的自然現象可以被當作審美觀照的對象而孤立起來,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禪宗美學自然觀的前導。”[1]
禪是本土文化與大乘佛學融合的文化產物。禪宗的基本原則:“不二法門”。“‘不二法門’就是超越一切‘分別智’,建立的一種大智慧。”[2]“不二法門”的核心觀點就是不著邊見。《般若經》說,“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即如如相。”大千世界的如如沒有邊見之分,是真實的意義存在。皮朝綱認為:“禪宗把‘心’作為本體范疇,作為自己在終極信仰中安身立命的源點,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建構了心性本體論。”[3]禪宗“心”性本體論是一元論,迥異于中國的傳統哲學,為中國美學提供了新的美學智慧:從經驗的世界,轉向了心靈的境界。這個轉換包括了兩個層面,中國美學的外在世界從莊子的天地,經郭象的自然,轉向禪宗的境界;中國美學的內在世界從莊子的以道觀之,經郭象的以物觀物,轉向禪宗的萬法自現。[4]縱觀中國美學的發展,郭象玄學開啟的物之美,終結了老莊虛無的天地,又開啟了物之外的境界大美。
禪宗的一元本體論將大千世界歸之于“心”的同時,卻將佛性還俗于具體的感性世界,從客觀上肯定了現實人生。它是絕對平等、超越邏輯、不可言說的真理。從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它顯然完全跳出了中國哲學中二元分別、道器分別、天人分別、主客分別的兩極思維模式,強調“分別是魔鏡”,這個顛覆性的原則為中國美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契機。
二、外在世界的轉換
歷來儒家重視善與美的統一,道家則重視真與美的統一。重視“真”是玄學諸子的一貫傳統。王弼之真,指涉本體的“道”。嵇康、阮籍之真,較王弼更進一步,將“真”與個體的“心”“神”聯系起來,但他們更多關注的是人的精神性,而非個體的感性。郭象融匯儒道,統一了真與善。如“真在性分之內”(《莊子·秋水注》)、“所以跡者,真性也。”(《莊子·天運注》)中所說,“真”與“性”共相依存。這種統一與匯通打開了對個體性情的關注。他說:“凡非真性,皆塵垢也。”(《莊子·齊物論注》)郭氏將個體感性之“真”提升至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為了肯定萬物存在的個體意義,郭象說,“物各有性,性各有極”。(《莊子·逍遙游注》)。“性”是一物之所以能成為該物的內在規定性,它確定了物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莊子·山木注》)郭氏認為任何事物皆性之必然,“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莊子·齊物論注》)物自生而不假外求,其存在、變化和發展都賴于自“性”。郭象賦予物個體性、平等性、完美性的特征,開辟了個體存在之“真”。郭象玄學的美學意義在于從混沌的天地中區分了“象”與“物”,中國美學發展從虛轉實。宗炳的“圣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畫山水序》)、顧愷之的“以形寫神”正是這一時期美學追求的印證。
禪宗美學對“真”的重視將郭象玄學的“取象”邁向了“取境”的藝術追求。馬祖云:“真即實,實即真。”“真即實,實即真”表達了禪宗關于世界意義的價值判斷。“真”是主觀價值判斷下的意義世界,“實”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世界。“真即實、實即真”意為存在即真實,世界的意義只在于其本身。有學者也曾指出:“中國哲學史上,禪宗確立世界本身的獨立自足意義,認為世界的意義在于其‘自性’中,郭象的崇有哲學與其最為相似。”[5]“真即實,實即真”是中國美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命題。這個命題的提出摒棄了個體之外的本體,又超越了主體的審美態度,消除了主客之間的界限。形而上的困惑在這里豁然開朗,事事無礙任物自由興現成為了可能。《五燈會元》卷17中,青原惟信禪師有一則語錄: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體歇處,依然是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禪師所言的三個階段代表了我們感應外物的運思方式與邏輯順序。第一個階段是以樸素的稚心去感應外物,物與我之間隔著理性的屏障;第二階段是以認識論的哲學思維來感應山水,通過具體的物象來尋覓與內心深處對應的聯系及意義;第三個階段即為摒棄語言與心智活動而回到物象的本原,讓物象各依天性而自由興現。山水從概念中的山水,進階到主體觀照下的山水,再復歸于山水本身。經過這三個階段,我們發現了山水依其自身而顯現的美,它超越了分別,具有般若的智慧。這個過程與前面我們提到的中國美學的發展歷程相吻合:從莊子的以道觀之——郭象的以物觀物——禪宗的萬法自現。禪宗中所謂的“一念心清凈,處處蓮花開”“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是一次次去掉分別心,打破主客橫杠的純粹個體生命體驗。禪宗提供的美學智慧,將美學的思考對象從郭象的個體可見的世界轉向了整體的心靈境界。這種泯主客的般若思維模式將中國美學由郭象玄學之實進一步虛化,實現了滌蕩的心靈與躍動的生命的雙向運動,開辟了中國美學對“境”追求,成就了爾后中國藝術領域中“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象外之象”“韻外之致”的審美追求。
關于這個命題,禪宗公案中還有很多類似的感性表述。有僧曾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禪師們回答說:“蒲花柳絮”“長空不礙白云飛”“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春來草自青”……這些禪機語錄本身就是詩意的語言,雖然其中指涉的事物眾多,但意思卻殊途同歸。即佛即性,即佛即心,這些活潑潑的自然生命本身就具有佛性。佛法的獲得不需要通過主體的理性推究,世界的意義就在于自己本身。在萬象紛呈的宇宙世界中,寓目的當下之物的自由興現即為佛法,除此之外再無任何超越的本體。“‘禪’承接了道家要重現的自由無礙、物我物物互參互補互認互顯的圓融生命世界,本質上,與一般佛教不同,在公案里,道、佛二字,往往可以互換,答案都回到活潑潑的生命世界里。”[6]禪宗重視外在的視覺感受,內在的詩意與意象,與郭象玄學獨標的“捐跡反冥”一脈相承。禪宗的“拈花微笑”超拔于儒家的“詠而歸”、道家的“與物為春”、郭象玄學的“悠然見南山”,蘊含著一股涌動著生命氣息的精神境界之美。“真即實,實即真”的提出給尋找世界意義的藝術家們提供了精神的滋養與皈依,它超越了東晉孫綽的“山水即天理”、宗炳“山水以形媚道”,以“真”的藝術執著為中國美學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認知路徑,從此“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境界如星星之火般燎原于中國的藝術天地。
三、瞬間永恒的心靈秘密
中國佛教史中僧肇首次提出“妙悟”這個概念,他說“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涅無名論》。“妙”出自《老子》開篇“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妙者,幽冥之道也。”“[7]悟”是禪宗美學的靈魂所在,展示了參禪修行時恍然洞見真諦的情狀。禪宗以“萬古長空,一朝風月”為妙悟的最高境界。萬古的長空與當下的風月渾然交織的境界成就了妙悟的大美,這種大美將短暫渺小的穿越至無限至上的時空,旨在表明妙悟獲得的途徑為當下的存在。妙悟是推宗的根本認知方式,它是一種超越個體功利、知識、經驗、語言的非邏輯性的審美認識活動。從時間義上說,“妙悟”指向一次偶然不期而遇的瞬間永恒。這是禪宗一元本體論思維建構下的認識論,主張以人的直覺體悟,強調當下即為全部。從這個角度而言,“妙悟”作為具有東方智慧的認知方式,與郭象的“獨化”玄學為同一思想文化脈絡下生發出的類似產物。
郭象用“獨化”圓融了自己的本體論學說,置“有”于自生之境,完成了自身的否定之否定。他使用了大量帶“自”的詞語來描述獨化的運動過程,如“自生”“自然”“自性”“自爾”等意在表明事物的變化不假外求,是一個純粹內部運動的結果。這些表述徹底顛覆了漢儒的“天地之理”“天次之序”,他說萬物“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肖馳先生說:“郭象否定了任何超越義的本體,更解構了漢儒宇宙圖式時間系統的連貫和規則。”[8]郭象的“游于變化之涂,放于日新之流”“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無心玄應、唯感是從”等表述皆指向事物變化的瞬間性。
在談及“獨化”的條件時,郭氏說“卓爾獨化,至于玄冥之境。”(《莊子·大宗師注》)。“玄冥”是一種深幽奧妙、不可言傳的境界。“玄冥”看似神秘而無跡可尋,郭氏卻明確提出“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莊子·大宗師注》)“玄冥”是對“無”的一種稱謂,“這種‘無’與其說是‘無’還不如說是‘有’;與其說是存在論意義上的‘無’還不如說是認識論意義上的‘無’。”[9]“玄冥”是“有”的運動變化的狀態過程,它存在于事物自身,是打破物物相際的動態之“有”,作為獨化的條件,“冥然”是打破二者界限的途徑。郭氏在描述事物在“冥然”的過程中,使用了大量帶有時間意味的副詞,“忽然”“掘然”“塊然”等表明事物的自生是時間上沒有規律的偶然發生。“玄冥”的神秘狀態意為不能被人所完全把握。“冥”在瞬間消融了自我與審美對象的界限,是當下的即是時間上的每一刻都保持著獨立的自主。“玄冥”雖然深不可測,但通過片刻的時間固化,可通過“無心”來把握剎那的永恒境界。“心”在一念的超越與客體之“物”于獨化中相融,在物我合一的境界中,逃遁了時間意義的本體就被主體真正把握了。我們至此揭開“獨化”哲學的現象學美學意蘊:宇宙的本質在于本然無主的當下如如,他們呈現出無時不移的變化,此變化是無規律可循的偶然發生,主體憑借著不期而然的當下的自然生命的原發精神,剎那間與之冥于大化。自然生命原發精神的空前高揚,完全跳出了漢儒天人圖式的藩籬,深刻地影響了當時中國的藝術創作。以陶淵明為代表的歸隱詩人、山水詩的興起、繪畫藝術中的“以形寫神”、劉勰的“文以物遷,辭以情發”以及對神思的關注都是這一美學思潮下生發的類似的文化現象。
從時間義來看,郭象的“冥于大化”標識著一次性的偶然中遭逢外物的直感,這與中國詩學推崇的“即目”“現量”一脈相承。禪宗美學的“瞬間永恒”是在郭象自主的每一刻中對永恒的追問,它截斷了時間之流,在片刻中探尋永恒的意義、拷問存在的價值,成為了中國藝術中最深刻的秘密。在深受禪宗影響的中國藝術理論看來,妙悟就是掙脫時間的具象,將美上升至空靈的永恒義之中。禪門李長者云“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闡釋了妙悟的時間義:當下即為全部,剎那即為永恒。禪宗美學的根本意義在于對現實的超越,這是逃遁了時間意義之后的永恒安頓。剎那不是郭象玄學中短暫的、具體的時間意義,它是一種截斷,指向超越性的永恒。這種時間義成為了中國美學中極富價值的思想,它升華為一種境界:任萬物自由興現,與主體之心完全相融,成就了禪宗美學中最重要的范疇:妙悟。中國詩歌創作在取景造境的過程中充分展示了這一時間義思維,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句。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人生代代無窮己,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等等。這些詩人肆意古今時空,將人生的領悟遁入了永恒,實現了心靈的超越。
郭象的“獨化”說為我們提供了觀物的依托,禪宗“妙悟”說則實現了由觀物到照物的審美跨越。“照”是破執語言文字的主體之心在與客體之物相泯時,在般若照的剎那間“自成佛道”“識心見性”。《五燈會元》中有則關于“妙悟”的故事,“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法從本來,帶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看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五元會燈》(卷六)這個故事生動地描述了禪宗美學提倡“頓悟心源”的參禪體驗方式,它將靜穆的觀照與躍動的生命歸之于靈動的內心,這恰是心靈擺脫知識經驗的滯塞和障礙之后的“平常心”。“妙悟”作為推宗的審美認知方式,其認知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靈性的思維游戲。這場悠然自得、天馬行空的心靈游戲給中國藝術家提供一個能夠伸展自我的想象空間,他們更注重這場游戲的過程,而非悟得的結果。僧人所偈的“百花”“黃鶯”實際上是非見,呈現了一派的“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于此,中國美學的發展已經完全架空了郭象“無心玄應,唯感是從”,將“心”推之于本體之位。禪宗“心即物”是與老莊思想完全背離的新型哲學,可以說是對郭象無無論的極致發揮。郭氏的“自有”意味著事物的本身就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無心”作為把握“有”的方式,還與物象、經驗世界相關,而禪宗的“妙悟”突破了個體存在之有的局限,轉向了不確定的空靈境界,已經與心靈世界相融。它以心靈當下的直接體悟切入佛性,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帶動了中國美學在唐后期的審美主體突顯的走向,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美學與藝術發展的方向。中國詩歌領域“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王昌齡《詩格》)、唐以后中國繪畫領域的“重神輕形”之風、“境生于象外”等與禪宗美學的藝術追求殊途同歸。
我們說禪宗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以往哲學,進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美學與藝術的發展方向,那么郭象玄學無疑為這場革命之先導。它一方面與禪宗本體論建構的邏輯方法最為相似,另一方面,它將“虛無”落實于具體之“感”,被禪宗之“空”發揮到了極致。禪宗美學強調返回內心,由對知識的滌蕩,進而冥于萬物,融于天地,指向絕對的永恒,獲得靈魂的適應,完成了郭象應世哲學的心靈走向。
[1]張節末.禪宗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2.
[2]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7.
[3]皮朝剛.關于禪宗美學本體論的再思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
[4]潘知常.禪宗的美學智慧——中國美學傳統與西方現象學美學[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0(3).
[5]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6.
[6]葉維廉.中國詩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128.
[7]蔣錫昌.老子校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11.
[8]肖馳.郭象玄學與山水詩之發生[J].漢學研究,2009(3).
[9]康中乾.有無之辨——魏晉玄學本體思想再解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79.
【責任編輯 曹 萌】
B516
A
1674-5450(2014)04-0106-04
2014-03-03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3CZW008)
李小茜,女,天津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