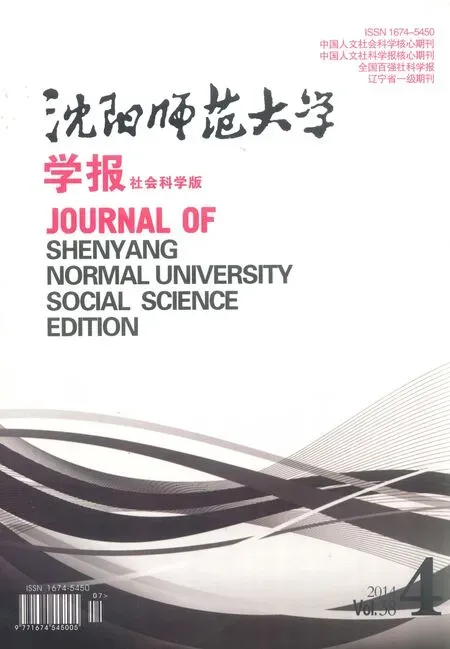羅什僧團譯經及其背后的政治推手
潘佳寧,丁 寧
(沈陽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沈陽 110034)
羅什僧團譯經及其背后的政治推手
潘佳寧,丁 寧
(沈陽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沈陽 110034)
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被梁啟超推崇為“兩大譯師”的鳩摩羅什和玄奘法師,雖時隔三百年之遙,卻殊途同歸,影響獨步一時。他們的譯著為后世研習,譯風被后人效仿。歸納其成功原因,二人同時具備三點:一、自身精通佛法,兼諳梵漢;二、依遵王命,奉旨譯經;三、云集眾賢,通力合作。但后人談羅什譯經,往往強調羅什自身才華,卻忽略其成功背后的客觀因素。這里包括后秦統治者姚興的鼎力支持和眾高僧通力合作。
佛經翻譯;羅什僧團;操控論;贊助人
我國的佛經翻譯源起于東漢,興于東晉,盛于隋唐。此一千二三百年間,佛經翻譯經久不衰。時間之久,影響之廣,碩果之豐,在世界翻譯史上可謂空前。在此期間,諸多翻譯大師橫空出世,各領風騷。但梁啟超在其《佛學研究十八篇》中不惜筆墨,著重提到鳩摩羅什和玄奘二人。他說:“譯經大師,前有鳩摩羅什,后有玄奘。玄奘法師卷帙,雖富于羅什,而什公范圍,則廣于奘。”[1]
梁先生將鳩摩羅什與玄奘法師比肩,且稱贊羅什“什公范圍,則廣于奘”[1],可見鳩摩羅什在佛經翻譯史的地位和影響。此外,《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一文還寫道
姚興時,鳩摩羅什入關,大承禮待,在逍遙園設立譯場,集三千僧諮稟什旨,大乘經典于是略備。故言譯事者,必推苻姚二秦[1]。
據此,我們得知鳩摩羅什譯經成功有兩個外因,即統治者的鼎力支持和三千僧眾的通力合作。若以此論,筆者認為如果將成就歸于羅什一人,而忽略其成功背后的客觀條件,對于贊助人姚興以及參與譯經的其他僧眾來說,有失公允。為了更全面、客觀地揭示贊助人對翻譯活動的影響,本文將重新描述以鳩摩羅什為首的譯經僧團(下文簡稱羅什僧團),并從操控論所及贊助人的視角出發,探究贊助人姚興對羅什僧團譯經活動的影響。
一、非一己之力,乃眾人之功
據《高僧傳》和《出三藏記集》,羅什之功有二:一、羅什本人深諳法相,盡誦佛旨,短短十一載,共譯佛典三十五部,近三百卷①呂先生在《呂佛學論著選集卷五》中第五講“關河所傳大乘龍樹學”中提出“三十九部,三一三卷”的不同見解。,且后人仍然為所出經文“十不出一”[2]感到遺憾。二、羅什對梵漢兩種語言駕熟就輕,譯風曲從方言,一改前人“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2]的譯法,首創“新譯”,后人將鳩摩羅什與真諦、玄奘、不空并稱中國佛教史的“四大譯師”。羅什法師對佛經的貢獻可想而知。但筆者認為,羅什固然偉大,但不應因皓月當空,而視群星無輝。下文將從譯經團隊的人數和人員質量,以及眾僧如何參與譯經這兩個層面進行論述。
(一)人才輩出、眾僧咸集
五胡亂華后,之前的佛教中心洛陽政局紛亂,僧眾四處奔走。隨著前秦在長安建立政權,加上統治者苻堅崇尚佛法,長安佛教開始逐漸興盛,四方僧人聚集長安,弘法傳經。據《宋高僧傳》和《中國佛典翻譯史稿》,早在竺法護、帛遠時,就已形成長安僧團的雛形,道安時期逐步發展,鳩摩羅什時期日臻完善,至唐代玄奘法師時達到頂峰。
關于羅什僧團數量的記載,《高僧傳》和《出三藏記集》中的記載有所出入:
——《出三藏記集》中《大品經序第二》
——《高僧傳》晉長安鳩摩羅什
上述兩段記載,關于僧團中參與譯經的僧眾數量分別為“五百余人”和“八百余人”。當下學者大多傾向于《高僧傳》中“八百余人”一說。因資料有限,具體數量無法得知,但兩段文字,都足以說明當時有眾多僧人與鳩摩羅什一同譯經。
此外,龔斌先生在其2013年出版的新作《鳩摩羅什傳》中記載這樣一段話:
四方沙門慕義向化來長安,乃秦國之光榮。國師羅氏,乃秦國之大寶。豈能阻遏求道者之腳步?命四方關尉,凡欲止長安之義學沙門,勿予阻隔,任其出入[4]。
這段文字記述的是統治者姚興對各地僧眾因慕羅什之名而趕赴長安這一現象的態度。最高統治者的首肯和支持,加上羅什在佛壇獨步一時,結果必然是眾賢云集長安,群星捧月。在眾僧之中,不乏許多高僧。如“冒涉艱危,遠奔神國”[2]的龜茲高僧頭達多,“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2]、于早年傳授羅什小乘佛法的佛陀耶舍,曾經點撥羅什戒律學的卑摩羅叉,再有在長安與羅什同譯《十誦律》的佛若多羅、繼佛若多羅之后、完成《十誦律》剩余翻譯工作的曇摩流支,還有佛學造詣可與羅什齊名、后于道場寺譯《華嚴》等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的佛馱跋陀羅,以及羅什身后、繼承先師衣缽、為世人敬為“十哲”“八圣”“關中四杰”的弟子道融、僧肇、曇影、道恒、慧嚴、慧觀、道生等諸多名僧。
(二)諸賢襄譯、共成碩果
從公元401年鳩摩羅什進入長安,到公元412年羅什去世,短短十一年內,佛經翻譯成績斐然。不但譯經總數多達“三十五部,近三百卷”,而且譯文“質而不野,簡而必旨”[5]。據《高僧傳》,其中不少譯經工作是由羅什與其他僧人共同完成的。如前文提及的佛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三僧與羅什共譯《十誦律》,再如佛陀耶舍助羅什譯《十住經》,并于弘始十二年(公元四一○年)譯《四分律》四十四卷,出《長阿含》經。
除上述幾位與羅什共同翻譯佛經的高僧之外,還有許多僧眾參與了譯文的修改校對程序。如僧團中的僧睿、僧肇就負責為羅什的譯文加工潤色。據《高僧傳》記載:
昔竺法護出《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睿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2
因出《大品》之后,肇便著《波若無知論》,凡二千余言,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2]
上面兩段文字記述了僧睿、僧肇兩位僧人與鳩摩羅什探究譯文措辭時的情景。其中,“什喜曰:‘實然。’”與“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兩句,形象地描述了羅什對二位僧人的譯法和文采表示首肯和稱贊。此外,對于羅什譯文的不妥之處,僧睿也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
法師于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尤隔而未通[3]。
僧睿對于羅什的這段批評,記錄在《大智譯論序》中。他認為羅什雖然通曉漢語,但許多語言的隱含信息仍然不甚了解。對于像羅什這樣身份顯赫的大師,僧睿敢于直言不諱,一方面揭示了當時譯場中知無不言的良好風氣,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眾僧在譯經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法依國主,幸遇姚興
“法依國主”[8]一詞最早是由前秦釋道安提出的。道安親眼目睹了先師佛圖澄在統治者石勒、石虎的支持下,佛教大昌的盛世;也親身感受了失去王權支持后,僧人無依無靠、顛沛流離的凄涼。于是在新野分張徒眾時,提出“法依國主”的觀點。道安后來有幸遇到了苻堅,成為“譯界之大恩人[1]”;同樣,羅什僧團若沒有后秦統治者姚興的支持,也很難取得如此斐然的功績。
操控論的代表人物,美國著名學者AndreLefevere在其《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一書中曾指出:“操控翻譯活動的社會因素有三,分別是意識形態,詩學與贊助人。”[6]在該書中,勒菲弗爾進一步指出,贊助人系統中包含三種影響翻譯活動的要素,即意識形態要素、經濟要素和地位要素。其中,意識形態要素控制翻譯的主題,經濟要素決定譯者的收入,而地位要素決定譯者的社會地位[6]。
在封建制度的中國,王權高于神權,佛教若要發展,必須得到王權的支持。而姚興正是一位禮敬賢哲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他曾為奪羅什一人,舉眾攻打涼州;羅什入長安后,他又建造譯場,親自參與譯經,選拔賢能,創建僧官制度。這一系列興佛重賢的政治舉措,正是羅什僧團譯經成功背后不可或缺的客觀保障。作為贊助人,姚興對佛經翻譯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崇尚佛法,躬親譯事
贊助人系統三要素中,意識形態要素控制翻譯的主題,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可以決定翻譯的內容。首先,姚興本人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出于對佛教的信奉,對羅什等佛法精湛的高僧自然是禮敬有加。姚興對羅什的敬重賞識,從《高僧傳》中的一段文字可見一斑:
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2]。
從這段描述我們得知,姚興對羅什格外敬重,先封羅什為國師,而且作為一國之君,經常不知疲倦地與羅什談論佛經。除了羅什以外,僧團中其他高僧也受到至高禮遇。如弗若多羅,姚興“待以上賓禮”[2];還有佛陀耶舍,“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于逍遙園中,四事供養”[2];甚至曾經對羅什出言不遜的佛馱跋陀羅,姚興也因其離開長安而“聞去悵恨”[2]。
其次,姚興潛心研習佛經,特別鐘意小乘禪定之學,撰寫《通三世論》一部。每逢羅什開壇弘法,他都攜眾臣虔誠學法;每遇羅什譯經,他也親自參與其中。《出三藏記集》中是這樣描述的:
法師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辨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咨其通途,坦其宗致[3]。
作為統治者,他親自與羅什共同商討舊譯中的不足,探究更好的譯文。姚興對佛法的虔誠和譯經的支持,自然是上行下效。上自太子姚泓、王公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對佛教熱衷推崇。如大將軍常山公姚顯、左將軍安城侯姚嵩也多次邀請羅什在長安大寺里講經說法。后秦時期,全國信奉佛教達到了“事佛者十室有九”的程度,佛學在后秦如日中天,自然促成佛經翻譯的如火如荼。
(二)建造譯場,廣羅才俊
Lefevere在描述經濟要素如何影響翻譯活動時說:“贊助人通過支付作者和譯者費用,或者委任工作的方式,以確保其生活的經濟來源。”[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姚興在經濟上支持羅什僧團譯經,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姚興以國家之力興建規模宏大的譯場,為僧團譯經提供專門場地。我國早期的佛經翻譯,“多是私人授受,既無一定體制,隨時隨地,皆可譯出。”[15]而羅什僧團的譯場則是氣勢雄偉,環境幽雅的皇家園林逍遙園,園內建寺院澄玄堂,設僧房,派專人服侍。除逍遙園以外,姚興還陸續建造了長安大寺、草堂寺等諸多譯場。
其次,姚興不惜重金,招攬天下賢能。如前文提到的佛陀耶舍,姚興為了邀請他加入僧團,“遣使招迎,厚加贈遺”[2];耶舍來到長安之后,又“四事供養,衣缽臥具,滿三間屋”[2]。關于姚興對僧眾經濟資助,《高僧傳》還有這樣一段記載:
除此以外,姚興的經濟支持還體現在供養僧人的人數上。前秦道安僧團在其鼎盛時期,人數約千人;但后秦時代的羅什僧團人數,據《高僧傳》記載,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余僧[2]。而《晉書》也有“自遠而至”的五千沙門的記載[7]。無論是三千、五千,還是前文提到的直接參與譯經的八百僧人,都足顯當時的羅什僧團人數空前。可以想象,幾千人譯場的工作場景是何等壯觀,在世界翻譯史上也屬罕見。而且這樣規模的譯經活動前后持續了十幾年,若不是舉全國之力,恐怕根本無法維持其龐大的開銷。
(三)創辦官譯,各盡其才
姚興對羅什僧團譯經的支持,還表現在他以統治者授權的形式,創辦官方譯場,建立僧官制度;并選拔人才,管理僧團。姚興時期的譯場,較比前朝最根本的變化就是建立了僧官制度,將僧團內部的自我管理規范改為國家授權的僧官機構進行管理。梁啟超在《佛典之翻譯》一文中將其列為“譯事進化之第六端”[1]。
僧官制度的建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在此之前的僧團,如道安時期的五重寺,僧團內部的管理主要靠佛教戒律和領導者自身的修行與道德權威來規范,而羅什僧團人數多達五千之眾,難免魚目混雜,良莠不齊。僅靠佛教戒律和僧人自身修養約束管理,顯得有些鞭長莫及了[10]。此時的僧團急需一個專門的管理團隊,依據國家法令,對眾僧加以約束管理,以保證譯經工作的正常進行。在這種情形下,姚興以統治者的身份任命僧官,管理僧團。據《高僧傳》記載:
“自童壽入關,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曰“:大法東遷,于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輿吏力。”[2]
從上述文字得知,當時的僧官機構共設國內僧主、悅眾、僧錄三職,姚興授以官階,配專人專車供其差遣。僧官體系的建立對規范僧人行為,維持譯經秩序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在羅什僧團遇到內部、外部危機時,為僧團化險為夷。
據史料記載,羅什僧團曾經面臨兩次生死存亡的危機。一次是僧團內部的佛馱跋陀羅挑戰鳩摩羅什的學術權威,提出“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2]的質問,后來又因為與羅什討論“色空義”,再次威脅鳩摩羅什在僧團的學術權威地位。這次危機最終是由道恒等人,以僧官之權,“顯異惑眾”之名,將佛馱跋陀羅師徒驅出長安而平息。第二次是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的外道婆羅門挑戰眾僧,欲搶奪僧團在后秦的地位。這一次,羅什、道融為了保護僧團的利益,借助僧官的行政權力,在辯論前設法得到婆羅門所讀書目,幫助道融在辯論中獲勝,捍衛了僧團在后秦政權國教的地位,客觀上也保證了譯經活動的延續。
除了創辦僧官制度外,姚興還知人善任,人盡其才。因羅什深通梵語,兼嫻漢言,加之其佛學修為和聲望,姚興尊羅什為國師,兼任譯主一職,全權負責譯經、弘法等學術事宜。但由于羅什曾經兩次破戒①羅什曾先后二次破戒。第一次是在龜茲,呂光強迫羅什娶龜茲王之女;第二次是姚興為讓羅什后繼有人,賜羅什十名妓女。,在戒律修為方面引人非議,難以服眾②卑摩羅叉曾問過羅什授業弟子人數,什答云:“三千徒眾,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而。”見《高僧傳——晉長安鳩摩羅什》第54頁。,因此任命行為清謹、嚴守戒律的僧為僧主,負責規范眾僧行為;又因為發現道恒、道標二人有治國才能,下詔命其還俗輔政。雖然姚興在道恒、道標一事上,有利用佛教維護后秦封建統治之嫌,但在客觀上規范僧團管理,為譯經提供了強大的政治保障。
三、結語
釋道安早年提出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觀點,揭示了翻譯活動中贊助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后來的羅什僧團譯經指明了方向。羅什僧團時期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完備了譯場分工,規范了譯經流程,不但提高了譯經的數量和質量,也為后來的佛經翻譯培養了諸多翻譯人才。雖然統治者姚興主觀上希望通過佛教鞏固其封建統治,但他興建譯場,廣羅眾賢,出經弘法,創建官譯等一系列政治舉措,都在客觀上成就了羅什僧團的輝煌,為佛學在我國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同時,也極大程度地促進了南北朝時期佛經翻譯的發展。
[1]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釋慧皎.高僧傳[M].北京:中華書局,1992.
[4]龔斌.鳩摩羅什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Andre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 LiteraryFame[M].NewYork:Taylor&FrancisGroupPress,1992.
[7]房玄齡.晉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尚永琪.鳩摩羅什譯經時期的長安僧團[J].學習與探究,2010.
【責任編輯 楊抱樸】
H159
A
1674-5450(2014)04-0110-03
2014-03-15
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L13CYY022,L12BYY007)
潘佳寧,男,遼寧沈陽人,沈陽師范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