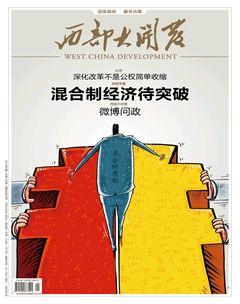中國智庫:面臨最好的發展機遇
2014年初,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在這一全球知名度最高、影響最廣的智庫報告中,中國智庫在數量上以426家位居全球智庫排名的“榜眼”。
過去的一年,也被媒體稱為中國智庫的“迸發年”。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首個中國智庫報告……智庫發展的熱潮撲面而來。那么,我國智庫是不是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
發展中的階段性特征
智庫,也稱為思想庫、智囊團,有人將其形容為一個國家的智商。服務于公共政策是智庫的“天然基因”,它能有效彌合知識和政策之間的鴻溝。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非常重視智庫的發展。
我國智庫發展處于什么樣的水平?《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指出,2013年,全球智庫總數為6826家,美國智庫以1828家位列第一,中國智庫以426家位列第二。中國社會科學院位列非美國的全球頂級智庫第九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均進入前100名。不過,“從全球頂級智庫排名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仍相對滯后”,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指出。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發布的《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將我國智庫分為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四大類。從我國活躍智庫(活躍智庫是指當前正常運行,并且對公共政策形成和社會公眾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智庫)的類別特征看,有2/5是黨政軍智庫,其中“國字號”智庫又占黨政軍智庫的30%左右。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主任王榮華指出,“我國受財政資助的智庫機構特別多,這是我國智庫有別于歐美國家智庫的一個顯著特點。”地區智庫發展不均衡是我國智庫的另外一個特點。我國活躍智庫約60%分布在東部發達地區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中部、西部地區的活躍智庫分布僅為17.0%和17.5%。
由于歷史沿革和體制原因,民間智庫一直是我國智庫發展中的“短板”。民間智庫盡管近年來有所發展,但在經費保障、項目來源、成果上升通道、建言獻策平臺上先天不足,患上了“侏儒癥”。“用魚龍混雜來形容當下的我國民間智庫,并不為過。”國觀智庫創始人任力波指出,“現在的民間智庫,有很多以前是咨詢公司、調查公司、信息公司,他們現在都在開展智庫發展計劃,其中既有實質業務上的轉型,但也有很多是提法上的噱頭。”
影響力是智庫發展的關鍵所在。王榮華指出,“我國智庫中,關注國家發展層面問題的智庫影響力會更大一些,關注區域層面問題的地方智庫的影響力則相對較小。”此外,我國智庫主要聚焦于經濟政策、政治建設與國際問題研究,專業化分工相對不足。這也是我國智庫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成長中的煩惱
不可否認,我國智庫已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有力推動了我國公共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進程。可若認真給我國智庫發展把把脈,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一是“近”與“遠”問題。當今中國,活躍度高、影響力強的智庫以官方或半官方為主。這些智庫與決策機構距離“近”,成果能快速被應用到公共政策中。但走得太近,就存在缺乏公信力、難以形成“獨到見解和意見”的危險,與公眾距離容易“遠”。錢由上級給,承擔人是圈定的,再加上項目結項也常由政府部門來組織,“這樣的智庫充其量只是個‘幕僚的角色,很難保證其獨立性、客觀性、社會性和創新性”,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社會科學教研部副教授胡銳軍指出。因此,如何保持“近”與“遠”的平衡,是我國智庫發展要嚴肅對待的問題。
二是“闡釋”與“創新”問題。智庫要走在決策的前面。但是,“在現有體制下,決策咨詢往往會出現‘專家秀等情況,即專家為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背書,從而出現專家決策咨詢的‘空洞化和‘符號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強認為,國內智庫有許多還屬于闡釋性智庫而非創新性智庫。官方智庫大多集中在政策的解讀而缺少研究關口前移的意識,高校智庫的專家學者在政策咨詢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上有所欠缺。這些都影響了“智”與“政”的結合水平。
三是“譜系長”與“頻道多”問題。縱向上,從中央到地方,不同層次的智庫形成長長的鏈條。所以,“譜系長”是我國智庫的特色之一。橫向上,黨政軍智庫可區分為發展研究中心、黨校、行政學院、各部委研究機構以及軍方智庫等不同類別,再加上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以及民間智庫等,使我國智庫呈現出門類龐雜、形態各異、“頻道多”的特點。“長”與“多”使我國智庫發展既分散又重疊,條塊分割,各個條塊封閉運行,相互間交流乏力,進而產生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
培育我國智庫的“中國特色”
我國智庫正面臨最好發展機遇,但要真正迎來發展的春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我國智庫發展的目標。那么,“中國特色”特在哪里?“新型”又新在何處?
“中國特色就是要充分反映智庫發展的‘中國國情‘中國背景‘中國元素;‘新型則主要是針對‘傳統而言。”王榮華指出,這個“新型”體現為研究必須以理論創新為基礎、以科學決策為目的,是公共政策變遷與專家參與互動的結果。胡銳軍指出,符合中國國情、反映中國實踐的中國智庫建設還應該堅持服務理念,“一流的智庫不僅僅只是服務領導,還要引領社會思潮,而最終目的是服務人民。”
毫無疑問,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王戰認為,“關鍵是要形成政府引導并影響智庫、智庫客觀獨立服務政府的新型關系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培育出獨立的思想與智庫的‘庫格。”
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民間智庫該如何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任力波認為,民間智庫要有自身的“格局”定位,科學看待與官方智庫的差異,“民間智庫有咨詢、調查、信息等類別,差異化發展反而是出路。”
人才是智庫的核心,沒有人才的智庫終將是個空架子。美國頂尖智庫人才的“旋轉門”機制已經被證明是其能夠產出高質量成果的關鍵所在。胡銳軍認為,我國智庫“也應該逐步建立類似的人才流動機制,建立起智庫人才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中國式‘旋轉門”。
(作者為人民日報記者)
觀察者說
智庫重要的是進行功能整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李 揚
現代智庫是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詢的機構,其基本功能是提供專業化的知識、信息等,幫助政策制定者和公眾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決策。在很多國家,智庫已成為政府決策鏈條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成為影響社會輿論最重要的社會治理機構之一。可以說,智庫已成為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獨立性、科學性和建設性,是頂級智庫必備的三大要素。獨立性,是指智庫通常都與當局保持一定距離。惟其獨立,智庫才能客觀、冷靜、不受干擾地進行研究和判斷。智庫的獨立性與資金來源的多樣化和民間化有關。以美國為例,其智庫也需要尋求外部資金支持,但這些資金必須是“非限定性”的,即不附帶任何條件,對智庫的立場、觀點和研究方向等基本不施加影響。科學性,是指智庫的研究以深厚的學術為基礎,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為依憑,掌握詳實可靠的數據和資料,用簡潔易懂的方式說話。惟有如此,智庫才能獲得公信力。顯然,為使智庫成果具有科學性,延攬一流人才從事研究當屬題中應有之義。建設性,是指智庫的研究不能止于發現問題,也不能以批判現實為能事,而應致力于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智庫將深厚的學術積淀與縝密的政策設計密切聯系起來。要做到這一點,顯然需要智庫的研究人員不僅是精通學術的行家里手,還應是深諳世情、國情的優秀實踐者。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智庫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對照國際先進標準,我國智庫的整體發展水平顯然還比較低。在未來發展中,我們不僅需要在思想上將智庫建設提升到發展國家軟實力的高度,更要努力拓展智庫的獨立生存空間,尋求經費支持的多元化,培育智庫發展的良好土壤。同時,建立有效的聘任和激勵機制、建立適當的智庫治理機制等也相當重要。
我們不妨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例,進一步分析我國智庫建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智庫功能未能充分發揮,除了體制機制存在諸多限制,學術研究和智庫這兩大功能的隨意混搭、相互攪擾也是重要原因。眾所周知,學術研究與智庫之間本質上存在著重大的功能區別。其一,學術的目的是發展學理、觀點和理念;而智庫的要義是運用現存的學理、觀點和理念闡釋現實問題,提出政策建議,解決實際問題。其二,學術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相當程度上被學者個人之志趣左右;而智庫則有明確的目的和效率指向,它要求匯聚各方專家、平衡多方觀點而形成共識,體現的是機構組織的共同看法。其三,學術追求的境界是“十年磨一劍”,講求厚積薄發;而智庫則要求及時、迅速做出反應,最忌延誤時機。其四,學術成果優劣的判別依據在于知識的積累與傳承;而智庫成果的判定標準則在于是否能在國家政策中得到體現,是否在社會公眾中產生影響等。其五,學術發展的過程高度依賴于“養士”機制和培養接班人機制;而智庫的運行則重在高薪“用士”等。學術研究與智庫的功能、運作模式如此不同,顯然必須有適當的體制安排來妥善處理兩類功能的關系。
從多數國家(地區)的實踐看,處理學術研究機構和智庫之間的關系,在體制上大致有兩類安排。一類是機構分設,即學術功能和智庫功能分別由不同的專業機構承擔,絕不混搭。即,若定位于學術研究,則其成員必須專注于皓首窮經,其成果評判標準便是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在學科發展上發揮引領作用等。若定位于智庫,則專注于戰略設計和政策咨詢,關注政策影響力和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另一類是學術研究與智庫功能共居一體,但這些功能分別由專門的下屬機構分擔,“功能專設、分別治理、適當交流、相互支撐”是其基本特色。如美國斯坦福大學擁有99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庫胡佛研究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擁有20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等。與純粹且單一的學術研究機構和單一智庫相比,這些機構便有了其他機構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設,考核機制得以專一,不致產生顧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其人員可以流動,能形成學術研究、政策設計與教學彼此促進、相互支撐的共贏局面。
我們以為,借鑒世界著名大學的方式,將學術研究和智庫在院、校的統一治理下實施“功能專設、分別治理、適當交流、相互支撐”,比較容易對目前我國的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準智庫”們進行整合,并能較快產生明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