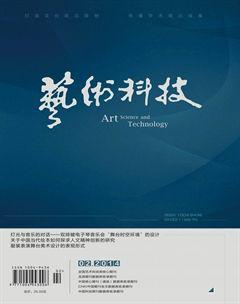從人文主義到科學主義:形式主義藝術史研究的興起
馮白帆
摘 要: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藝術史學科為最明顯的變化是其研究方法從人文主義轉向科學主義和形式主義。這一轉變最初表現在18世紀歐洲文化藝術研究地理中心的遷移。在這個時期,德裔學者科學化的藝術史研究方法逐漸取代了之前意大利學者人文主義的藝術史研究方法。通過溫克爾曼、瓦爾堡、沃爾夫林和潘諾夫斯基等人的努力,藝術史學科在現代大學中獲得了獨立。而帶有科學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的藝術史研究方法逐漸占據了19世紀至20世紀這段時期藝術史研究的主流。這些德裔學者為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關鍵詞:人文主義;科學主義;形式主義;藝術史;潘諾夫斯基
在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藝術史研究在18世紀和19世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藝術史寫作觀念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說,首先表現在藝術史研究地理中心的轉移。籠統地說,在18世紀之前,意大利作為古典文化和藝術的中心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和藝術家理想中的圣地,深厚的古典人文基礎和無以計數的藝術珍寶讓意大利變成了藝術領域名副其實的思想中心,同樣,意大利在歷史上也一度是藝術研究的中心。這一點具體的體現在各國紛紛在羅馬和意大利設立各自的美術學院的事實上。
早在1633年,路易十四(Louis XIV)統治時期的法蘭西皇家美術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便專門在羅馬設立了法國皇家學院。不僅如此,法國宮廷還設立了“羅馬獎學金”(Prix de Rome),用以獎掖優秀的年輕藝術家到羅馬進行深造。[1]如果藝術家獲得了“羅馬獎學金”并去意大利待上幾年,那么他的作品會身價倍增。其原因在于,獲得羅馬獎學金不僅意味著皇家的首肯與認可,同時在羅馬的藝術訓練也往往暗示了更為優良的藝術品質。這和早期美術學院中一直秉承的人文主義觀念有著莫大的關聯。①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對于早期的藝術史家而言,意大利也是不能錯過的深造場所。
但是從18世紀開始,意大利作為藝術史學術中心的地位開始遭到了來自德語國家學者們的挑戰:“盡管藝術史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甚至遠至古代文化,但是,它仍然是學術大家庭中新加入的一個成員。可以說藝術史就是對那些除了功利價值之外,我們還為其賦予了其他價值的人工制品進行的歷史性分析和解除它一方面與美學、評論學、鑒賞和‘欣賞不同,另一方面又與純古董研究有別。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指出的,很偶然地,‘藝術史的母語是德語。藝術史首先是在德語國家被當作一門正規學科的,它是在德語國家受到精心培育的,它是在德語國家對有關學科發揮了日益顯著影響的,這些學科中甚至包括了它更古老、更保守的姊妹學科——古典考古學。第一部在書名頁上堂而皇之印有‘藝術史的著作就是溫克爾曼1764年的《古代藝術史》……”[2]潘諾夫斯基的觀點可能代表了現代大部分藝術史學家的觀點。而且從藝術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事實確實也是這樣的。
在瓦薩里之后,真正影響了藝術史研究方法發展的確實是德裔藝術史學家。就像人們所熟知的,潘諾夫斯基曾在《美國藝術史研究30年》(Three Decades of Art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Impressions of a Transplanted European)對這一過程進行了充滿自豪的論證。同樣知名的還有從德國遷往倫敦的瓦爾堡學院(The Warburg Institute)(此處有待進一步補充)。
不僅如此,這些經過了二戰洗禮的德裔藝術史學家紛紛逃往英美,這使得藝術史研究的中心徹底地從原來的意大利轉移到了英國和美國。潘諾夫斯基自己就是在二戰期間流亡美國之后寫下這段話的。不管這種影響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后果,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藝術史研究的專業化和科學化進程主要是由德裔的藝術史學家完成的。然而,潘諾夫斯基的這段話所表達的觀點卻有著更為久遠的歷史,它幾乎可以被視為另一位德裔藝術史學家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Johan Winckelmann,17171768)藝術史觀念的現代演繹。
溫克爾曼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弗拉維奧·比翁多(Flavio Biondo,13921463)的信徒,比翁多通常被現代學者視為一位古物收藏者和鑒賞家。從溫克爾曼《古代藝術史》的前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他繼承了某些人文主義者的觀念,比如瓦薩里生物學周期似的藝術發展觀念(將希臘藝術分為古風、古典、希臘化三個時期)。另一方面他還確立了美術史上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風格”(Style)在藝術史中的地位。“風格指的是文學作品中語言的運用,以及所有藝術的某一時期、流派或門類共同的形式特征的總和。”[3]在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那里,它指的是作家們書寫的方式或雄辯家們發表演說的方法。在羅馬時期風格這個詞匯的前身(Stilus)和手法(Manner)是可以互換的,在文藝復興時期,Style更多指代的是某種語言或修辭風格。正是在溫克爾曼之后,“風格”(Style)的含義才在藝術史領域固定下來,用以指稱藝術家或藝術作品中體現出的某種代表性的形式組織模式。不僅如此溫克爾曼所提出的以風格和形式對藝術史進行重新編撰的研究方法,以及以藝術品本身為核心的研究方式都極大地影響了之后藝術史的發展脈絡。在《古代藝術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Antiquity)的前言中,他對自己的意圖進行了闡述:“我撰寫的這部《古代美術史》,不僅僅是一部記載了若干時期其間發生變化的編年史。我是在希臘語的更為廣闊的含義上來使用‘歷史這一術語的,其意圖是要呈現出一種體系……主要目標是論述藝術的本質,而這一內容是那些藝術家傳記所極少論及的……美術史的目標是要將藝術的起源、進步、轉變和衰落,以及各個民族、時期和藝術家的不同風格展示出來,并要盡可能地通過現存的古代文物來證明整個美術史。”[4]
他認為,之前的藝術史學家“很少談到藝術”或藝術作品本身,“因為作者對藝術不夠熟悉,除了從書本與傳聞得來的東西之外,就談不出什么東西了……即便談到藝術,要么只是說些泛泛的贊揚的話,要么將其觀點建立在怪異與錯誤的基礎上。”[4]由此,藝術史的研究方法開始從之前那種綜合了鑒賞、批評和傳記的文化史研究方式轉向了藝術作品的形式或風格本身,并按照某種獨立、科學、嚴謹的態度開始對藝術進行風格或類型化的分析。就這一點來說,潘諾夫斯基是正確的。他在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謙虛卻不乏自豪地指出了同時代英國和美國藝術史研究的落后狀況。并列舉了在此之后具有德國藝術史研究血統的學者對這個學科本身做出的卓越貢獻。[2]
正如我們所熟知的,阿道夫·希爾德布蘭德(Adolf Hildebrand,18471921)、李格爾(Alois Riegl,18581905)、海因里希·沃爾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等卓越的德裔藝術史學家逐步完善了的這種以作品內在因素(題材、風格、形式等)為重心的、科學化的研究方式。沃爾夫林等風格史學派的藝術史學家這種注重純粹的形式分析的研究方法沖擊了之前那種傳統的、綜合性的藝術史研究方法。他們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風格分析為基礎的、獨立的藝術史語言。這種藝術史研究方法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形成了巨大的一股勢力。在法國是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18811943),英國則是羅杰·弗萊和克萊夫·貝爾。盡管他們在形式風格領域的研究讓人欽佩不已,而且他們為現代藝術史學科的建立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卻越來越多的遭到了質疑。
就像溫尼·海德·米奈(Vernon Hyde Minor)在《藝術史的歷史》中總結以沃爾夫林為代表的藝術風格史研究的特點時所指出的那樣:(沃爾夫林)“以我們可見的事物開始,隨后用可見的、客觀的、在經驗上可以被證明的資料創立了一個體系(如,線描的與涂繪的)。我們無須依賴享有特權的、富裕的藝術品收藏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走進博物館,都可以聽配有幻燈放映的講座)的才智與經驗,也不必理解康德、黑格爾或其他19世紀德國美學家的那些復雜的唯心主義哲學,就可以寫出沃爾夫林的著作,無一例外。”在德裔藝術史學家的努力下,藝術史逐漸成了某種不需要與其他社會文化因素聯系在一起的、獨立自主的學科,“要么權當我們的文化背景和沃爾夫林所處的文化背景是十分相似的,要么權當文化背景(Zeitgeist),以及歷史意識與我們的觀看方式無關。”她認為,這些藝術史學家實際上給了我們一種“無價值取向、無文化偏見、客觀的、多少科學的、非政治性的對藝術品德接收方式。”②而且,藝術史編撰的主體也從“畫家、人文主義者和鑒賞家”變成了學院中的教授或專職研究人員。
也許德國人血統中嚴謹的思維習慣和某種懷疑論的傳統使得20世紀的許多學者逐漸不滿足于這種局限于藝術作品“內部”的研究方法,開始從多個路徑對藝術史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索。在20世紀初期,各種不同的藝術史研究方法開始涌現。比較突出的是20世紀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和圖像學研究方法。藝術史研究中的心理學方法是由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創立的。弗洛伊德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版了一系列心理學研究的著作并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學理論體系。他在藝術史研究方法方面的貢獻主要指的是1910年發表的《列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段記憶》(Leonardo da Vinci,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他建立在自己心理學學說基礎之上的藝術史研究方法并沒有獲得藝術史學界的認可。大部分學者認為這種研究方法幾乎完全是推理性的,而且無法獲得實質性的證明。就像阿諾德·豪澤爾在《藝術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中指出的那樣,除了受到抑制的性欲望、俄狄浦斯情節、對閹割的畏懼或自戀傾向,心理學的闡述方式似乎就再也沒有別的什么東西了。[6]作為一種輔助性的研究方法,弗洛伊德的理論還是有一定的追隨者的,但其影響仍舊有限。③與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研究方法相比,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18661929)所開創的圖像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則要大的多。從某種意義上說,圖像學的研究方法是“對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和純美學研究的一種反動”。[7]1912年,瓦爾堡在《費拉拉的斯基法諾亞宮中的意大利藝術與國際星相學》中首次正式地闡述了圖像學的理論。“瓦爾堡從一開始便反對沃爾夫林所堅持的藝術史主要是風格史的觀點。瓦爾堡相信藝術史必須引進、依賴其他學科領域,因為藝術史就是文化史(Kulturge schichte)的一部分。”[7]這種開放性的研究方法隨即吸引了一批年輕的藝術史學者,愛德華·溫德、潘諾夫斯基、貢布里希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這種強調圖像的內涵與它所在語境之間關聯的研究方式在戰后的英國和美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且對風格史的研究方法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然而,正當它的影響力逐步擴大時,另外一種試圖將藝術史研究同各種社會因素結合起來的方法開始在藝術史領域出現。也就是我們后來稱之為“藝術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在藝術史領域,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藝術史研究方法,首先,它是由東歐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藝術史學家引入歐美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其次,這種研究方法的理論背景也并不植根于歐洲固有的藝術史研究傳統。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對于20世紀初期歐洲的藝術史學家來說,這種研究方法都更像是來自藝術史外部的入侵者。
注釋:①另外,就“羅馬獎學金”本身而言,它在歷史中的作用長期以來被人們低估了。從歷史上看,“羅馬獎學金”似乎并不是只法蘭西皇家美術學院的獨創。歐洲其他美術學院也先后建立了類似的獎勵機制。這些獎勵機制無一例外的將意大利作為學習和深造和核心,將古典的人為主義傳統作為教學實踐的核心思想。而且,作為某種溝通機制,羅馬獎學金似乎還擔負了歐洲各國美術學院之間的交流與聯系工作。比如,16941696年間成立的普魯士皇家美術學院(Preuische Akademie der Künste)就和法蘭西皇家美術學院有著頻繁的交流。在拿破侖執政期間,法蘭西皇家美術學院還一度支持過荷蘭王國(Kingdom of Holland)的“羅馬獎學金”。隨著歷史的發展,羅馬獎學金作為一種制度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19世紀達到了頂峰。美國甚至直到1894年還迫不及待地在羅馬地區海拔最高的賈尼科洛山(Janiculum Hill)上設立了“美國羅馬學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為獲得美國“羅馬大獎”(Rome Prize)的學者和藝術家提供生活和深造的場所。而且,法蘭西學院的羅馬獎學金直到1968年才徹底終止。在這里,我必須指出的是,在傳統的藝術史研究領域,人們提起羅馬獎學金往往指的僅是它與法國皇家美術學院這種單一的聯系。但實際上羅馬獎學金的背后可能存在著一幅更為宏大的社會圖景,如果我們將它視為某種機制,我們會明確地感覺到它的貢獻不止是在藝術領域。或者我們從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傳承的角度來看,羅馬獎學金似乎肩負了更為重要的歷史任務。正是由于范景中先生指出的那種“專業化的、孤立的”藝術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之前的學者似乎一直沒能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考察。或許也有許多學者早已意到了這個問題,對于他們而言,缺少的可能只是一種合適的研究方法。
②溫尼·海德·米奈(美),藝術史的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4.另外,范景中先生在《美術史的形狀》一書的序言中也表達出了類似的擔憂:“我深知,很多人不想把藝術視為天下公器,他們覺得那是懂藝術者的專有之物,他們抱著專家的優越態度,高視傲兀,目空一切,正如歌德所說,當他們局限于自己的專業領域時,便會表現出固執,而當超出他們的專業領域時,又會顯得無知。”見:《美術史的形狀》,第6頁。
③比如貢布里希就曾借助這樣的方法來輔助自己的圖像學研究,見:藝術與錯覺:圖畫再現的心理學研究[M].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參考文獻:
[1] 〖JP3〗邢莉.自覺與規范:16世紀至19世紀歐洲美術學院[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64.
[2] 歐文·潘諾夫斯基(美).視覺藝術的含義[M].傅志強,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375.Erwin Panofsky.Three Decades of Art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Impressions of a Transplanted European,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Garden City,N.Y.,1955:321323.
[3]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ed,wiene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4:330.
[4]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History of the Art of Antiquity(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1764),Adolf H.Borbein,Editorial Consultant,Michelle,Manuscript Editor,Getty Research Institute,Los Angeles,Acknowledgements,2006:71,72.
[5] 溫德·海德·米奈(美).藝術史的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4.
[6] Arnold Hauser,Philosophie der Kunstgeschichte(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M].1958,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Psychoanalysis,Sociology,and History,p.7177.
[7] 邵宏.美術史的觀念[M].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228229.
[8] 貢布里希(英).藝術與錯覺:圖畫再現的心理學研究[M].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