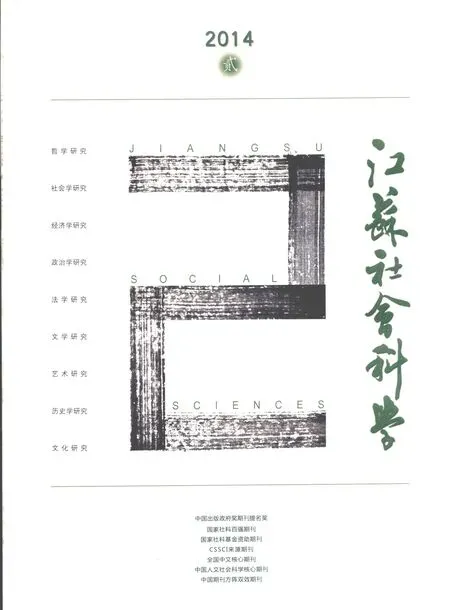論微博的圖文景觀及其內在張力
楊向榮
論微博的圖文景觀及其內在張力
楊向榮
相比傳統(tǒng)的紙媒時代,在網絡媒介時代,觀者的自覺意識前所未有地加強了,其閱讀心理與閱讀期待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微博作為現(xiàn)代新興的網絡媒體之一,其表現(xiàn)出來的圖文景觀無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圖像的興起以及對文字的優(yōu)勢,也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當下社會文化和審美心理的轉型,其表征出來的圖文景觀在一定程度體現(xiàn)了當前視覺文化語境中圖文關系的發(fā)展趨勢。以微博的圖文景觀為切入點,進而探討虛擬空間中圖文關系的生成和建構,將有助于我們在視覺文化語境中明確圖文關系的內在張力及其言說邏輯。
微博 讀圖時代 圖文景觀 張力
貝爾曾寫道:“目前居‘統(tǒng)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tǒng)率了觀眾。”[1]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154頁。而伯格也提出,我們如何理解所看之物的方式,既受到視覺對象和媒介方式的制約,同時也是一種自覺選擇和自覺加工生產的過程[2]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可以說,視覺文化的興起所引發(fā)的圖文景觀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相比傳統(tǒng)的紙媒時代,在網絡媒介時代,觀者的自覺意識前所未有地加強了,其閱讀心理與閱讀期待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而微博作為一種新興的網絡媒介,其表征出來的圖文景觀無疑有著很好的代表性。筆者以為,以微博的圖文景觀為切入點,進而探討虛擬空間中圖文關系的生成和建構,將有助于我們明確圖文關系的內在張力及其言說邏輯。
一、微博圖文景觀的表征
在眾多的網絡媒介中,微博以其便捷、交互、即時、跨媒體的優(yōu)勢迅速發(fā)展起來,成為近幾年交互式網絡媒介的代表之一。在這一新興的網絡媒介中,圖文互文表達是其突顯的一道景觀。雖然與傳統(tǒng)媒介相比,微博中的圖像與文字的功能并沒有發(fā)生很大變化,圖像還是直接作用于觀者的視覺,文字的排列方式也仍是傳統(tǒng)的線性方式,不過相對于傳統(tǒng)媒介而言,微博的圖文景觀表征,特別是圖文的表達方式還是有著很大的變化:圖像延伸了視覺的功能,在虛擬現(xiàn)實中,圖像甚至帶有觸覺等感官的全面體驗,直觀的具象思維也開始延伸到抽象思維層面。與圖像的轉變相呼應,微博中的文字形式也出現(xiàn)一系列變化,文字逐漸變得形象化和符號化,甚至有些文字與圖像并沒有多少區(qū)別,同樣可以給觀者直觀的感受。此外,在微博中,圖像的生存空間明顯占有優(yōu)勢,如新浪微博中,圖像信息占的比重達到90%。在騰訊微博中雖然比重不如新浪微博,但騰訊微博設有專門瀏覽圖片的瀏覽范式,圖片瀏覽范式窗口完全將圖片作為瀏覽內容,由此可見騰訊微博對于圖像的重視。據(jù)筆者梳理,微博圖文景觀的具體表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以圖釋文型。在這類圖文景觀中,先以少量文字敘述核心內容,再配以圖片,用以闡釋文字。在以圖釋文型圖文景觀中,還有一類比較特殊的圖像,即以圖像來代替文字的敘述,有些微博用戶為了敘述一個事件或者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他不是以文字來表達,而是以圖片來表達,運用圖片將事件串聯(lián)起來,從而提供更為直觀的表現(xiàn),給觀眾多感官享受。
互動交流型。互動交流型圖像主要是指微博上發(fā)布的圖文信息并非原創(chuàng)信息,而是通過轉發(fā)其他微博用戶的圖文信息來闡釋自我的觀點。互動交流圖文景觀并不在于展示圖像和文字本身,而在于圖文景觀背后意義的交流互動。
消費引導型。這一類型的圖文景觀通常出現(xiàn)在微博的軟廣告中。微博作為一個極具廣告潛力的媒體,大量具有說服性目的的圖像型廣告存在于其中,甚至某些文字的圖像化設計本身就是一種廣告,圖像承擔著消費的“包裝”作用。而且,在微博中還存在許多視覺消費說服型圖像,這些圖像用視覺表現(xiàn)包裹廣告的商業(yè)消費目的,致力于說服微博用戶進行網上消費。在一個眼球經濟時代或者說注意力經濟時代,消費的核心在于消費注意力,而微博作為一個有著廣大用戶群的信息交互平臺,自然在商家的關注之列。消費社會強調的不僅僅在于物品的實用價值,更尋求物品的審美體驗,而微博中的圖像就承擔著這樣的包裝作用,它將說服目的隱含在審美的外表下,使人們更容易接受。
繼續(xù)深入下去,筆者以為,微博的圖文景觀反映了現(xiàn)代人的生活狀況。在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中,隨著現(xiàn)代性的展開,出現(xiàn)的是個體的碎片化生存。所謂現(xiàn)代性的碎片化,就是指現(xiàn)代社會的諸多方面,包括個體、世界、知識、道德,認知,等等,都成為了碎片。在某種程度上,碎片表征著現(xiàn)代生活本身,對此,齊美爾曾認為,現(xiàn)代個體也是生活中的一個碎片。“我們總是在不同的層面間來回地循環(huán),它們依據(jù)不同的規(guī)則,全都構成了世界總體,但從每一個平面來考察,我們的生命在任何特定的時候所獲得的只是一個碎片。”[1]由于現(xiàn)代生活的碎片化,個體的感知也出現(xiàn)了印象主義風格,現(xiàn)代個體不再關注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內涵,也不希冀建立一種闡釋現(xiàn)實的宏大結構體系,而是注重以主觀的內在心理感悟社會生活的表面現(xiàn)象或現(xiàn)實碎片。
現(xiàn)代性的碎片化體現(xiàn)在微博圖文景觀上,主要表現(xiàn)為現(xiàn)代人對于文字的忽略和對于圖像的“淺閱讀”和“淺表達”,而這也正是微博圖文景觀的另一重要表征。在微博這樣一個網絡交互平臺上,個體所表達的往往只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經驗的一角,文字是思緒的一剎,圖片是景觀一瞬。圖文都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因而更注重表達審美體驗和注意力效果。微博的這個特點也正是當下日常生活審美化的一個很好的個案,這正如齊美爾所言,在現(xiàn)代性的感性主義生存中,“藝術本質上的意義在于它能夠從一個現(xiàn)實的偶在碎片(它依賴于同現(xiàn)實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出發(fā)構筑出一個獨立自主的統(tǒng)一體,一個無須其他的自足的微觀世界。個體存在與超個體存在之間典型的抵牾,可以被闡釋為這兩種因素要達到美學上令人滿意的表現(xiàn)形象而無法妥協(xié)的抗爭。”[1]齊美爾:《貨幣哲學》,陳戎女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現(xiàn)代生活中的每一個碎片都隱含著成為美的可能性,而生活的整體內蘊通過審美的方式從任何一個點上都能夠得到展現(xiàn)。在這個意義上,微博的圖文碎片化景觀也是個體自我實現(xiàn)和自我確證的策略。由于社會的碎片化,導致人們身份認同的碎片化,才使得互動交流變得如此急需,不管是名人還是草根,人人都渴望交流和展現(xiàn)。微博這種全民的公共空間就顯得很可貴。正是因為如此,微博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得不同人群的共鳴而逐漸為人們所青睞。
我們發(fā)現(xiàn),在微博的圖文景觀中,“重圖輕文”的傾向是比較明顯的。但如果我們把這一問題放到“讀圖時代的到來”的問題域中,微博的“重圖輕文”現(xiàn)象實際上可以視為視覺文化時代圖文戰(zhàn)爭的一個縮影[2]圖文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課題,詩畫關系、語圖關系、圖文(文字)關系都是其應有的問題域之一。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基于微博的探討,其主要切入點和對象是圖像與文字的關系。但由于文學是通過語言文字而得以建構,文學的基本是語言文字,因此,在具體的探討語境下,我們的研究對象也將轉為廣泛的文學與圖像的關系。。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中曾占據(jù)著社會的主導地位,但20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視覺文化開始取代傳統(tǒng)的印刷文化形態(tài),并使當代文化實現(xiàn)了從語言向圖像的轉變。海德格爾在20世紀30年代也曾宣布一個“世界圖像時代”的到來,人們開始以視覺化的方式來了解世界。艾爾雅維茨認為,“在后現(xiàn)代主義中,文學迅速游移至后臺,而中心舞臺則被視覺文化的靚麗光輝所普照。”[3]艾爾雅維茨:《圖像時代》,胡菊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可以說,當下人們的生活和文化開始依賴于視覺,大量的視覺符號占據(jù)了人們生活的空間,電子傳播媒介的高度發(fā)達形成以視覺圖像符號為主導的社會文化形態(tài),使得視覺圖像和形象代替語言文字符號成為文學傳播的主要符號,現(xiàn)代文化正在脫離以語言為中心的文化,逐漸轉向以圖像為中心的文化形態(tài)。
在當下的讀圖時代語境中,圖像日益凌越于文字之上,并對傳統(tǒng)文學閱讀構成了挑戰(zhàn)。電視、電影、廣告、包裝設計等視覺符號逐漸覆蓋我們的生活,沖擊我們的視覺感官,視覺文化在大眾消費文化中開始占據(jù)主流形態(tài)。現(xiàn)代性的生活方式使圖像取代文字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工具,這種快速、準確、便捷的文化消費方式適合現(xiàn)代人快節(jié)奏的生活方式。消費社會的到來使現(xiàn)代社會人們的生活呈現(xiàn)出快節(jié)奏、娛樂化、感官化的特點,而無深度的視覺圖像正好滿足了大眾趣味。視覺消費的虛擬性和體驗性給大眾帶來快感,圖像的刺激性滿足了受眾的好奇心,一張張充滿美感和視覺刺激的圖像成為人們宣泄煩惱、擺脫壓力的方式。而且,圖像視覺符號本身作為一種信息符號,具有直觀性、生動性,沒有了地域、民族、語言的限制,更易被受眾認知和把握。
在這個意義上,微博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不確定性、零散性、差異性等特征,可以說都與視覺文化時代所倡導的視覺理念不謀而合,同時也可以說是后現(xiàn)代文化的一種表征。在后現(xiàn)代文化場域中,微博體現(xiàn)出來的碎片式、戲仿式、身份的漂移以及對傳統(tǒng)話語權的解構等特征是十分明顯的。圖像在其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圖像本身就是一種碎片式敘述。相對于文字而言,現(xiàn)代人們更喜歡用圖像來敘述生活。后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的身份游離于各種符號之間,圖片能更好表征身份,表征即時的狀態(tài)和環(huán)境。此外,后現(xiàn)代文化注重體驗,以游戲的態(tài)度對待生活,相對文字而已,微博的圖像體驗顯然更全面,而且隨著媒介技術的發(fā)展,這種體驗還在不斷地延伸。如果說圖像中也存在某種話語或權力關系,那么現(xiàn)代的媒介也在提供平臺迎合或闡釋圖像的話語表達。微博是個全民平臺,發(fā)布圖像的不僅僅是媒介,大眾更是其中的參與者,大眾即時發(fā)布著自己生活中的信息,與全體進行著對話,爭取著自己的話語權。
至此,我們可以將微博的圖文景觀置于觀者審美心理轉變的語境中來加以考察。后現(xiàn)代時代,大眾對于各類文化產品的審美動機,已經不像前現(xiàn)代文化時代的人們那樣去品位,普通大眾觀看的動機,往往只是打發(fā)時間、游戲心理、尋找群體認同,等等。在這個層面上,顯然圖片相對于文字更符合大眾的口味。文字需要人們的抽象思維,去想象文字的上下文語境以及線性的邏輯線索,而圖片和影像則有天然的優(yōu)勢,不需要觀者太多的思考,并消解了文字閱讀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而且,在微博的審美心理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所謂的“迷心理”或者“控心理”。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中,現(xiàn)代人渴望被關注,而微博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平臺,微博中圖像的現(xiàn)場感更能讓人產生被關注的錯覺,因而也備受現(xiàn)代人歡迎。而微博的即時性和便利性,使得人們的空閑無聊時間被填滿了,每天人們在空閑活動時全線圖片直播自己的狀態(tài),微博極其容易將人置于“被看”的角色上。
此外,媒介技術的發(fā)展也助推了微博圖文景觀的形成。當前,視覺技術的發(fā)展早已從手工藝圖像(繪畫)進入機械復制圖像(影視)時代,并開啟了數(shù)字擬像(數(shù)字化虛擬影像)時代。因此,技術對視覺文化的影響首先在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上反映出來。DV制作顛覆了傳統(tǒng)電影生產模式,數(shù)碼攝影改變了傳統(tǒng)膠片攝影方式,數(shù)字衛(wèi)星電視、網絡視頻、微博、微信等,使得圖像的生產變得簡單便捷。新視覺技術的發(fā)展對社會結構乃至文化結構有著很大的變革作用,人人都是作者或匿名的作者使得圖像由誰生產變得不重要了,技術發(fā)展正在導致巴特意義上的“作者之死”。在微博上,人們樂于上傳自己拍攝和制作的圖片,甚至影像。媒介技術的發(fā)展讓圖像有了大展身手的舞臺,現(xiàn)在只要有手機即可拍攝照片,有電腦即可編輯圖片,圖片的生產變得如此簡單。這似乎比構思長段文字要簡單,一張現(xiàn)場照片,所蘊含的內容,恐怕不是幾百個文字所能表達的。隨著未來網絡擬物技術的發(fā)展,電腦模擬現(xiàn)實社會景觀的能力越來越強,現(xiàn)實社會在虛擬電腦世界中也就成為了一幅幅圖景的直觀再現(xiàn),而圖文戰(zhàn)爭也只會是愈演愈烈。
二、微博圖文景觀的內在張力
微博作為現(xiàn)代新興的網絡媒體之一,其表現(xiàn)出來的圖文景觀無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圖像的興起以及對文字的優(yōu)勢,也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當下社會文化和審美心理的轉型。可以說,微博以有限的文字內容和鏈接式無限的數(shù)字圖像內容,為人們立體展現(xiàn)了一個虛擬視覺圖像世界,其表征出來的圖文景觀在一定程度體現(xiàn)了當前視覺文化語境中圖文關系的發(fā)展趨勢。
從微博的圖文景觀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文字與圖像的內在張力關系,而這種張力也是讀圖時代圖文之間的內在張力之表征。文字與圖像作為人類交際、思維和表情達意的符號系統(tǒng)都具有再現(xiàn)的功能,都可以通過符號本身的特性再現(xiàn)現(xiàn)實世界。無論視覺還是聽覺,圖像還是語言,都是我們生活所借助的符號,圖像與文字雖是不同的敘事系統(tǒng),兩者之間的張力卻是顯而易見的。圖像以鮮明、具體的形象打動受眾,給受眾帶來形象的直觀性和視覺快感,但卻讓受眾喪失了自由想象的空間,而文字的特性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失。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聯(lián)想性喚起受眾豐富的想象,以其獨特的、深層表意的功能挖掘文本的內涵。因此,圖像與文字雖相異,但是兩者卻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發(fā)展。筆者以為,文字的抽象性與圖像的形象性,文字的線性化與圖像的非線性化,文字的深層表意與圖像的淺層表象,文字的可說性再現(xiàn)與圖像的可視性再現(xiàn),使兩者形成一種互補和互動的張力關系。
在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中,文字的表達,或者說以文字為符號表征的文學,是通過文字的線性符號陳列而得以呈現(xiàn)。文學是一種通過語言文字媒介來實現(xiàn)其功能的藝術形式。文學語言在很多時候受制于理性,與個體的閱讀和思考等相關,它更多運用豐富的表現(xiàn)手法來合理安排材料,并通過對材料的理性思考來實現(xiàn)其價值和功能。在線性連續(xù)性符號空間中,語言文字所建構的空間可以給讀者提供更多反思和想象的可能。就文學而言,它是由詞語構成,詞語與詞語之間有著嚴密的邏輯關系,在表達上采取的是一種連續(xù)的、線性的表達方式,不同于圖像的直白、淺易。文學作為一種線性接受模式,文字符號具有的張力可以使讀者的思維有無限的延展性,讀者可以靜下心來專心地閱讀文學作品,透過語言想象其傳達的形象,領會作者的深層內涵。而圖像作為視覺藝術,通過視覺形象這種非線性符號而得以呈現(xiàn),圖像或形象在很多時候受制于感性,與個體的視覺感性和體悟等相連。從對立關系來看,文字作為語言的符號,是一種線性接受的模式,側重于時間的連續(xù)性,適合把握事物的動態(tài)過程,因此以語言為媒介的文體更適合敘事與論說。相對于文學的線性表達模式,圖像的非線性模式側重于空間性,所表現(xiàn)的是一種靜態(tài)的景象,傾向于形象和感性層面。此外,非線性圖像符號的虛指性,也使圖像能對世界進行更形象化和直觀化的表征。圖像的本性是視覺直觀,因此以圖像為媒介的藝術就表現(xiàn)為視覺形象的客體展示,也更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給觀者帶來視覺的快感。
此外,文字與圖像都具有再現(xiàn)的功能,都能以再現(xiàn)的方式表現(xiàn)某些內容,只不過前者是一種“可說性”再現(xiàn),后者是一種“可視性”再現(xiàn)。語言文字的再現(xiàn)不能像圖像那樣將客體的視覺面呈現(xiàn)出來,詞語只能被引用,但卻看不見客體,而想象或隱喻克服了這種不可能性,用這種視覺再現(xiàn)語言,通過隱喻將形象與文本縫合,成為一種形象文本。米歇爾認為,形象、圖像、空間和視覺性只能通過語言話語比喻想象出來,語言話語也要根據(jù)圖像比喻、聯(lián)想[1]米歇爾:《圖像理論》,陳永國、胡文征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頁。。在一幅畫中,文字是對畫中圖像及所代表的意義的闡釋,這種圖像與文字的相輔相成使語言變成可視的了。同時用文字記錄形象,也使圖中所傳達的精神形象成為一種可視語言。文字可將看不見的聲音和信息改造成可視的圖像,這種可視語言可以彌補圖像與使用圖像的語言之間的裂痕。
圖像作為“可視性”再現(xiàn),它的直觀性、可視性可以給受眾帶來視覺沖擊,滿足受眾的情感需求。文字作為“可說性”再現(xiàn),可以通過語言表達人物內心活動,它具有發(fā)散人思維的作用。在讀圖時代語境下,圖像所帶來的強烈的感官刺激使讀者無法展開深層思考,而文字的理性因素恰巧可以彌補這種視覺文化對受眾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消解。此外,圖像的可見性使它作為一種可視證據(jù)出現(xiàn)在文本中,圖像可以讓我們更加生動地想象過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圖像有各種用途,曾被當作膜拜的對象或宗教崇拜的手段用來傳遞信息或賜予喜悅,從而使它們得以見證過去各種形式的宗教、知識、信仰、快樂等。這正如伯克所言,盡管文字也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線索,但圖像本身卻是認識過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視覺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導[2]伯克:《圖像證史》,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這種形象的建構正是通過模仿和再現(xiàn)的方式來呈現(xiàn)的,是對圖像所要表達的文學文本的形象建構。
作為可視性的文本,圖像對形象的建構是創(chuàng)作主體通過觀察和感受外部世界,運用記憶、圖像或語言的媒介將外部世界再現(xiàn)出來,由此可見,圖像或文本的形成是主體對外部世界的反映和解讀。在形象的建構中,文本創(chuàng)作存在著文本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相似對應關系,文本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對應性也就意味著文本必然要對現(xiàn)實進行模仿與再現(xiàn)。正是通過這種再現(xiàn)的形式,藝術家才能使藝術品不再以鏡子似的反映個別或具體的事物,而是為這些事物創(chuàng)造一種內在的聯(lián)系,使外部世界的事物通過圖像或文字的形式展現(xiàn)在觀者面前。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說,詩人應當表現(xiàn)的是物質、形式、色彩、明亮、暗淡等一般的視覺特性,而人們借助于這些特性可輕易地分辨出大類——個體只是這個大類里的一員[3]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張照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頁。。因此,圖像再現(xiàn)形象,主要通過模仿和再現(xiàn)的方式來建構視覺形象,或者利用圖像的直觀性和可視性表現(xiàn)某些主題,以涉及文本避開的問題,表達未用文字表達的內容。
作為可說性的文本,文學用語言文字進行形象再造,也就是對語言所要描繪形象的文本建構。文學建構文本,是通過語言文字的形式來呈現(xiàn),比如詩的創(chuàng)作,人們讀到詩就會聯(lián)想到詩所描繪的意象。也就是說,文學用語言的形式構建了一種形象。這種形象不同于視覺的建構,它是由文字的深層表意引人深思的理性思考而形成的。相對于圖像來說,它并不是直觀的,而是需要運用想象完成的,是一種形象的間接性表達。此外,文學通過形象反映現(xiàn)實,文學的思想體現(xiàn)在形象中,其形象是經作家的概括、集中,用文字的形式在作品中重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學作品所塑造的雖然只是形象,但這一形象卻包含了豐富的概念。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文學借語言來塑造、描寫藝術,藝術家的構思過程是從語言中提煉準確、鮮明、生動的、形象化的語言過程。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就意味著文字是非感官的感受,非具象的形象。由于不具有物理形象的直觀性與真切感,文學所展示的形象僅僅是一種喻像。
文學作用于感官的間接性,表現(xiàn)形態(tài)的虛幻性成為它的缺陷。但也正是由于文學不具有物理形象的真切感和直接性,才不受物理規(guī)律的局限,才能提供更廣闊的審美想象空間。文學的語言藝術不僅可以通過人物的行動、獨白、對話等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也可以直接剖析人物的內心活動,揭示人物的心靈。而且,一切藝術的構思都需要文學的想象介入,一切的意境也要靠文學來提升,文學豐富的精神內涵和廣闊的自由想象的空間是圖像永遠無法替代的。文字符號具有的張力使讀者的思維有無限的延展性,使讀者透過語言想象其傳達的形象,領會作者的深層內涵。文字的深度性、表意性可以使觀者深入了解作品的深層意義。文本往往以標題或題名等形式出現(xiàn)在圖像中,從而把圖像轉變成“圖像文本”,通過文字的形式幫助或影響觀眾對畫面的理解,讓觀眾從字面上和隱義上去解讀它們。在圖配文的作品形式中,視覺信息因文字而得到強化,圖像文字被認為比單獨的圖像更能產生效果。圖像與文字的相互表達,使畫面和文本的再現(xiàn)相得益彰,這也就使作為“可說性”的文字與“可視性”的圖像具有關聯(lián)性與可比性。
文字作為一種線性接受模式,文字符號具有的張力使讀者的思維有無限的延展性;圖像作為一種非線性的模式,以形象性與直觀性著稱。而且,文字和圖像都具有“再現(xiàn)”的功能,都能以再現(xiàn)的方式表現(xiàn)某些內容。基于符號學的視域,文字與圖像在并存的文本體系中可以達到一種相互映襯的互文性。基于此,文字與圖像作為再現(xiàn)實踐的異質領域,將建構形象文本與視像文本關聯(lián)可能性。此外,圖像與文字也絕非簡單意義上的自我指涉體,在某種意義上,形象和文本、圖像和語言可以相互表達和相互言說:圖像具有文學功能,而文字具有圖像功能,圖文的相互言說建構了二者互文表達的共同情境。
需要注意的是,在討論語圖關系時,我們也不能忽略語言與圖像在再現(xiàn)層面的張力。這種張力,在我看來,可以從“言說的自我”與“被看的他者”之間的差異、講述與展示之間的差異、“道聽途說”式的文學與“親眼目睹”式的圖像之間的差異等方面具體展開。此外,這種張力也與特定的政治、文化領域內的斗爭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如話語與圖像之間的權力斗爭。在這個意義上,“文學遭遇圖像”也可以視為話語與圖像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表征,而這,也是我們在關注微博圖文景觀時需要注意的一個方面。
〔責任編輯:平嘯〕
On the Image-and-Word Landscape of Microblog and Its Intension
Yang Xiangrong
Compared to the age of traditional paper media,viewers'self-consciousness has enhanced unprecedented ly in the age of internetmedia,changing greatly their reading psychology and expectation. As one of today's new ly rising internetmedia,m icroblog,which disp lays an image-and-word landscape,is undoubted ly representative.The rising of images as well as their advantage over words reflects a more profound convers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aesthetical psychology.The image-and-word landscape embodies to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s and word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visual culture.Starting from the image-and-word landscape of m icroblog and further exp lor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s and words in virtual space will contribute to defining the intension and logic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mages and words in the context of visual culture.
m icroblog;the Image Age;the image-and-word landscape;intension
楊向榮,湘潭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411100
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文學與圖像關系研究:基于學理層面的考察”(11A126)、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語圖’藝術史的圖文關系研究”(12YBA298)、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6批特別資助“圖文關系的學理淵源及其內在張力研究”(2013T60230)、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1批面上資助項目“文學與圖像關系研究:基于‘語-圖’關系史的考察”(2012M51006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