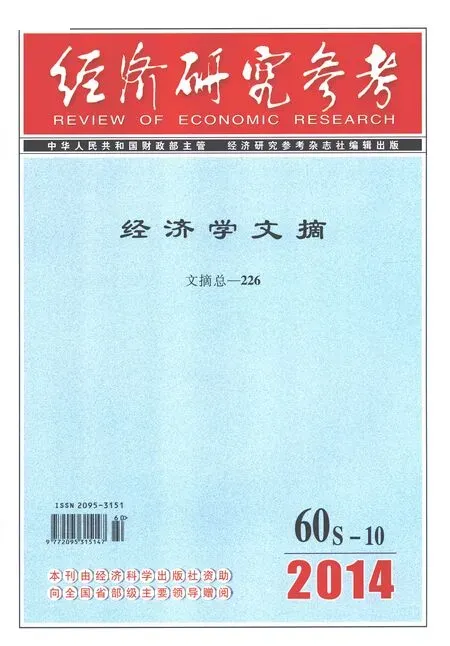中國“新常態”經濟的特征
汪紅駒
中國“新常態”經濟的特征
汪紅駒
1.經濟增長告別過去兩位數高增長模式,進入次高增長階段,官方文件對此的表述是經濟增長進入換檔期。2001~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年平均值為10.4%;從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個季度的GDP增長率都在7%~8%之間,2014年一季度GDP增長7.4%。根據“十二五”規劃目標,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夠了。李克強總理做公開經濟報告時也指出,如果中國每年要維持新增1000萬的就業,中國經濟增速只需要7.2%就可以了。
2.“保增長”和“控風險”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新常態。宏觀政策需要告別過去刺激依賴癥。保增長是保增長底線,如果經濟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區間,不會采取非常規的刺激措施。控風險仍是當前宏觀政策的焦點之一。導致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減速的周期性原因主要來自債務擴張和隨后的政策緊縮效應。2008年危機之后中國的強力刺激措施通過債務擴張實現經濟的超常反彈,杠桿率上升之后,產能過剩和局部的房地產價格泡沫無以為繼,只能通過痛苦的債務緊縮過程實現去產能、去杠桿的目標。去產能的典型表現是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長期負增長。為控制局部房地產泡沫風險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中國采納了緩慢縮減貨幣供應增速、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等結構性緊縮貨幣政策;同時加大反腐力度,財政支出增幅也時有放緩。很顯然,真正地去杠桿目標未實現之前,時斷時續的結構性金融緊縮和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將是常態。
3.結構調整的新常態。中國正從工業大國向服務業強國轉型,以第三產業衡量的服務業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經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伴隨著收入和資本存量的增長,中國正在從投資和出口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經濟過渡。從歷史經驗看,這必將明顯提升對服務業的需求,尤其是商貿物流、互聯網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另外,中國區域結構將趨向均衡發展的新常態。如京津冀經濟圈、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超大城市群等區域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發展空間。
4.要素供給的新常態約束。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資本形成的增速將隨儲蓄率有所下降;土地、能源和環境約束加大。經濟發展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環境成本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國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優勢將逐漸消失。全要素生產率難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時期內技術水平難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有所減弱。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城鎮化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再配置帶來的整體生產率上升,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但我國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數量出現下降趨勢。這些要素供給的新常態決定了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存在下移趨勢。
5.改革與完善國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態。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快速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存在兩個不平衡:一是內部不平衡,具體表現為: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第二,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第三,區域發展不平衡。二是外部不平衡,主要表現為憑借低成本優勢擴張貿易和經濟增長上升紅利吸引海外投資,形成多年國際收支雙順差,由此導致外匯儲備積累余額上升到讓人眼紅的水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上升,資源對外依賴程度不斷提高;受技術和能源結構限制,碳排放量大以及環境污染影響世界氣候環境;在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中中國位于中低端制造業,高技術產品和服務嚴重依賴國際進口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體不斷以這些外部不平衡問題對中國發難,如匯率操縱指控、貿易爭端、氣候談判、高技術轉讓限制等。這兩個內外不平衡是影響中國社會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根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規劃了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和路線圖。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因此從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促進內部和外部結構優化,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保障國家安全將是中國式“新常態”的重要內容。
6.中國式“新常態”的三種前景展望:一是定力不夠,重新出臺強力的刺激政策,勢必使債務杠桿率更加惡化,對局部區域的房地產泡沫火上澆油,未來經濟出現斷崖式墜落的可能性加大;二是政策預判失誤,微刺激的政策著力點不夠保持經濟的底線,或者受地緣政治沖突影響,能源供應中斷,經濟增長的底線守不住;三是保持定力,通過適當的微刺激,堅守保增長的底線,促進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釋放創新和改革紅利,到2020年順利實現改革目標和“十八大”雙倍增長計劃。
(夏摘自《經濟學動態》2014年第7期《防止中美兩種“新常態”經濟周期錯配深度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