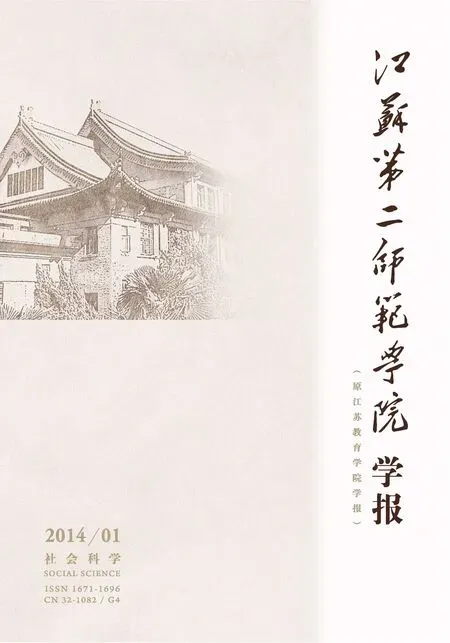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與經(jīng)典建構(gòu)——以中國(guó)畫(huà)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為例*
李 健
(南京大學(xué)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高級(jí)研究院,江蘇南京 210093)
中國(guó)畫(huà)作為特定的藝術(shù)史范疇,有一個(gè)漫長(zhǎng)的發(fā)展演變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由畫(huà)家及其作品所構(gòu)成的經(jīng)典序列,則是我們把握其演進(jìn)脈絡(luò)的重要?dú)v史線索。可以說(shuō),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在客觀上是藝術(shù)經(jīng)典得以最終形成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之一。所謂藝術(shù)的經(jīng)典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guò)藝術(shù)史的書(shū)寫(xiě)工作最終得以實(shí)現(xiàn)。如果說(shuō)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經(jīng)典序列已經(jīng)在反復(fù)的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過(guò)程中完全確立起來(lái),那么基于社會(huì)轉(zhuǎn)型語(yǔ)境對(duì)其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狀況予以剖析,將尤其有助于我們思考經(jīng)典建構(gòu)中的一些微觀問(wèn)題。對(duì)此,本文所關(guān)注的核心問(wèn)題是: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對(duì)于經(jīng)典建構(gòu)過(guò)程的具體影響,其實(shí)是可以通過(guò)其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自覺(jué)意識(shí)被我們把握的。具體來(lái)看,近百年來(lái),中國(guó)畫(huà)一直在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時(shí)代背景中艱難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期間,不斷有藝術(shù)家試圖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的張力中探尋中國(guó)畫(huà)的現(xiàn)代表達(dá)形態(tài)。其中,以徐悲鴻、林風(fēng)眠、吳冠中等人為代表的老一輩藝術(shù)家,已經(jīng)為我們開(kāi)拓出現(xiàn)代中國(guó)畫(huà)發(fā)展的多種可能路徑。但與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展軌跡不同的是,中國(guó)畫(huà)在現(xiàn)代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并沒(méi)有像前者一樣在藝術(shù)語(yǔ)言上遭到釜底抽薪式的革命。事實(shí)上,即使是進(jìn)入新世紀(jì),墨守成規(guī)、因循守舊的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仍然受大量藝術(shù)家以及欣賞者追捧。但是如果從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角度看,這種狀況無(wú)法令人滿意。近年來(lái)中國(guó)畫(huà)的熱度有所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種反思性的立場(chǎng)上實(shí)現(xiàn)的。唯其如此,中國(guó)畫(huà)才可在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進(jìn)程中扮演更無(wú)可替代的獨(dú)特角色,真正形成屬于當(dāng)代的經(jīng)典序列,也才可更自覺(jué)地立足于現(xiàn)代語(yǔ)境探尋自己的未來(lái)發(fā)展之路。具體到藝術(shù)家對(duì)于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自覺(jué)意識(shí),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予以探討。
一
如上所述,近年來(lái)藝術(shù)界對(duì)于中國(guó)畫(huà)的關(guān)注程度不斷得到提升。其中一個(gè)比較顯著的變化是,具有自覺(jué)歷史反思意識(shí)的有影響的中國(guó)畫(huà)畫(huà)展日益增多。這里僅以自2012年開(kāi)始啟動(dòng)的“重塑東方美”系列畫(huà)展活動(dòng)為例,無(wú)論以“水墨的現(xiàn)代詮釋”為主題的首展畫(huà)展,還是以“現(xiàn)代生活·水墨心印”為主題的第二屆畫(huà)展,無(wú)不體現(xiàn)出主辦方參與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勃勃雄心。正如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杜大愷先生在首屆畫(huà)展前言所指出的那樣,所謂“東方”不僅主要是指稱(chēng)中國(guó),而且既針對(duì)西方,針對(duì)其持續(xù)太久的話語(yǔ)霸權(quán),針對(duì)其依然事實(shí)存在的對(duì)世界的主導(dǎo)性;亦同時(shí)針對(duì)中國(guó),針對(duì)中國(guó)的生存尊嚴(yán),針對(duì)中國(guó)的文化尊嚴(yán),亦針對(duì)中國(guó)對(duì)世界的責(zé)任和關(guān)懷。所謂“重塑”意在構(gòu)建中國(guó)畫(huà)的“當(dāng)代性”,并以其“當(dāng)代性”實(shí)現(xiàn)歷史的延續(xù)。首屆畫(huà)展以“水墨的現(xiàn)代詮釋”為題,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水墨”仍是繪畫(huà)的主要形式,其對(duì)歷史的過(guò)去與未來(lái)都有更多的承擔(dān);另一方面亦關(guān)注“水墨”因“重塑”而必將遭際的困惑、思考和希望。這一自覺(jué)意識(shí),不僅僅是一次畫(huà)展及其相關(guān)系列活動(dòng)的邏輯起點(diǎn),更可視為藝術(shù)家參與藝術(shù)經(jīng)典建構(gòu)過(guò)程的重要前提。
我們知道,無(wú)論西方還是中國(guó),在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關(guān)節(jié)點(diǎn)上都有一些重要的變化。根據(jù)經(jīng)典社會(huì)學(xué)家馬克斯·韋伯的現(xiàn)代性診斷,西方社會(huì)現(xiàn)代轉(zhuǎn)型集中體現(xiàn)在價(jià)值領(lǐng)域的分化上。藝術(shù)也就是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變成一個(gè)完全依據(jù)自身游戲規(guī)則行事的獨(dú)立價(jià)值領(lǐng)域。從學(xué)科的角度來(lái)說(shuō),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正是在這一背景中成為我們理解藝術(shù)世界的重要學(xué)術(shù)行為之一。而藝術(shù)史的書(shū)寫(xiě)作為一個(gè)由身處藝術(shù)世界中所有成員共同參與的活動(dòng),并不是由藝術(shù)史家獨(dú)立完成的。這其中,藝術(shù)家所扮演的角色至關(guān)重要。因?yàn)殡x開(kāi)藝術(shù)家的存在,藝術(shù)史,尤其是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史的書(shū)寫(xiě)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對(duì)于藝術(shù)家而言,價(jià)值領(lǐng)域分化的直接后果是獨(dú)立身份和自由職業(yè)的確立。藝術(shù)家隨之對(duì)自身的職業(yè)定位也就有了更強(qiáng)烈的自覺(jué)意識(shí)。這一論斷,在中國(guó)畫(huà)的實(shí)踐語(yǔ)境中同樣是有效的。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從事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的文人或士的形象,在現(xiàn)代社會(huì)被角色相對(duì)單一的畫(huà)家形象所取代。這意味著現(xiàn)代畫(huà)家基本上只通過(guò)繪畫(huà)即可確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以此成為藝術(shù)史的主要書(shū)寫(xiě)對(duì)象。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藝術(shù)家只能以一種被動(dòng)的方式參與藝術(shù)史的書(shū)寫(xiě)。因?yàn)橐粋€(gè)由“藝術(shù)家(亦即畫(huà)家、作家、作曲家之類(lèi))、報(bào)紙記者、各種刊物上的批評(píng)家、藝術(shù)史學(xué)家、文藝?yán)碚摷摇⒚缹W(xué)家等等”構(gòu)成中堅(jiān)力量的藝術(shù)世界,需要所有成員的共同參與,才能不停運(yùn)轉(zhuǎn)并持續(xù)生存下去。[1](P.111)正因?yàn)槿绱耍囆g(shù)家在事實(shí)上始終都是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直接參與者。而藝術(shù)家有沒(méi)有一種參與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自覺(jué)意識(shí),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衡量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職業(yè)精神和藝術(shù)追求的高下。
之所以能如此理解,一個(gè)關(guān)鍵性的問(wèn)題就在于:這種自覺(jué)意識(shí),絕不簡(jiǎn)單是說(shuō)一位畫(huà)家首先要去考慮自己需要、應(yīng)該或希望在藝術(shù)史中扮演一個(gè)什么角色。更基礎(chǔ)性的問(wèn)題是,藝術(shù)家應(yīng)該考慮:我的繪畫(huà)能不能帶來(lái)真正區(qū)別于包括前人在內(nèi)的其他畫(huà)家的有價(jià)值的東西——當(dāng)然更不是琢磨如何用最經(jīng)濟(jì)實(shí)惠的方式,讓我的畫(huà)每平尺賣(mài)更高的價(jià)格。綜觀繪畫(huà)史的演進(jìn)之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gè)隨時(shí)代變遷而致繪畫(huà)語(yǔ)言形式革新的邏輯線索是清晰可辨的。一方面,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史價(jià)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guò)這種革新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另一方面,他們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又是我們把握這一邏輯線索的基本途徑。越是處于新舊激烈交鋒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史價(jià)值就越是體現(xiàn)在這一點(diǎn)上。西方繪畫(huà)史如此,中國(guó)繪畫(huà)史亦如此。現(xiàn)代以降,關(guān)于中國(guó)畫(huà)革新問(wèn)題的爭(zhēng)論幾乎從來(lái)都沒(méi)有停歇過(guò)。就藝術(shù)史的演進(jìn)邏輯而言,在一個(gè)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時(shí)代背景之下,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進(jìn)行必要的革新,無(wú)疑是其得以進(jìn)入藝術(shù)史視野的前提條件之一。但就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雖則徐悲鴻、林風(fēng)眠、吳冠中等諸前輩藝術(shù)家已經(jīng)極大地開(kāi)拓了中國(guó)畫(huà)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然其現(xiàn)代轉(zhuǎn)型工作恐怕仍在繼續(xù)當(dāng)中。自陳獨(dú)秀在《美術(shù)革命——答呂澂》中倡導(dǎo)革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命以來(lái)[2],中國(guó)畫(huà)仍始終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尋求平衡點(diǎn),并不斷展現(xiàn)其頑強(qiáng)的生命力。需要說(shuō)明的是,在該文刊發(fā)之前,藝術(shù)實(shí)踐領(lǐng)域的革新運(yùn)動(dòng)業(yè)已展開(kāi)。不過(guò)作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領(lǐng)袖于其核心陣地上發(fā)布的關(guān)于中國(guó)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宣言式文本,它的意義遠(yuǎn)超出藝術(shù)活動(dòng)本身,因此極具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標(biāo)本意味。但作為藝術(shù)史的書(shū)寫(xiě)對(duì)象,身處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之中的中國(guó)畫(huà)又不得不一再面臨被邊緣化的境地。這一方面反映出中國(guó)畫(huà)經(jīng)漫長(zhǎng)歷史積淀留存下來(lái)的遺產(chǎn)本身所具有的極大價(jià)值;另一方面也可理解為中國(guó)畫(huà)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仍在路上,任重道遠(yuǎn)。至少,從更為宏闊的藝術(shù)史視野出發(fā),諸如中國(guó)畫(huà)的價(jià)值取向、語(yǔ)言建構(gòu)及其與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生活的關(guān)系等問(wèn)題,仍有待于我們通過(guò)作品來(lái)回答。
二
以上述立論為前提,我們不難理解,要判斷一個(gè)藝術(shù)家是否具有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自覺(jué)意識(shí),就必須審視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能否展現(xiàn)出一種區(qū)別于他人的存在價(jià)值。就藝術(shù)史發(fā)展的宏觀脈絡(luò)而言,這種價(jià)值又可以被指稱(chēng)為一種具有增值效應(yīng)的文化價(jià)值。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作品,以“文化增值”為尺度,對(duì)應(yīng)的則是“技術(shù)性復(fù)制”。因此,這一尺度為我們書(shū)寫(xiě)藝術(shù)史提供了一個(gè)從“技術(shù)性復(fù)制到文化增值”的考察路徑,再以此審視藝術(shù)家及其作品,將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解讀其在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過(gu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無(wú)疑,這里所謂技術(shù)復(fù)制,主要不是在本雅明《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一文中的意義上使用的。它不特別指向因技術(shù)手段進(jìn)步而遭際的藝術(shù)生產(chǎn)形式的變化,而指涉更寬泛意義上的繪畫(huà)技巧、技能。以中國(guó)畫(huà)來(lái)說(shuō),所謂技術(shù)性復(fù)制,主要是指在技術(shù)層面可以通過(guò)學(xué)習(xí)熟練掌握的各種繪畫(huà)技巧、技能乃至情感、觀念表達(dá)的常規(guī)化圖式等。
毫無(wú)疑問(wèn),中國(guó)畫(huà)經(jīng)過(guò)那么漫長(zhǎng)的發(fā)展歷程,在它走入現(xiàn)代之際,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創(chuàng)作程式。所謂“墨守成規(guī)”,大抵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守成易,變更難。單就從事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的畫(huà)家而言,因循守舊未必日子過(guò)得不滋潤(rùn)。甚至因?yàn)橛辛四敲匆惶紫热肆粝碌倪z產(chǎn)——不僅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面的遺產(chǎn),也包括藝術(shù)接受方面的遺產(chǎn),總可以把畫(huà)賣(mài)出個(gè)好價(jià)錢(qián),把日子過(guò)得有滋有味。這就是所謂“慣習(xí)”的力量。它不僅僅是藝術(shù)家的問(wèn)題,也涉及欣賞者、批評(píng)家等。可以說(shuō),如果藝術(shù)家只是將繪畫(huà)作為一種完全私人化的興趣、一種表明個(gè)體身份的職業(yè),那么這樣一個(gè)積淀如此深厚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足夠玩味,足夠讓一個(gè)畫(huà)家活得有滋有味了。當(dāng)然他也就不會(huì)再難為自己,去琢磨什么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問(wèn)題。但對(duì)于有參與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意識(shí)的藝術(shù)家來(lái)說(shuō),思考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yàn)椤凹夹g(shù)復(fù)制”式的繪畫(huà)創(chuàng)作,是很難進(jìn)入藝術(shù)史視野的。但凡進(jìn)入藝術(shù)史視野的,無(wú)疑都是那些具有文化增值意味的藝術(shù)家藝術(shù)品。韋伯有言,“一件真正‘完美’的藝術(shù)品,永遠(yuǎn)不會(huì)被超越,永遠(yuǎn)不會(huì)過(guò)時(shí);每個(gè)人對(duì)它的意義評(píng)價(jià)不一,但誰(shuí)也不能說(shuō),一件藝術(shù)性完美的作品被另一件同樣‘完美’的作品超越了”[3](P.82)。科學(xué)史家托馬斯·庫(kù)恩也指出藝術(shù)史與科學(xué)史具有非常不同的建構(gòu)邏輯,因?yàn)榍罢呓⒃谒臒o(wú)窮可能的豐富性之中,構(gòu)成藝術(shù)史的所有內(nèi)容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這一論斷是有前提的,即能夠進(jìn)入藝術(shù)史的藝術(shù)品無(wú)疑都具有其區(qū)別于其他作品的獨(dú)特性。簡(jiǎn)單點(diǎn)說(shuō),它必須具有某種文化維度的增值效應(yīng)。所謂永遠(yuǎn)不會(huì)被超越,永遠(yuǎn)不會(huì)過(guò)時(shí),就在于它的存在始終可以為藝術(shù)史增添價(jià)值。
如果中國(guó)畫(huà)的演進(jìn)史還不夠令我們警醒,我們不妨看一看中國(guó)文學(xué)史,作為一個(gè)參照。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一向有“體以代變”“一代之文學(xué)”的說(shuō)法。綜觀中國(guó)文學(xué)史,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學(xué)樣式。及至現(xiàn)代,盡管傳統(tǒng)的詩(shī)詞歌賦仍然有眾多的愛(ài)好者,仍然有人從事詩(shī)詞創(chuàng)作,但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幾乎已沒(méi)有傳統(tǒng)詩(shī)詞的書(shū)寫(xiě)空間了。因?yàn)槿文闳绾蝿?chuàng)作,也已很難擺脫技術(shù)復(fù)制式的創(chuàng)作窠臼,與文學(xué)史的“文化增值”效應(yīng)基本無(wú)涉。中國(guó)畫(huà)或許還沒(méi)有到這個(gè)地步,但在當(dāng)前中國(guó)藝術(shù)界大致三足鼎立的態(tài)勢(shì)下,“當(dāng)代藝術(shù)”作為一個(gè)專(zhuān)屬名詞,幾乎不關(guān)涉中國(guó)水墨。從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角度而言,這至少應(yīng)是我們自覺(jué)反思的核心問(wèn)題之一。而要反思這樣一個(gè)相對(duì)宏大的藝術(shù)史問(wèn)題,還需要從更加微觀的現(xiàn)當(dāng)代畫(huà)家畫(huà)作入手,思考我們時(shí)代的中國(guó)畫(huà)究竟具有多大的“文化增值”效應(yīng),而不只是因襲前人的“技術(shù)性復(fù)制”的產(chǎn)物。
三
近年來(lái),中國(guó)畫(huà)持續(xù)受到關(guān)注的一個(gè)關(guān)鍵因素,就在于一批中國(guó)畫(huà)畫(huà)家開(kāi)始自覺(jué)思考如何通過(guò)作品的創(chuàng)新來(lái)突破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束縛,以拓展藝術(shù)表達(dá)的空間。仍以“重塑東方美”畫(huà)展活動(dòng)為例,無(wú)論首屆畫(huà)展的七位參展畫(huà)家,還是第二屆畫(huà)展的15位畫(huà)家,希望突破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程式的意圖無(wú)疑是清晰可辨的。正如畫(huà)展策展人兼參展畫(huà)家、南京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林逸鵬教授在首屆畫(huà)展時(shí)所強(qiáng)調(diào)的那樣:“水墨畫(huà)的創(chuàng)作客觀上進(jìn)入轉(zhuǎn)型期,但如果這個(gè)轉(zhuǎn)型無(wú)限期拖延下去,就是藝術(shù)家的責(zé)任了。”這種責(zé)任感可以說(shuō)是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自覺(jué)意識(shí)的另一種形式的表達(dá)。若從“文化增值”的角度再做進(jìn)一步微觀考察的話,這些作品帶給我們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視覺(jué)體驗(yàn)可以概括為:富于“韻味”的“陌生化”體驗(yàn)。
我們知道,本雅明在《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一文中,區(qū)分了傳統(tǒng)藝術(shù)與現(xiàn)代藝術(shù)之間的根本不同。其中前者富于“韻味”,具有一種膜拜價(jià)值;后者帶給人一種“震驚”體驗(yàn),具有的只是一種展示價(jià)值。[4](PP.231-264)寬泛地說(shuō),傳統(tǒng)水墨畫(huà)與現(xiàn)代水墨畫(huà)或可作此區(qū)分。但就個(gè)人體驗(yàn)來(lái)說(shuō),問(wèn)題又并不如此簡(jiǎn)單。從觀感來(lái)說(shuō),現(xiàn)代水墨畫(huà)的現(xiàn)代意味,與本雅明以現(xiàn)代主義尤其是達(dá)達(dá)派延展而來(lái)的“震驚”體驗(yàn),未必完全接洽。若說(shuō)“震驚”,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中的裝置藝術(shù)、行為藝術(shù)早已一次次挑戰(zhàn)我們視覺(jué)體驗(yàn)的極限。這種不同意味的現(xiàn)代體驗(yàn),或許恰恰是把握“水墨的現(xiàn)代詮釋”的一條有益線索。
具體來(lái)說(shuō),縱觀兩次畫(huà)展的參展作品,給觀者的一個(gè)突出印象便是既不乏“水墨”的傳統(tǒng)基因所帶來(lái)的“韻味”,又由于對(duì)“水墨”的現(xiàn)代挪用而造成特定的“陌生化”效應(yīng)。之所以會(huì)產(chǎn)生這樣一種特殊的視覺(jué)體驗(yàn),關(guān)鍵性的因素恐怕還是參展畫(huà)家在其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將自己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yàn)“融入”水墨世界的自覺(jué)意識(shí)。這種現(xiàn)代經(jīng)驗(yàn)里面,既包含他們面對(duì)全球語(yǔ)境所吸納的多元呈現(xiàn)的繪畫(huà)表現(xiàn)方式,更有畫(huà)家身處當(dāng)下而獲得的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的生存體驗(yàn)。所謂“韻味”,在于作品并沒(méi)有徹底遺棄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的精神內(nèi)核以及表現(xiàn)形態(tài)。換言之,中國(guó)畫(huà)的創(chuàng)新不是另起爐灶重新開(kāi)張,重塑必須建立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優(yōu)秀文化基礎(chǔ)之上。而所謂“陌生化”,則主要指涉畫(huà)家通過(guò)對(duì)“水墨”這一傳統(tǒng)繪畫(huà)語(yǔ)言形式進(jìn)行自覺(jué)改造之后必然帶來(lái)的結(jié)果。“陌生化”作為文藝?yán)碚擃I(lǐng)域的一個(gè)專(zhuān)有術(shù)語(yǔ),與“自動(dòng)化”相對(duì)應(yīng)。后者關(guān)乎“慣習(xí)”,意指我們的語(yǔ)言如果處于習(xí)慣成自然的狀態(tài)之下,就會(huì)成為缺乏原創(chuàng)性和新鮮度的自動(dòng)化語(yǔ)言;行為處于這種狀態(tài)之下則會(huì)變成自動(dòng)化行為。如此,我們的一切活動(dòng)都將成為一個(gè)自動(dòng)化環(huán)境中的無(wú)意識(shí)活動(dòng)。“陌生化”正好與此相反,它以“新奇”體驗(yàn)為訴求,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自動(dòng)化語(yǔ)言及行為的反撥。但其對(duì)“新奇”的追求,意不在新奇本身,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手段,使人得以在社會(huì)生活的麻木狀態(tài)中警醒起來(lái)、亢奮起來(lái)。面對(duì)仍習(xí)慣于傳統(tǒng)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程式、批評(píng)模式、接受方式的藝術(shù)家、批評(píng)家以及欣賞者,這種“新奇”感所帶來(lái)的視覺(jué)沖擊既是一種感官層面的“喚醒”,更是對(duì)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自覺(jué)意識(shí)的一種“召喚”。[5](PP.1-10)
不失水墨立身于傳統(tǒng)的特有“韻味”,又借助現(xiàn)代語(yǔ)匯給人以警醒意味的“陌生化”體驗(yàn),這既是對(duì)真正面向當(dāng)代社會(huì)生活進(jìn)行中國(guó)畫(huà)創(chuàng)作的畫(huà)家作品的總體性把握,也是立于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來(lái)思考當(dāng)代中國(guó)畫(huà)的價(jià)值取向、語(yǔ)言建構(gòu)以及解讀方式等問(wèn)題的一個(gè)很好的角度。就經(jīng)典建構(gòu)而言,作品無(wú)疑是最有說(shuō)服力的。無(wú)論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這些作品都帶給我們進(jìn)一步思考中國(guó)畫(huà)未來(lái)走向的巨大空間。在作品背后,則隱藏著藝術(shù)家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史書(shū)寫(xiě)的自覺(jué)意識(shí)。也正是這種自覺(jué)意識(shí),強(qiáng)化了藝術(shù)家在經(jīng)典建構(gòu)過(guò)程中的主體地位。在這個(gè)意義上,藝術(shù)家并不僅僅為藝術(shù)史的書(shū)寫(xiě)提供素材這么簡(jiǎn)單,他們本身就是這一書(shū)寫(xiě)過(guò)程的參與者,與藝術(shù)史家、批評(píng)家以及理論家共同建構(gòu)起藝術(shù)史的經(jīng)典序列。
[1][美]喬治·迪基.何為藝術(shù)(Ⅱ)[A].李普曼編.當(dāng)代美學(xué)[M].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6.
[2]陳獨(dú)秀,呂澂.美術(shù)革命——答呂澂[J].新青年,1919(1).
[3][德]馬克斯·韋伯.以學(xué)術(shù)為業(yè)[A].韓水法編.韋伯文集[M].北京:中國(guó)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
[4][德]本雅明.機(jī)械復(fù)制時(shí)代的藝術(shù)作品[A].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M].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8.
[5][俄]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手法的藝術(shù)[A].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國(guó)形式主義文論選[M].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