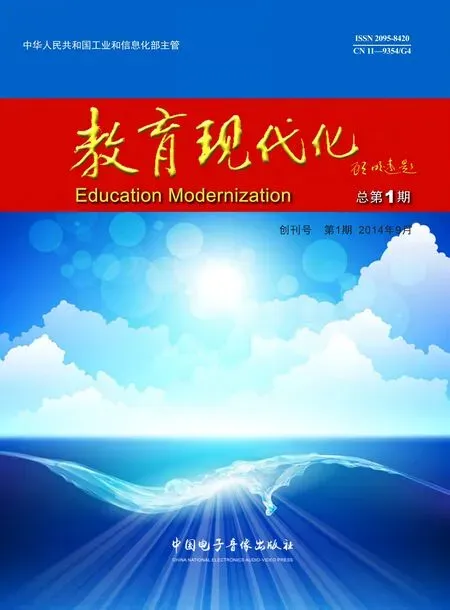“自愛”到“道德”
——盧梭道德情感的線索及啟示
李文嫻,傅建明
(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盧梭在其教育著作《愛彌兒》對他所假設的教育對象愛彌兒進行一系列的自然教育。在第四卷中他集中談論了自己關于道德教育的設想,試圖回歸到人自身去尋求道德的情感基礎。“自愛”就是這樣一個熠熠閃光的概念,彌散于盧梭道德教育所構建的情感空間。因而,本文立足于盧梭道德情感的線索去詰問當今德育的困境,試著探索一種有益的啟示。
一 道德情感的獨特價值及失落
哲學家休謨在描述道德情感時曾指出:“道德概念本身要求一種人類情感,這種情感使各個角落、最遙古的人的行為也成為道德上贊許或反對的對象”[1]。人是一種情感動物。有如俗語所述“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很多程度上是以情感維系的,而個體的判斷、行為選擇等也始終帶有情感的色彩。與一般性的、動物性的情感不同,道德情感是人所特有的高級社會性情感,是人在一定的道德認識基礎上對現實生活中道德現象、道德關系和道德行為等表現出的一種愛憎或好惡的情緒態度。它從更深層次上表征著個體的道德面貌。
在當今的語義環境中,我們衡量一種行為道德與否很多程度上是從社會關系角度切入,以行為的動機和社會后果加以衡量。歸根究底,“道德”處理的是“他人與我”的問題。從本質上說,道德是以人為主體的,是人合目的性的現實表現和價值形態[2]。而真實的道德行為必須基于人的需要并直接與人的情感一致,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的確立,進而衍生出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所做出的選擇。毋庸置疑,在道德判斷與道德行為選擇的過程中,道德情感不可能“缺席”,相反,它是溝通道德橋梁最為直白的一種聯系,它提供最為強勁的力量和動力。道德情感作為一種內在的心理機制和重要的精神力量,對完善自我、提升人格具有重要作用[3]。個體對其行為的選擇、發生與塑造都注入了強烈的“非理性”因素——情感,而在道德行為的選擇和生發過程中道德情感無疑也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誠如布拉梅爾德所述:“人類決不完全是理性的動物,他們總是無意識地深受感情和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的”[4]。只有經由主體情感體驗,外在的道德要求和規范才能真正為個體所認可并內化為自身的道德信念,并具化為現實的道德行為。不僅如此,個體在對道德行為或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時,往往采用“對”與“錯”、“應該”與“不應該”等價值關系進行表達,而這種個人傾向性的表達都是基于個體的情感體驗所做出的判斷。有別于自然科學命題的嚴密邏輯和精準答案,道德價值判斷的內容和對象總是摻雜著個體的道德情感傾向,為這種“非理性”因素所渲染和滲透。不同于一般性的情感,道德情感不單純是個人意義上的“恣意妄為”,而更多的是社會道德規范與要求的理性要素與個人非理性要素的統一,實質上蘊含了道德理性的內控機制。在個體的道德價值判斷的過程中,道德情感與道德認知相互協調,立足于社會道德規范的一般性原則和要求,對行為的動機、效果等做出理性而不失人情味的判斷。
反觀現實,道德教育的真實場景中卻不乏各種難題。面對這樣或那樣的道德困境,我們抨擊社會大環境下人情冷漠、道德淪喪的種種現象與慘劇,指責學校德育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冷漠、表里不一的“道德知識容器”。但當我們開始試著發掘這些現象背后的深層根源并將矛頭指向唯經濟主義與唯工具理性對人和教育的宰割時,我們似乎將自身置于這種物質與精神“分裂癥”的“被害者”席位。而事實上,這一切絕不是毫無緣由,更不應是“無作為”的。我國“德育”在總體上偏重道德說教、社會-政治說教,人們對此不乏共識[4]。也有國外學者指出,認知性道德教育理論無法解釋青少年中較常見的“故意失德”現象[5]。無論是“故意失德”的現象還是那些讓人唏噓不已而又無奈的道德冷漠事件,當事人并非對此類不道德行為的惡劣后果“一無所知”,更不是道德認知的匱乏或意志的缺陷,而是缺乏遵循道德規范的動力和情感支持。由此可見,將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務定位于道德認知能力的培養無論是從理論還是現實依據上來看,確實有失偏頗。道德教育呼喚道德情感的參與,而道德情感的積極配合更是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前提和關鍵。因此,道德教育必須關注道德情感這一重要維度,去追問道德情感的重要線索,去尋求一種解答。
二 道德情感的線索及其解讀
任何一個理論都有一個邏輯起點,同理,道德情感也有其特定的情感線索。道德教育對道德情感的關注必須立足于對這一線索的準確把握。而盧梭在《愛彌兒》中對道德情感及其道德教育詳盡的論述無疑為此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價值。如果說盧梭道德教育的理論起點是他對人性以及人性發展的認識,而他關于道德情感的線索則以“自愛”作為邏輯起點,進而衍生出其他社會性的情感,并最終指向道德。
(一)起點:“自愛”
盧梭這么說道:“我們的種種欲念的發源,所有一切欲念的本源,唯一同人一起產生而且終身不離的根本欲念,是自愛”[6]。在他看來,“自愛”是最為原初的情感,是其他情感衍生、發展的根基。在對“自愛”的重要性作了一番敘述之后,他這么說道:“為了保持我們的生存,我們必須要愛自己,我們愛自己要勝過愛其他一切的東西;從這種情感中直接產生這樣一種結果:我們也同時愛保持我們生存的人”[6]。顯然,他所說的“自愛”究其本質是一種自我保存的情感,表現為個體為對自己生命的觀照。“自愛”作為美德倫理學的一個基礎性范疇,它表達的是一種最重要的基礎美德[7]。一直以來,西方倫理學對“自愛”這一范疇始終保持著研究熱情,無論是亞里士多德對無邏各斯的“壞人的自愛”和遵循邏各斯的“好人的自愛”的區分,還是伊壁鳩魯、霍布斯、愛爾維修、休謨、沙夫茨伯等思想家對自愛的解讀,他們或多或少支撐著自愛這一情感之于個體生命的重要意義,并肯定了自愛本身蘊含的道德特性。道德意義上的自愛是對自我人格、榮譽與價值的一種恰如其分所謂態度和要求,表現為珍視自己的生命,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8]。與自私截然不同,真正的自愛必定建立在自我需要和社會需要的平衡點上。正如盧梭所言,“自愛始終是很好的”,它不等同于“自私”,“敦厚溫和的性情是產生于自愛,而偏執妒忌的性情是產生于自私”[6]。誠然,“自愛”首先指向個體自己,但這并不否認自愛對他人的效用。正如亞里士多德曾說的“好人,必定是一個自愛者”[7]。自愛是愛己與愛人的立足點,是個體的存在是一切道德行為可能的前提。無論是自愛還是他愛乃至上升到對全人類道德理想的熱愛,最終都是必須以“我”的存在,“我”的感受,“我”的需要,“我”的標準為前提,將“自愛”作為德性涵養的生長起點。
(二)延伸:“憐憫心”
在“自愛”這個情感起點之后,盧梭描述了這么一種情感:“我們之所以愛我們的同類,與其說是由于我們感到了他們的快樂,不如說是由于我們感到了他們的痛苦;因為在痛苦中,我們才能更好地看出我們天性的一致,看出他們對我們的愛的保證。如果我們的共同的需要能通過利益把我們聯系在一起,則我們共同的苦難可通過感情把我們聯系在一起”[6]。在他的觀點里,“憐憫心”是出于人類對“共同的苦難”的覺察。“憐憫心”或者說“同情”,作為一種社會性情感,它不同于原始的“自愛”情感,它開始轉向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的范疇。倫理學者何懷宏就曾說:“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憐憫之情作為人類最原始和最純正的一種道德情感,對于使人們履行最起碼和最基本的道德義務,使社會不致長久墮入野蠻的巨大意義。所以,不僅現代社會的底線倫理乃至我們整個生活都需要這種道德情感‘墊底’”[9]。而在盧梭的觀點里,“憐憫心”是可以培育的,需要加以認識并引導。“為了使孩子變成一個有感情和有惻隱之心的人”[6],他指出要讓他們知道有一些跟他相同的人也遭受到他曾經遭受過的痛苦,也感受到他曾經感受過的悲哀。從而使這種對同伴的同情與關懷“愈來愈擴充的力量用之于那些能擴大他的胸襟,能使他關心別人,能使他處處忘掉他自己的事物”[6]。不僅如此,盧梭認為人們單單從“憐憫心”就足以衍生擴展出人類的一切道德情感,諸如“慷慨”、“寬容”、“仁義”等等。憐憫心的情感使人們不會因為關注自己的生活狀況而對他人的處境麻木不仁,不會為了個人私利而罔顧大眾的利益和苦難,它將促使我們與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這種“共情”不但是社會道德認同感的根源,也是評價人們行為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重要因素。霍夫曼在《移情與道德發展——關愛和公正的內涵》中就這么論證道:“移情的發展階段與個體道德發展的過程是一致的,移情是情緒社會化的基礎,因而也是道德發展的基礎”[10]。
(三)升華:“良心”
如果說“自愛”首先指向的是個體的生命,“憐憫心”擴充的是自己對他人的相對情感,那么“良心”規范的則是己與他人的關系。
在盧梭看來,良心為一種人之共有的道德情感,它是人類天生的一種稟賦,是人類的一種先天的內在情感,而這也與良心的客觀普遍性特征相互吻合[11]。《愛彌兒》中有這么一段論述:“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生來就有一種正義和道德的原則;盡管我們有自己的準則,但我們在判斷我們和他人的行為是好或是壞的時候,都要以這個原則為依據,所以我把這個原則稱為良心”[6]。簡而言之,良心是一種辨別道德善惡的能力。它是基于道德認知、意志等因素統合而成的,表現為踐行一定道德義務時的責任感及對現象與行為的評價能力。曾有學者對良心先驗的觀點加以批判。而實際上,盧梭所謂的良心是一種自然的潛能,就如同種子一般,它的生長需要陽光、土壤和雨露。他這么引證到“我就試想指出從心靈的最初的活動中是怎樣產生良心的真正呼聲的”,可見,良心的“產生”就如同他對自然教育的深刻理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如前所述,“自愛”和“憐憫心”是道德情感中即為關鍵的環節,那么,“良心”的作用又體現在何處呢?誠然,道德的社會屬性必定將一些特定的要求與規范傳遞并附加給我們,而我們的道德情感在篩選和處理這些道德原則、要求的同時,也為這些外在賦予更為強大的內驅力。而在這個過程中,道德情感絕不僅僅是指向自我的“自愛”和針對他人苦難所產生的憐憫情感那么簡單,對行為或現象的道德價值判斷乃至道德行為的形成,始終需要一個指揮棒的角色,而這就是“良心”。可以說,良心是更為深層、理性化的道德情感,它所體現出對道德價值準則的自覺把握和責任感是人們道德發展由他律上升至自律的重要標志。可以說,道德良心對行為的控制是人的道德綜合水平的顯現[8]。
(四)終點:“道德”
“只要把自愛之心擴大到愛別人,我們就可以把自愛變為美德,這種美德,在任何一個人的心中都是可以找到它的根柢的”[6]。至此,盧梭將道德情感的故事主線呈現在我們面前。正如他所說的“人所應該研究的,是他同周圍的關系”[6]。而道德,究其實質,就是一種關系范疇。
在呈現“自愛”、“憐憫心”、“良心”這一系列情感層次和次序之后,盧梭聲稱“我們終于進入了道德的境界”[6]。在他的道德體系中,“自愛”、“憐憫心”以及“良心”這一系列情感線索是原始情感的循序發展,指向的不是純粹道德的概念,而是經由理智啟發最終形成的關于“善”與“惡”的道德觀念。他這么說道:“由自愛而產生的對他人的愛,是人類正義和本原。《福音書》中所包括的全部道德,歸納起來就是這一條法則”[6]。現代意義上的道德,從一定程度來講,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特殊形式,它更多地被用于規范特定社會形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大多數的場合,道德行為更近似于個體所選擇并采取的某些具有道德意義的親社會行為,而這類行為恰恰是特定社會或族群所認可并推崇的。從盧梭個人所贊譽的“自愛”到普羅大眾均推崇的“憐憫”和“良心”,這條道德情感線索的實質就在于“自愛”到“仁愛”的轉換。從個人的自我保存情感到形塑社會形態與合理秩序的移情性情感,“自愛”開始借由“憐憫心”與“良心”這種相對的社會性情感,實行個體對他人“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體貼著想,進而完成親社會行為。而這種內在的力量,究其實質,是個體主動建構的道德觀念和判斷,是內化了的道德動機,幫助個體誘發并生成真正的道德行為。
三 盧梭道德情感線索對道德教育的啟示
許多道德理論研究與實踐都說明,道德認知不一定導致道德行為,從道德認知到道德行為,其中介是以道德情感為核心的意向系統[12]。盧梭關于道德情感的內部機理和線索,無疑為我們把握這種動力系統提供了更為細節、詳盡的參考,也為我們的德育實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啟示。
(一)理清道德教育的根基,關注個體生命與道德情感
道德來源于生命,來源于人的自愛,關注生命是道德理想真正意義之所在。道德教育不是一種外在強加的規訓,而是指導生命獲得意義的過程。反觀現今的德育實踐,始終固著于“灌輸式”、“知識授受”的形式,試圖以抽象的道德說教向個體傳遞種種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及行為準則。顯然,通過這種外爍的過程,學生固然學習到了系統的道德理論,卻無法真正形成對道德價值的內在認同和情感共鳴。最終,他們學習到的只是脫離他們主體價值的“教條”,而不是那些能夠震撼他們心靈的道德情感和真實體驗,難以激發踐行道德行為的意愿和動機。而這也正是現今道德教育的感染力和實效性低下的根源所在。而要厘清道德教育的根源問題,就要首先明確一個基本性前提,即道德教育的根基。
作為一種自然存在,個體生命的價值不言自明。道德所起到的框定社會秩序、規范行為的功能不可能脫離人的生命存在。無論特定的條件、對象等因素如何變遷,道德的本質屬性依舊是為人類服務。而道德教育作為一種道德傳遞和授受的重要載體和平臺,它所面向的主體依舊是人。因而,道德教育必須扎根于個體生命,首先立足于“自愛”這一原始情感,在關照個體生命價值的前提下予以展開。以往的道德教育常常在處理“他人與我”的關系問題上會不知不覺地陷入一種人我不對稱的境地。一味地提倡抑制自我而將集體或他人的利益置于一個絕對優先的位置,倡導犧牲個人的自我價值以獲取外在的“道德楷模”之類的贊許的稱謂。在這種觀念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集體的,是忽視個體珍貴的生命價值的。而事實卻是,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愛人與愛己,并非絕對的二元對立,更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排斥關系。更多的時候,只有個體生命被給予恰當的尊重,個人對道德才能真心實意地迸發出強烈的熱情和積極踐行的內驅力。盡管道德情感具備“非理性”、“激情”的成分一直以來備受理性主義的詬病,但它在道德價值判斷和選擇過程中卻體現出內在動力的獨特價值,為道德主體搭建情感共鳴的橋梁。
因而,真正的道德教育必須立足于這兩大根基,關注道德主體自身的生命價值,激發個體積極的道德情感體驗。一方面,要從觀念上實現無主體、無生命的道德教育模式向主體性道德教育模式的轉變,寓生命教育于道德教育,關注道德主體的價值,既要關注道德所要求的社會效益和集體利益,又要重視個體生命的深刻意義。另一方面,道德教育要重視道德情感在個體道德發展過程中的內驅作用,變革過去只重道德認知或道德規范的錯誤偏向。無論是何種教育場景,道德教育都不應忘卻“人”的獨特價值,只有這樣,才能讓道德迸發出生命和情感的活力,也只有這樣,道德教育才能實現從烏托邦式的空想向高效可行的德育范式的轉變。
(二)創設“真”的道德情境,喚醒主體的道德情感
任何道德情感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與發展起來的。情感培育不可能脫離具體的情境而產生,情境是整個道德情感培育中的重要而有意義的組成部分。現今常被指責與詬病的“填鴨式”、“灌輸式”的道德教育形態很大程度就源自于對道德情境的忽略。由教師、家長、社會輿論等外部因素所強加的條條框框由于缺乏相應的情境,往往難以引起道德主體積極的情緒體驗。在不同的道德教育場域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么一種矛盾,那就是教育者精心安排的教育情境大部分是虛擬情境,而那些容易被人們忽視的生活情境卻被排除在外。更多的時候,教育者更傾向于選擇一些“高大全”的道德情境,以盡可能拔高道德水平。然而,在真正的實施過程中卻發現,這一類虛擬情境卻是脫離一般人的現實生活,而過高的道德要求也是難以企及的。可以說,這樣的虛擬情境對道德情感的生成的效果非常有限。它們是不真實的。無論這種虛擬情境有多么逼真、生動形象,但對學習者來說,至多是一種“旁觀者情境”,與他們的實際生活始終存在一定的距離,他們的道德情感實際是“不在場”的。因此,我們應盡可能地創設“真”的情境。所謂“真”的道德情境即貼近實際、真實、自然的情境,而不是“戲劇化”或“假想”的情境。因此,教育者在實施道德教育的過程中要重視道德情境的重要價值,寓情于景,以景育情,喚醒主體的道德情感。創設道德情境,必須把握它的基本屬性,避免將一些過度理想化的“榜樣”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可以從生活中常見且具體微小的一些生活場景入手,從涵養最基本的道德情感開始。“同情心的萎縮、義務感的匱乏與道德良知的遮蔽是造成德性發育不良和普遍性社會道德問題的直接原因”[13]。要想改變當前德育的面貌,必須重塑對他人處境和生命的關切。那么,道德情境的創設必須立足于現實的道德情境,把憐憫心及道德良知的培育作為重要的目標加以追求,把握道德情感的動態特征,通過教育過程的逐步深化和教育者的正向引導,激發學習者的道德情感,并鼓勵將這類情感積極表達出來。只有這樣,學習者才能實現由原本“旁觀者”與“局外人”向“當事人”身份的轉變,也只有這樣,學習者才能真正融入并參與到情境互動中,溝通與其他道德主體之間的情感聯系,達成道德情感的共鳴,并最終把“共情”投射到當前或者類似的道德情境中,做出符合社會期待且受個人主觀情感認同的道德行為。
(三)提供道德實踐的契機,實現道德品行的養成
荀子有云:“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我們強調道德情感的動態生成過程的同時,必須關注由道德情感向道德品行的轉換路徑。而最行之有效的就是道德實踐。現實的道德關系和問題,不是書本上、故事中那些至善至美的道德理想,諸多矛盾與沖突始終有待解決。而用脫離實踐的眼光和理想化的標準去看待道德實踐,無疑會面臨滿腔的熱情與現實不匹配的困惑與無奈。作為個人道德行為中表現出的穩定的、一貫的特點和傾向,道德品行必須依靠持續不斷的道德實踐加以塑造,在解決真實的道德沖突的過程中實現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脫離道德實踐侃侃而談個人的道德情感如何豐沛、道德境界如何之高,是不現實的。誠如我們之前論證道德情感的重要性、層次及培育方式,但歸根究底,道德品行的養成才是根本目的。道德情感的培育最終要為個體道德品行的養成服務,指向個體道德綜合素質的提升。因此,道德教育要始終立足于實踐,將實踐作為貫穿道德教育的重要環節。一方面,要特別關注道德實踐在德育各個階段中的滲透。德育的各個階段有不同的發展任務,任務的達成必須有相匹配的實踐環節以滿足道德發展的生成條件。因此,道德實踐的開展必須結合德育的階段性任務及道德情感發展的內在層次,在恰當的時機提供必要的道德實踐的機會以強化主體的道德行為。另一方面,要開發道德實踐的多樣化形式。“1+1=2”是再簡單不過的數學公式,而一個道德實踐的形式加上另一個道德實踐的形式卻能煥發出“1+1>2”的奪目光彩。形式多樣的道德實踐不僅能夠為主體帶來豐富的情感表達,更能提供更多踐行道德的場合和機會。因此,道德實踐活動應基于對現實生活中各種德育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重點發掘慈善公益活動、社區服務、志愿者活動等社會實踐活動的德育價值,讓個體在參與中實現由道德情感轉向對道德品行的執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