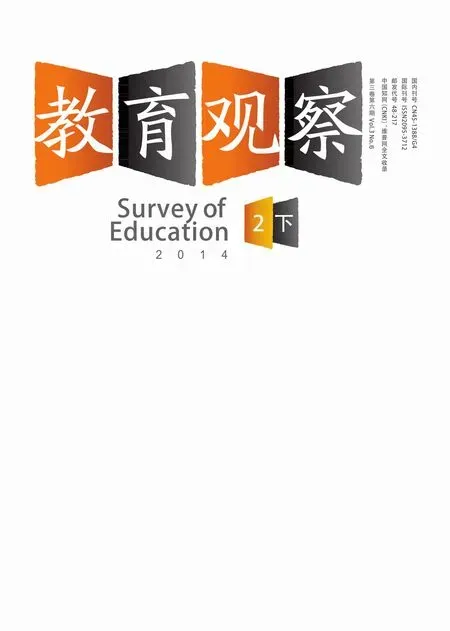當(dāng)代中國鄉(xiāng)村教育存在的困境
——關(guān)于《村落中的國家》
劉 蘋,馬靜淑
(1.德州市樂陵花園小學(xué),山東德州,253600;2.濰坊臨朐縣五井鎮(zhèn)五井小學(xué),山東濰坊,262603)
一、當(dāng)前中國鄉(xiāng)村教育的困境
(一)鄉(xiāng)村教育資源貧乏
教育資源是學(xué)生接受教育的基礎(chǔ)要素。當(dāng)前,我國鄉(xiāng)村教育在發(fā)展的道路上步履維艱,進(jìn)步緩慢,這與鄉(xiāng)村教育資源的匱乏不無關(guān)系。而現(xiàn)今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無論是硬件資源還是軟件資源都處于匱乏的境地。首先,教育經(jīng)費(fèi)不足是制約鄉(xiāng)村教育發(fā)展的主要因素。鄉(xiāng)村教育經(jīng)費(fèi)主要來源于國家和地方財政的支持。然而,自20世紀(jì)90年代起,我國開始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地方財政收入壓力增大,加之教材和教師工資上漲,許多鄉(xiāng)鎮(zhèn)都出現(xiàn)了拖欠教師工資的現(xiàn)象,教師教學(xué)積極性嚴(yán)重受挫。同時,教育經(jīng)費(fèi)不足還直接制約著教學(xué)設(shè)施的完善,狹小的校園,破爛的桌凳,稀有的學(xué)生活動場地,更不用說現(xiàn)代化的教育手段、網(wǎng)絡(luò)設(shè)施和其他教育活動設(shè)施,許多貧苦鄉(xiāng)村的孩子不得不在年久失修的危房里學(xué)習(xí)。其次,師資匱乏是鉗制鄉(xiāng)村教育發(fā)展的又一要素。盡管近年來國家為鼓勵大學(xué)生支持鄉(xiāng)村教育出臺了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如免費(fèi)師范生,研究生支教團(tuán)等),但這依然未能從根本上扭轉(zhuǎn)鄉(xiāng)村教師短缺的局面。
(二)鄉(xiāng)村教育質(zhì)量降低
鄉(xiāng)村教育資源的貧乏不僅限制了鄉(xiāng)村教育的發(fā)展速度,更是制約著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教育水平。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地理環(huán)境、生活條件、福利待遇相對較差,使之缺乏吸引力。外邊教師不愿意來,在編教師向外走,教師嚴(yán)重缺編。例如,在李書磊所著的《村落中的國家》一書中提到,豐寧希望小學(xué)共有11名公辦教師,這11名公辦教師中一類是從民辦教師轉(zhuǎn)正過來的,好多老師都要帶好幾個班的科目。還有些掛名教師,不教書,但領(lǐng)工資。同時,隨著城市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城鄉(xiāng)差距逐步擴(kuò)大,加之大學(xué)畢業(yè)生增多,就業(yè)難度加大,“知識改變命運(yùn)”的黃金法則不斷受到質(zhì)疑,許多鄉(xiāng)村青少年在完成義務(wù)教育后選擇去城市打工,鄉(xiāng)村教育出現(xiàn)了生源斷層。學(xué)生數(shù)量的減少也挫傷了教師的教學(xué)積極性,進(jìn)而演變成“學(xué)生不想學(xué),老師不愿教”的惡性循環(huán),嚴(yán)重削弱了鄉(xiāng)村教育的發(fā)展?jié)摿Α?/p>
(三)鄉(xiāng)村教育與鄉(xiāng)村社會的割裂
鄉(xiāng)村社會是鄉(xiāng)村教育的大背景,而當(dāng)前中國的鄉(xiāng)村教育卻從城市“空投”而來,脫離鄉(xiāng)土的氣息,鄉(xiāng)村學(xué)生正在接受著遠(yuǎn)離鄉(xiāng)村社會背景的教育。中國的鄉(xiāng)村教育從教學(xué)內(nèi)容的選擇、教學(xué)大綱和標(biāo)準(zhǔn)的制定、教材內(nèi)容的編選,到考試內(nèi)容的設(shè)定,都是以城市教育為依據(jù)的。鄉(xiāng)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使鄉(xiāng)村本土知識和鄉(xiāng)土文化逐漸萎縮,失去了生存空間,也淡出了鄉(xiāng)村學(xué)生們的視野。鄉(xiāng)村學(xué)生正遭遇著城市取向的教育設(shè)計,他們學(xué)習(xí)的都是與自身生活和親身經(jīng)歷極度割裂的陌生的體驗,他們每天面對著如霧里看花般的教材內(nèi)容,聽著虛幻縹緲的城市生活,不少時候還不得不面對教學(xué)材料里有意無意流露出的對農(nóng)村的鄙夷。這導(dǎo)致農(nóng)村孩子精神生活貧乏,精神之根缺失,對鄉(xiāng)村的認(rèn)同感明顯下降,村莊共同體逐漸解體的現(xiàn)象。鄉(xiāng)村教育在解構(gòu)鄉(xiāng)村價值體系和行為邏輯上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對鄉(xiāng)村教育困境的原因探究
中國鄉(xiāng)村教育是中國教育系統(tǒng)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制約著我國由人口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推進(jìn)的進(jìn)程。然而,當(dāng)今中國的鄉(xiāng)村教育存在著一系列困境,探究其原因,筆者認(rèn)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城市中心的課程價值取向未能培養(yǎng)起農(nóng)村學(xué)生對鄉(xiāng)村的認(rèn)同感
早在1926年,陶行知先生就尖銳地抨擊當(dāng)時中國的鄉(xiāng)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xiāng)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wù)農(nóng),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nóng)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qiáng)的變?nèi)酰醯淖兊酶裢馊酢薄=袢盏泥l(xiāng)村教育,這種情形依然存在。
我國的教育政策一貫奉行城市中心的課程價值取向。“教學(xué)內(nèi)容與教學(xué)模式的選擇,教學(xué)大綱和標(biāo)準(zhǔn)的制定,教材內(nèi)容的編選,考試內(nèi)容的設(shè)定,都是以城市學(xué)生為依據(jù),長期忽視農(nóng)村的教育環(huán)境、教育資源和學(xué)生的承受力。在實際教學(xué)過程中,課堂幾乎不給學(xué)生傳授他們能夠在農(nóng)村中有效發(fā)揮作用所需知識、技能和思想。”有學(xué)者更是進(jìn)一步指出,當(dāng)前學(xué)校課程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培養(yǎng)對工業(yè)、城市與現(xiàn)代生活的向往與羨慕,這種內(nèi)容面對鄉(xiāng)村小學(xué)及其學(xué)生時愈發(fā)顯得突出。城市在這里成了工業(yè)、現(xiàn)代化和幸福生活的象征。這種內(nèi)容也許是課本與課程的編訂者下意識設(shè)定的,但它們在鄉(xiāng)村學(xué)校中則會被接受為一種明確的意識。那些顯現(xiàn)與渲染高樓大廈、立交橋、大街、公園、超市與機(jī)場畫面及文字恰足以形成城市生活的強(qiáng)烈誘惑。語文課與社會課本中無意間出現(xiàn)的事物與形象,如動物、公共汽車、電話亭,在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眼中也都成為城市生活隱約但誘人的閃現(xiàn)”。余秀蘭還以教科書和高考試卷為對象,對教育內(nèi)容和評價標(biāo)準(zhǔn)的文化傾向進(jìn)行了比較分析。她認(rèn)為,目前的教科書總體上不利于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而高考試卷中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文化偏向也不利于農(nóng)村考生。考試內(nèi)容較多地反映城市生活,所反映的熱門話題或時代話題多是城市背景下的,有些內(nèi)容,農(nóng)村孩子非常陌生,甚至是從未聽說過的。
這樣一來,鄉(xiāng)村學(xué)校的課程實質(zhì)上成為了一種“他者的課程”,無視鄉(xiāng)村文化,漠視鄉(xiāng)村生活,使城鄉(xiāng)學(xué)生在競爭中處于極不平等的地位。鄉(xiāng)村學(xué)生想要得到主流的認(rèn)可,不得不付出比城市學(xué)生多得多的努力,而且就算他們有朝一日步入大學(xué)的殿堂,在將來就業(yè)時,還得面臨鄉(xiāng)村身份給他帶來的諸多尷尬。更糟糕的是,鄉(xiāng)村學(xué)生在這種城市中心價值取向的教育之下還要“承受著心靈上的巨大負(fù)荷,他們被迫放棄許多從小就接受的價值準(zhǔn)則,鄉(xiāng)村的‘自然野趣之習(xí)染’不斷地受到侵蝕,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內(nèi)心的煎熬,而這種煎熬伴隨著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日益明顯”。
鄉(xiāng)村學(xué)生在城市人的教材面前,找不到半點(diǎn)鄉(xiāng)村文化自豪感和親切感,找不到“根的感覺”,厭學(xué)、輟學(xué)成為他們反感、抵制城市中心主義課程的自然選擇。然而,這種反感與抵制卻并不是緣于他們的鄉(xiāng)村情結(jié),并且在結(jié)果上也沒有增進(jìn)他們的鄉(xiāng)村情結(jié),他們的整個學(xué)生生活都“與鄉(xiāng)村無涉”,無法從根本上形成對鄉(xiāng)村價值的認(rèn)同,這就在鄉(xiāng)村學(xué)生內(nèi)心深處埋下了“厭農(nóng)”“離農(nóng)”的種子。其結(jié)果就是,他們或外出務(wù)工或逗留鄉(xiāng)村本地,成為游手好閑的人,并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流民群體。外出務(wù)工者又分為兩類,一類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努力地賺錢,然后回家“修房造屋、生兒育女”,或者干脆就在城市買房,成為一個“鄉(xiāng)里人”羨慕的“城里人”,從而彌補(bǔ)丟失在學(xué)校里的“成龍、成鳳”之夢;另一類人則成為了城市的一種不穩(wěn)定因素。一項調(diào)查表明,城市外來務(wù)工人員中的犯罪率呈逐年遞增態(tài)勢,而且犯罪者受教育程度較低,并有呈低齡化趨勢,而這些犯罪青年正是城市中心主導(dǎo)下的鄉(xiāng)村教育的產(chǎn)物。
至于逗留鄉(xiāng)村的游手好閑者,既對鄉(xiāng)村和土地沒有好感,又不愿外出打工,“怕失身份”,這類人最令鄉(xiāng)村擔(dān)憂。他們不斷地消蝕鄉(xiāng)村,“敗壞著鄉(xiāng)村的風(fēng)氣”。可以想象,鄉(xiāng)村社會的主力除了“386199部隊”外,便是這些根本就不認(rèn)同鄉(xiāng)村社會的“局外人”。作為局內(nèi)人的“386199部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這些本土的“局外人”卻有力不往鄉(xiāng)村使,從而導(dǎo)致整個鄉(xiāng)村社會的灰心喪氣,形成一種集體性的社會氣餒。面對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城市文化的矛盾,無數(shù)充滿困惑與苦楚的鄉(xiāng)村兒童——未來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真正力量,正在將鄉(xiāng)村由一個文化概念變成一個純粹的地域概念,文化正從鄉(xiāng)村淡出。
(二)精英教育體系倚重于“向上看、往上流”的民眾意識,直接塑造了精英們對鄉(xiāng)村的離棄心理
傳統(tǒng)中國是一個城鄉(xiāng)雙向自由流動的社會,科舉制度和選拔制度為每一個人向上流動提供了機(jī)會和保障。在這種制度框架下,集中國文化之大成的鄉(xiāng)村可以說是充滿活力富有生氣的。一方面,鄉(xiāng)村的精英可以通過科舉進(jìn)入城市,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進(jìn)入城市的精英,也可以自由地回流至鄉(xiāng)村。這些精英群體回到鄉(xiāng)村后,“把主流社會的人文話語道德動向帶回并適用于鄉(xiāng)村,從而塑造了同城市同等鄉(xiāng)村人文道德”。所以,他們總能在歷代亂世之后的鄉(xiāng)村廢墟上,重建社會秩序,使鄉(xiāng)村生活再度文明。然而,近世以來,正所謂“水往低處流,人向高處走”,走出鄉(xiāng)村成為“村里的人的人生理想”,再回鄉(xiāng)村意味著“丟人”和“沒臉面”。尤其是高考制度吸收了鄉(xiāng)村精英,發(fā)達(dá)的工業(yè)文明和高薪也進(jìn)一步吸引著精英們向城市集中,城鄉(xiāng)差距日益擴(kuò)大,鄉(xiāng)村的吸引力幾乎喪失殆盡。
置身在這種制度框架和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鄉(xiāng)村自然而然地把“要脫農(nóng)皮”“不再捏泥巴”作為“一輩子的大事”,“考上了穿皮鞋,考不上穿草鞋”成為他們的警示語。所以,以高考制度為核心的精英教育正好滿足了這一民眾心理,不管我們對精英教育、對高考制度作什么樣的評價,都不會影響它在鄉(xiāng)村社會的地位。
高考成為農(nóng)村學(xué)子跳出農(nóng)門、改變命運(yùn)的主要通道,這本身是一件好事。可問題在于:一方面,高考制度所提供的通道完全是單向的,農(nóng)民學(xué)生升學(xué)之后,其戶籍既被本村注銷,即使有心,也無從返回鄉(xiāng)村。從情感和意識上說,正如上文所言,無根的鄉(xiāng)村教育已經(jīng)使從鄉(xiāng)村出來的大學(xué)生與鄉(xiāng)村喪失了情感與道德上的任何聯(lián)系,缺乏一種關(guān)心社會文明秩序的基本情懷,因此,這些學(xué)生即便再回鄉(xiāng)村,也只是看看而已,或是作無謂的喟嘆,幾無反哺鄉(xiāng)村的意識和行為。另一方面,精英教育讓學(xué)習(xí)努力的農(nóng)村孩子有機(jī)會“跳出農(nóng)門”走向上層社會,這給城市建設(shè)增添了人才,對農(nóng)村建設(shè)來說卻是釜底抽薪。精英外流已成為鄉(xiāng)村文明式微的主要原因。
(3)鄉(xiāng)土課程的不得力與鄉(xiāng)村德育的無效,使鄉(xiāng)村學(xué)生進(jìn)一步喪失文化根基,成為“精神游民”
我們曾長期實行大一統(tǒng)的課程政策,并且課程設(shè)置大部分以城市生活為導(dǎo)向,是為培養(yǎng)城市人做準(zhǔn)備的。“盡管城市生活在近代工業(yè)文明的沖擊下,確實具有許多鄉(xiāng)村無法比擬的便利性,但也不能忽視城市之外廣闊的鄉(xiāng)村,不能忽視已存在于鄉(xiāng)村文化中的大量豐富的優(yōu)秀的教育資源。鄉(xiāng)村中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傳統(tǒng),以及鄉(xiāng)村生活現(xiàn)實中原本就存在著許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著對于鄉(xiāng)村生活以及鄉(xiāng)村生活秩序建構(gòu)彌足珍貴的價值成分”,而它們卻難以進(jìn)入正規(guī)的課程體系。
2001年,教育部《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頒布實施后,打破了全國上下一本教材的局面,實行國家、地方和學(xué)校三級課程管理。但是,受高考、中考制度的影響,地方課程實際上成為了國家課程的一種翻版,是一種縮小了的國家課程。
另一方面,最能體現(xiàn)鄉(xiāng)村生活實際的校本課程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也根本無法普遍實施,它還僅僅是一種點(diǎn)綴,并且還只存在于個別“掙錢有門道”的學(xué)校,如省、市示范校。普通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或缺乏課程開發(fā)的正確理念和能力,或缺乏必要的條件,當(dāng)然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兩者都缺乏,從而使校本課程成為空談,豐厚的鄉(xiāng)村文化再次與課程無緣,與教育無緣。
總之,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的不得力使鄉(xiāng)村學(xué)校再一次失去了表達(dá)自我的機(jī)會。一方面,以省為單位的地方課程不僅沒能成為地方教育價值追求的代言人,而且從實際上看也無法顧及到各種各樣的鄉(xiāng)村實情。所以,對鄉(xiāng)村學(xué)校而言,地方課程與過去的國家課程并無多少差別,反正“照章執(zhí)行就是了”。另一方面,最有可能表達(dá)鄉(xiāng)村自我的校本課程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撐體系,在絕大部分鄉(xiāng)村學(xué)校成為泡影。他們的校本課程只是課程表上的一個符號而已,“不是讓給語文數(shù)學(xué)就是學(xué)生自習(xí)”,仍然關(guān)照不了鄉(xiāng)村生活。
三、鄉(xiāng)村教育走出困境的思考
我國的鄉(xiāng)村教育確實面臨諸多問題與困境,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rèn)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jìn)行:
(一)加大鄉(xiāng)村教育投入
鄉(xiāng)村學(xué)生教育舉步維艱,教育投入不足是瓶頸。教育資源是鄉(xiāng)村教育發(fā)展的基礎(chǔ),是學(xué)生賴以學(xué)習(xí)的前提。使鄉(xiāng)村學(xué)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唯有加大教育投入,以保障教育資源。當(dāng)前鄉(xiāng)村義務(wù)教育經(jīng)費(fèi)全部納入公共財政的保障范圍,實行了“兩免一補(bǔ)政策”,公用經(jīng)費(fèi)和教師工資都基本得到保障,但鄉(xiāng)村自然條件艱苦,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資源匱乏的現(xiàn)狀在鄉(xiāng)村學(xué)校,尤其是偏遠(yuǎn)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依然很普遍。因此,加大財政投入份額和統(tǒng)籌力度,是當(dāng)前改變偏遠(yuǎn)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育資源匱乏的首要之舉。第一,要在每年財政預(yù)算中對鄉(xiāng)村教育經(jīng)費(fèi)投入進(jìn)行單列,確保經(jīng)費(fèi)來源;同時擴(kuò)大投資渠道,吸收多方面資金投入。第二,建立規(guī)范的責(zé)任分明的鄉(xiāng)村教育經(jīng)費(fèi)保障機(jī)制,并將鄉(xiāng)村與城市的教育投入進(jìn)行分開統(tǒng)計,并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jiān)督。分開統(tǒng)計的目的是保證鄉(xiāng)村學(xué)校教育投入的數(shù)額和流向,針對特別貧困和偏遠(yuǎn)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要設(shè)立專項經(jīng)費(fèi),專款專用,保證學(xué)校正常運(yùn)行,使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教育不受影響。第三,對于貧困和偏遠(yuǎn)的鄉(xiāng)村教師實行高于其他地區(qū)的特殊津貼制度并由中央或省級財政直接負(fù)擔(dān),以吸引和留住教師。教師質(zhì)量決定教學(xué)質(zhì)量,教師水平?jīng)Q定教育水平。吸引教師和穩(wěn)定教師隊伍是保證貧困和偏遠(yuǎn)鄉(xiāng)村學(xué)生正常接受教育的前提。在市場經(jīng)濟(jì)充分發(fā)展的今天,鼓勵大學(xué)生或教師到鄉(xiāng)村教書育人,不能僅靠思想教育和輿論宣傳,而應(yīng)出臺實實在在的激勵政策和保障機(jī)制,否則“到鄉(xiāng)村去”僅是一句口號。從經(jīng)濟(jì)待遇上來提高鄉(xiāng)村教師崗位吸引力,來保障鄉(xiāng)村教育的師資力量。另外,免費(fèi)師范生可適當(dāng)擴(kuò)大到省級師范院校,為鄉(xiāng)村教育培養(yǎng)“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優(yōu)秀師資。因為鄉(xiāng)村教師的品質(zhì),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地影響甚至決定鄉(xiāng)村孩子發(fā)展的品質(zhì)。相對穩(wěn)定的、高素質(zhì)的、富于愛心的師資,是發(fā)展鄉(xiāng)村教育、提升鄉(xiāng)村文化,甚至實現(xiàn)整個鄉(xiāng)村社會健康發(fā)展的重要保障。
(二)構(gòu)建鄉(xiāng)村學(xué)生所需的教育模式
“人類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動物,一個重要的標(biāo)志是人類有自己的文化,而人之所以成為人,也正是因為他是生活在一定文化系統(tǒng)中,是有文化的人。”鄉(xiāng)村孩子生長在鄉(xiāng)村文化中,對他們的教育不能脫離鄉(xiāng)村特有的文化,要和鄉(xiāng)村社會聯(lián)系起來。辦鄉(xiāng)村孩子所需要的教育,構(gòu)建鄉(xiāng)村學(xué)生所需的教育模式。這并不意味著使鄉(xiāng)村孩子局限于鄉(xiāng)村,而是站在鄉(xiāng)村世界里,用平視的姿態(tài),把鄉(xiāng)村孩子的教育納入我們的教育“視界”和“我們的世界”,來關(guān)注、傾聽、理解鄉(xiāng)村孩子的教育處境和教育需求,意在面向鄉(xiāng)村生活現(xiàn)實,真實表達(dá)鄉(xiāng)村孩子的教育期望和理想。教育應(yīng)給予鄉(xiāng)村孩子更廣闊的生活世界,在他們的生活境遇中生活方式的改善和幸福的實現(xiàn),使他們可享有進(jìn)入高一級教育的機(jī)會,使那些沒有此機(jī)會的孩子在他們的人生中享受一段對他們而言良好的教育。教育應(yīng)能使鄉(xiāng)村學(xué)生澄明前景,能使他們具備改造和建設(shè)鄉(xiāng)村的能力,能使他們飽受鄉(xiāng)土的滋養(yǎng)。而當(dāng)前鄉(xiāng)村社會真空的教育模式?jīng)]有給他們帶來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卻增加了他們對鄉(xiāng)村的冷漠、疏遠(yuǎn),使他們總想從“他們的世界中走出來”,既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又無法從事繁重的農(nóng)活,使他們處于尷尬的境地。因此,應(yīng)在現(xiàn)代社會的大背景下,立足鄉(xiāng)村社會,在為鄉(xiāng)村孩子提供現(xiàn)代性價值中必不可少的發(fā)展機(jī)會的同時,給他們提供鄉(xiāng)村社會的精神滋養(yǎng),促進(jìn)其對鄉(xiāng)村文明與鄉(xiāng)土價值的內(nèi)在理解,增進(jìn)他們對鄉(xiāng)土認(rèn)同,厚實他們的鄉(xiāng)土精神底氣,提升他們的文化自信,使他們獲得一種與現(xiàn)代化接軌過程中又不失鄉(xiāng)土精神資源的鄉(xiāng)村生活方式重新建構(gòu)的可能性。為此,第一,要根據(jù)鄉(xiāng)村現(xiàn)實和學(xué)生需求構(gòu)建鄉(xiāng)村教育,營構(gòu)鄉(xiāng)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間,保障鄉(xiāng)村孩子發(fā)展和多種選擇。第二,要培育扎根鄉(xiāng)村,并愿為鄉(xiāng)村教育服務(wù),能夠肩負(fù)起鄉(xiāng)村教育特殊使命的優(yōu)秀師資,即能夠理解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境遇,又有遠(yuǎn)見、能開啟鄉(xiāng)村學(xué)生的知識視界,能夠吸收鄉(xiāng)村社會的教育資源,引導(dǎo)鄉(xiāng)村學(xué)生理解周遭的鄉(xiāng)村世界,引領(lǐng)他們的鄉(xiāng)村情感并進(jìn)行全面孕育,使之不僅生活在對未來走出農(nóng)門的想象之中,而且盡可能生活在當(dāng)下,并親近當(dāng)下的生活世界。第三,
要在現(xiàn)行的教育內(nèi)容中適當(dāng)添加體現(xiàn)鄉(xiāng)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新內(nèi)容。
(三)加強(qiáng)鄉(xiāng)情教育,培育鄉(xiāng)村自信
由于城市中心的課程價值取向及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的不得建立,導(dǎo)致了鄉(xiāng)村文化在課程內(nèi)容中的缺席,以及教育目標(biāo)對鄉(xiāng)村的背離。加上精英教育體系倚重于“向上看、往上流”的民眾意識,直接塑造了精英們對鄉(xiāng)村的主動逃離和整個鄉(xiāng)村的社會氣餒,進(jìn)而導(dǎo)致了鄉(xiāng)村文明的式微。在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侵蝕下,消費(fèi)主義無限制地擴(kuò)張,也正在使越來越多的沒能產(chǎn)生鄉(xiāng)村價值認(rèn)同的學(xué)生、村民乃至整個村莊成為一個純粹的物質(zhì)軀殼。然而,教育的功能是雙向的,既可以生產(chǎn)社會排斥,也可以增進(jìn)社會團(tuán)結(jié),關(guān)鍵看我們施以怎樣的教育。對此,美國社會學(xué)家華德在他的《動態(tài)社會學(xué)》一書中就曾指出“教育是促進(jìn)社會進(jìn)步的切近方法”。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也認(rèn)為教育改革可以促成社會改革。功能主義學(xué)派也主張社會之所以能夠保持穩(wěn)定發(fā)展,主要是因為成員之間有著共同的信念、態(tài)度和統(tǒng)一的價值觀。因此,因教育而起的社會排斥,也可以教育化解之,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教育改革,促使社會成員對不斷變化的社會在思想、態(tài)度方面能夠保持和諧一致,以達(dá)到促使鄉(xiāng)村社會團(tuán)結(jié)的目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團(tuán)結(jié)不僅來自鄉(xiāng)村自身,而且來自鄉(xiāng)村對外流精英的感情。
[1] 李書磊.村落中的“國家”——文化變遷中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