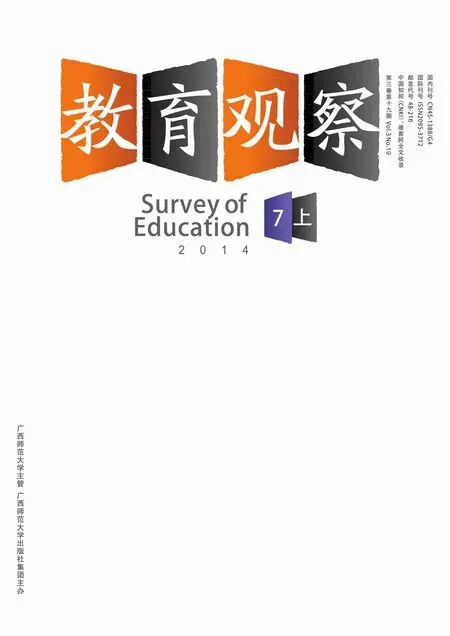芻議我國大學科技創新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應然功能與實然困境
溫正胞
(杭州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浙江杭州,311121)
一、大學的科技創新
科技創新的重要地位,從來沒能像在知識經濟時代一樣受到推崇與重視。在知識被視為最重要資源的時代,科技創新的重鎮——大學,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社會經濟發展與創造物質財富的動力站。人們對大學的看法,在科技創新對經濟和產業發展奇跡般的貢獻的影響下,經歷了從“象牙塔”到經濟發展“動力站”的轉變,大學的科技創新直接服務于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功能的出現,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大學的第二次學術革命。“斯坦福(大學)和硅谷被看作是這一伙伴關系的典范,是大學與工業、企業之間互相需求的產物,它為大學高新技術成果迅速商品化、產業化提供了適合的環境。”[1]大學如何通過其所擅長的科技創新來實現對經濟發展的引領與推動,成為這個時代最熱門也是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事實上,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知識創新,尤其是大學科技創新在促進和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各國都加大了激勵大學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力度。比如,像硅谷這類大學科技創新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成功案例引發的效應,使得美國在進入21世紀以后,接連發表了以《美國競爭力計劃》《國家創新教育法》和《領導力的檢驗:美國高等教育未來指向》等為代表的十多份研究報告,這些報告要求國家加大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教育與研發投入,助推科技創新成果對美國經濟競爭力的促進作用,提出了以高等教育科技創新服務經濟競爭力提升來保持美國領先世界的戰略目標。同樣,我國政府對高校發揮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優勢更好地引領與促進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予以高度重視,期望也非常高。2002年,科技部、教育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充分發揮高校科技創新作用的若干意見》,2006年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中更明確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使科技發展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支撐,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我們國家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的科技發展目標。在國家的“十二五”發展規劃當中,更是把提升高等教育機構的科技創新能力,實現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提高國家經濟的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列為重大任務。
二、大學科技創新與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之間的現實困境
可以說,知識經濟社會的最重要特征與內涵之一就是以大學為主體的科技創新成為社會競爭力,尤其是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源泉。對這一事實的認識,對于處在世界知識體系的底部的發展中國家及其高等教育體系來說,意義尤為重大。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世界第二,高等教育規模世界第一,但是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弱點,那就是粗放型發展,技術含量不高,只是純粹的數量優勢。而發達國家的經驗則證明了高等教育發展與產業升級之間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提升產業的競爭力。“美國高等教育與產業之間的良好關系的關鍵在于形成了科技研究創新活動與商業活動的密切接觸,從歷史的傳統來看,美國的大學一直以來以其卓越的科技創新能力回報經濟發展對大學的支持。”[2]
從理想的角度,我國現在的高等教育體系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跨越式發展之后,已經具備了比較可觀的科技創新能力。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這個宏偉目標的推動下,國家對科學研究與科技創新的資助與投入比例大幅增加。北大、清華、浙大等一批“985”高校以及一大批“211”高校在很多領域的研究已經達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在科研成果方面的技術創新數量非常可觀。在論文與專利數量等指標上,我國大學的科技創新水平與能力并不是一無是處。關于這一點,各級政府部門與高校自身發布的各類科研成果論證、鑒定及獲獎的數量就是很好的佐證。
但是,數量可觀的大學的科技創新成果并不會帶來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必然結果。與許多美好的愿望一樣,認識到某件事情的美妙與重要同在真實的環境中實現這件事的美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應然的烏托邦往往很美麗,實然的塵世卻往往困苦不斷。國家對大學的巨資投入與特殊制度安排使大學有條件創造出數量可觀的科技創新成果,但這些成果并沒有轉化生升力,也沒有創造出如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的大學科技創新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美好現實。我國大學科技創新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論與政策文本層面,距離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大學科技創新與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之間形成良性循環還有很大的差距。
三、導致大學科技創新在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方面存在困境的原因與突破
就我國目前的高校科技創新與經濟和產業發展來看,在大學文化與科技創新評價機制以及大學所擁有的知識產權與發明專利轉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限制大學科技創新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理想功能實現的障礙。
就大學文化而言,我國大學的科技創新活動一直以來未能形成走出“象牙塔”的文化。許多大學的科技創新活動習慣于停留在“象牙塔”及其主管部門間的申報與論證、鑒定、頒獎的層面。大學研究機構的科技創新研究成果在形成結論之后,往往以論文與研究報告為終結,以獲得主管部門的鑒定與頒獎為終結。這樣造成的結果是一大批科技創新成果躺在大學的研究機構中。與此同時,我國的產業發展缺少技術推動,產業結構一直以來未能實現從勞動密集型向科技知識密集型升級。可以說,行政化色彩明顯的大學存在方式直接決定大學科技創新成果的評價方式。在大學大部分資源都依賴于行政手段計劃分配的體制背景下,大學的科技創新活動必然不會自主去尋找市場需求,其市場價值也必然不被重視,因為行政化的科研課題申請與科技成果獲獎可以帶來更多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哪怕非常需要科技創新成果來實現產業升級,也可能會有個別企業通過與大學科研機構的良好合作關系獲得了成功,但在國家與社會層面,大學科技創新與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之間的聯系必然是缺位的。
同時,我國目前還缺乏保證或推動大學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有效政策與法律條件。大學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產業生產力需要相應的制度設計來保證轉化過程的高效與合理。但目前我國對高校科研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歸屬與轉讓等規定缺乏明確與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對于接受國家財政撥款的科研項目資助開展的科學研究成果的知識產權的認定模糊,對其轉讓與獲益的分配等重要政策與法律的制定更是處在起步階段。許多大學科技創新成果的研究者、發明者、開發者在當前的規定當中看不到有效的激勵,自然不會致力推動研究成果在實際生產中的轉化。通過制定適當的法律,改革現有的大學科技創新轉化的制度,從合法性與合理性上來保障大學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促進經濟與產業發展的助推器,不僅需要充分強化以重點大學為龍頭、以眾多地方高校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的引領意識,更需要政府及高校主管部門改變對大學科技創新成果的評價方式,強調科技創新成果的實際應用效果,并且為這種應用提供有效的激勵和合法性保障。
“科學技術只有被應用到生產中,才能推動經濟發展。高校向企業轉讓科技成果,為其提供技術咨詢和指導,與企業合作建立高新技術園區。美國高等教育創新體系成功地扮演了這一角色,加快了科學技術的傳播速度、更新速度及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3]高等教育規模躍居世界第一、經濟規模世界第二的現實條件,以及知識經濟對科技創新的依賴與強調,已經足以讓人們對我國大學科技創新在引領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方面產生美好的聯想。從政府到高校、企業,從科技創新成果的研究者到企業家,都已經認識到了大學科技創新與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之間必須要建立起良好的轉化機制。而要想破解我國大學科技創新與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之間的兩張皮現象,首先需要解決大學科技創新主體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科技產品的積極性不高的問題。我國大學中科技創新工作者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科研能力上,都有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基礎,但是與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系統中擁有良好的學術創業傳統的同行相比,他們還存在集體無意識。從這個角度上看,我國大學科技創新工作者的創業意識,以及在積極進行學術與市場對話的能力方面亟待提高。其次,要從合法性上解決大學科技創新轉讓的知識產權等相關法律制度問題,健全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機制。在保證科研成果數量與水平的同時,需要考慮如何激活這些數量與規模可觀的科技創新成果的市場價值,以一種科學的制度設計實現其真正的功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政府需要解開大學行政化的桎梏,在大學自主進行科技創新與促進經濟和產業發展之間架起溝通與對話的橋梁,實現學術與市場的有效對話,將市場話語體系與學術話語體系進行有機制融合,需要在大學中營造一種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科技創新與學術創業文化。
[1] 胡欽曉.美國研究型大學與國家核心競爭力提升[J].南通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6(6):14-18.
[2] Partick J,Kelly Briant T,Prescott.Amerca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s ability to compete global economy[J].Change,2007(3/4):33-37.
[3] 許桂清,黃銳.戰后美國高等教育創新體系的形成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J].外國教育研究,2004(5):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