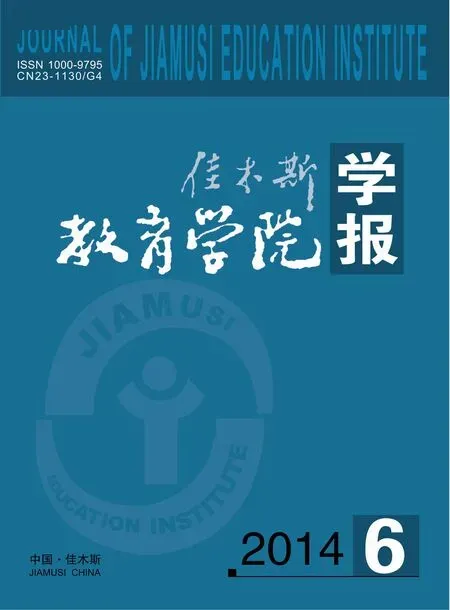從本我、自我的角度看《廚房》中惠理子的人物形象
蔣亞男 浦 麗
(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江蘇南京 210095)
從本我、自我的角度看《廚房》中惠理子的人物形象
蔣亞男 浦 麗
(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江蘇南京 210095)
弗洛伊德將人格結構分成三個層次:“自我”、“本我”和“超我”,從“本我”和“自我”的矛盾與斗爭來分析吉本芭娜娜的成名作《廚房》一書中的惠理子這一形象,來分析她的人生中重要的三個轉折點以及所產生的人物形象。而“本我”和“自我”這兩者的斗爭與沖突,從始至終都是本我戰勝了自我。
惠理子;自我;本我;人物形象
吉本芭娜娜是日本當代著名女作家。可以說,她目前與村上春樹一同領跑日本當代文學,在國外也與村上齊名。吉本芭娜娜于1987年11月在《海燕》雜志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廚房》,博得廣泛好評,獲得第六屆海燕新人文學獎。從此,她如同一顆璀璨的新星出現在日本文壇。1988年1月發行的單行本《廚房》(收錄《廚房》、其續篇《滿月》和處女作《月影》)銷售量達到130萬冊,在日本掀起空前的“芭娜娜熱”。
《廚房》的情節十分簡單,講述的是失去摯愛親人主人公櫻井美影,是怎樣慢慢走出孤獨,最終決定遺忘過去的悲傷勇敢生活下去的故事。而在她走出孤獨的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位是溫和善良的青年田邊雄一,另一位就是田邊的母親,田邊惠理子。
田邊惠理子是吉本芭娜娜小說《廚房》中萌動性別解構意識、大膽地向傳統意識形態挑戰、把自己從男性變為女性的一位勇者。惠理子本是雄一的父親,原名雄司, 英年喪妻后,覺得自己“再也不可能愛上任何人了”,于是做了變性手術, 并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惠理子”。雖然惠理子看似是配角,但是她在文章中卻是有著很重要的意義,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津田洋行把惠理子看做是“最重要的人物”,“即使在風格特異的三個人當中也是尤為特殊的存在,是不可思議的人。”因此,本文將著重從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的角度來分析惠理子這一角色的形象。
在惠理子還是雄司的時候,從小就被雄一的親生母親家里收養,雄一的親生母親與雄司一直在一起長大。雄司還是男孩子的時候,他也是很帥,很討女孩子喜歡。可是不知道怎么會喜歡上這副長相的我媽。雄一是這樣講述雄司與自己親生母親的過去的。雄司要娶自己名義上的姐妹為妻,本我的意志是“非她不娶”,雖然沒有實際的血緣關系,但這肯定是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但是雄司卻“結果竟然不顧父母的養育之恩,一起私奔了呢。”因而在本我和自我的斗爭中,本我戰勝了自我。
私奔是惠理子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折點,第二個轉折點就是雄司的老婆,也就是雄一的親生母親去世,失去“那個與他最相知相愛的人”顯然對惠理子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不光是心如死灰——“再也不可能愛上任何人了”的絕望,還讓他對自己的人生軌跡產生了懷疑,在妻子的病到了晚期的時候,雄司“第一次萌發了不做男人的念頭” ,“之后沒多久,妻子就死了,菠蘿也枯了。我不懂得照料,澆水澆得太多了。我把菠蘿扔到了院子角落里。雖然嘴上說不清楚,可我心里卻真正明白了一件事。說起來也很簡單,世界并不是因為我而存在的。”雄司似乎是大徹大悟了,回想我們看到的別的文學作品中大徹大悟的人一般都會是選擇遁入空門,斬斷紅塵,從此不問世事,但是雄司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選擇了對立面,對自己進行徹底的改造——變性并且從事了風俗業。是為了這也與我們常說的“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林”是一個道理。對于惠理子變性的動機,正如周閱在《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一書中所說的一樣“雄司選擇變性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表明對亡妻的深愛, 這是男性對女性的殉道式的愛情表達。”雄司希望自己和死去的妻子合二為一,把將自己也變成女人作為是對妻子的懷念、對妻子的愛。
事實上,在小說問世的1987年,日本還未有公開施行的變性手術,最早的變性手術是在1998年施行的,而這時距離小說發表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的時間,因此變性人惠理子完全是作者的想象,這也難怪津田洋行會給惠理子貼上“科幻”的標簽。可見當時的人們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接受變性行為這樣一個新奇而且不太符合社會主流的行為,最開始肯定是會有很多反對的聲音,有很多的不理解,本我想要變性,不去理會世俗的眼光,但是自我要求他不要這樣做,這里又出現了本我和自我的斗爭,最終雄司沒有懼怕自我、懼怕社會道德的約束,他順從了本我的意志,做了變性手術,做了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從這第二個轉折點看,本我又一次打敗了自我。
惠理子的人生的第三次轉折點就是她被一個精神失常的男子盯上后殺害了,也就是惠理子生命的終結。時間的流逝,惠理子已經不僅只是外表上是一個女人的形象了,她的內心、行為等都開始逐漸轉變成一個真正的女人,如同她給雄一留下的遺言中說的一樣“我想,至少這封信要用男性用語來寫,也很努力地嘗試了,可還是覺得怪怪的。覺得不好意思,羞于下筆。當了這么長時間女人,本來還一直以為在身體的某處還有那個男性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存在著,女人皮相只是我的任務。現在看來,身心都變成女人了,是名副其實的母親啊。好笑。”
無論是從內心到形態還是從形態到內心,惠理子在文中最后出現的形象都已經完完全全是女性了,但是她卻并沒有被這個社會所包容。比如那個精神失常殺死她的男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那人自從在街上偶遇惠理子,便對她一見傾心,于是尾隨著她,發現她是在一家同性戀酒吧里工作。接著他寫了一封長信,說那么美麗的一個人竟是個男人,這使他深受刺激。”很明顯這個精神失常的男子就是因為不能接受變性人而殺死了變性人惠理子,可以把他看做是當時社會上人們的縮影,他相當于是代表了當時的社會懲罰惠理子這樣一個離經叛道的人。但是惠理子也沒有示弱,她接受自己的形象也接受自己的內心,她絲毫不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有絲毫的羞恥,所以沖突的焦點就是男子認為惠理子的形象、外表是個謊言,是騙人的,而惠理子則認為這就是我,我的內心和我的外表是一致的,我的形象、外表沒有任何的問題。所以在受到所謂的“社會的懲罰”時,她奮起反抗,“流著血,雙手抓起吧臺上裝飾用的鐵啞鈴,砸死了兇手。”她要為自己,為本我做斗爭。而且惠理子到死還是以一個女性形象去世的,是她自己內心所期望的樣子,而且還可以說是在最美的時候,在最風華絕代的時候去世,不得不說這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宣戰。因此,從這里看,惠理子的死又是一次本我對自我的勝利。
惠理子的一生中的本我和自我的斗爭總是以本我的獲勝為結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就是說惠理子的一生總是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也就是雄一評價惠理子的一句話“那個人總是隨心所欲地過日子。不過,有能力實現,也很不簡單呢。”
[1]津田洋行.吉本芭娜娜《廚房》之我論[J].文藝理論研究會,1999(3).
[2]周閱.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3]吉本芭娜娜.廚房[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The characters of Eri Ko in "kitc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 and ego
Jiang Ya-nan, Pu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Freud divided personality structure into three levels: "ego", "ID" and "superego", from the contradiction and struggle of "ego" and "ID" to analyze Banana Yoshimoto's masterpiece "kitchen" a Book of Eri Ko this image, to analyze the thre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in her life and the figures. "Ego" and "ID" of the two conflicts, ID win the ego.
Eri Ko; ID; ego; characters
I206
A
1000-9795(2014)06-0118-01
[責任編輯:董 維]
2014-03-07
蔣亞男(1989-),女,江蘇徐州人,從事日漢語言比較方向的研究。
浦 麗(1981-),女,江蘇常熟人,講師,從事漢日語言比較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