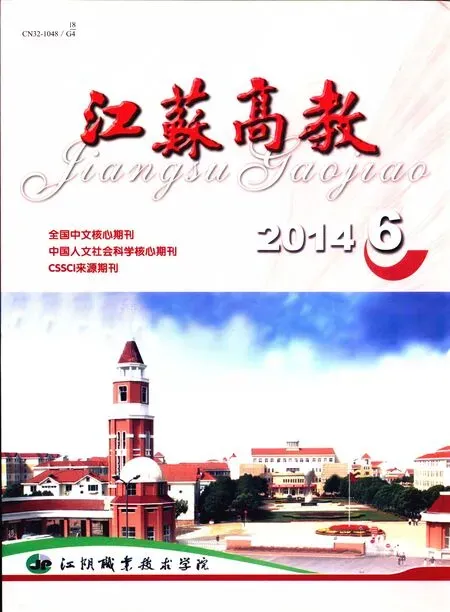高校決策執行偏差的制度分析
肖京林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武漢430074)
高校決策執行偏差的制度分析
肖京林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武漢430074)
高校決策執行是將決策理念付諸實施的重要環節,是實現決策目標的必經之路,對高校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決策執行是一個非線性的過程,在執行中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導致決策執行發生偏差。文章以新制度主義為研究視角,以制度的三種組成要素: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文化—認知性要素為分析框架,揭示高校決策執行者受到工具性邏輯、適當性邏輯和正統性邏輯的影響,從而影響決策的執行方式以及效果,導致執行偏差的產生。
高等學校;決策執行;執行偏差;新制度主義
管理學家西蒙認為:“管理就是決策。”可見在任何組織中,決策都占據著組織管理的中心地位,高校也不例外。作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高等學校,決策關系到學校的人才培養質量、科學研究的發展以及社會服務的水平等學校發展事務。決策的重要地位,決定了決策應當是作為高等學校管理的重要研究議題。決策包括決策制定、決策執行與決策評估三個階段。從當前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高校決策制定,關于決策執行與評估的研究較少。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決策研究在我國高等學校管理研究中還處于起步階段。劉獻君教授認為高校決策是最重要但也是極易被研究者忽略的問題。他用“慣性論”、“后效論”、“黑箱論”解釋了研究者較少研究決策問題的原因[1]。第二,線性思維的決定論。認為決策制定與執行是一種線性的關系,即只要決策制定出來,執行活動就會自動發生;只要決策水平高、決策質量好,執行活動也必然會有效地實施。第三,決策執行的復雜性。決策執行是一項復雜的工程,涉及高校的職能部門、院系、教職工、學生等。決策執行研究屬于動態過程研究,相對于決策制定研究來講,執行研究具有復雜性,從而增加了研究的難度。決策執行是實現決策目標的必經之路,沒有執行,決策也只能是一紙空文。然而,高校決策在執行過程中總是會出現偏離決策目標的現象,影響決策執行力,導致決策目標難以實現。本文就高校決策執行中所發生的偏差問題進行分析,以新制度主義為理論框架,旨在解釋決策執行偏差產生的原因。
一、高等學校決策執行以及執行偏差
(一)高等學校決策執行
“決策”,即做出決定或選擇;“執行”,即貫徹實施的活動。決策執行,即貫徹實施決策者所做出的決定或選擇,是將決策理念付諸實踐的一系列活動。高等學校決策執行是指,在高等學校內部,決策執行者依據決策的指示、要求,為實現決策目標、取得預期效果,決策執行者調動人力,利用資源、技術,不斷采取積極措施的動態過程。高校決策執行包括:決策執行者、決策執行資源、決策執行程序、決策執行目標群體和決策執行環境等。從高校決策活動來看,決策執行是高校決策中的重要一環,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首先,高校決策執行是將決策理性轉變為實踐現實性的過程;將靜態的決策文本、思想理念轉變為動態的行為活動的過程。高校決策執行是實現決策目標、解決組織問題的途徑,實現組織中教育資源的權威性分配。美國政策學家艾利森認為:“在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決于有效的執行。”[2]其次,高校決策執行是檢驗決策是否科學、合理的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項決策是否科學、合理,通過決策執行可以得到檢驗。第三,高校決策執行為決策制定者提供反饋。在執行過程中,一些決策制定者未曾預料的問題會凸現出來,決策執行者及時把問題反饋給決策制定者。決策制定者根據執行情況進行及時調整、解決問題,確保決策的有效執行。第四,決策執行是決策評估的重要依據。決策執行的結果為決策評估提供了依據,評估者根據決策目標實現程度、目標群體滿意度、執行成本、執行效率等因素進行評估。
(二)高校決策執行偏差
高校決策執行偏差指的是,在高校中,決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有意的或無意的偏離決策目標的現象。高校決策執行偏差有積極的偏差與消極的偏差兩種形式。積極的偏差指決策執行者在執行過程中盡管偏離既定的目標,但是其執行活動對高校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來看,可謂是更好地實現了決策目標;消極的偏差指決策執行者在執行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消解著決策目標,使得執行活動變異,不但沒有實現決策目標,甚至使得學校發展、改革受阻。在高校中,決策制定者經常為決策執行中出現的消極偏差苦惱不已。決策制定者為制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殫精竭慮,可是一到付諸實施時卻不盡如人意,總會出現一些“無預料的后果”。如,高校出臺了一系列教學改革決策,可是到院系實施層面卻發現存在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現象。在本文中,主要探討的是消極的執行偏差。
(三)高校決策執行偏差的類型
高校決策執行中的偏差表現形式多樣,有的是“敷衍搪塞”,有的是執行的“形式化”,有的甚至是公開對抗等。在對高校決策執行中出現的種種偏差進行概括總結,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第一,儀式性執行。儀式性執行指的是高校決策執行者表面上大力宣傳決策思想理念,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決策執行方案,但是并沒有將決策落到實處,造成決策執行的表面化。儀式性執行造成學校資源的浪費,如為了表面上執行政策,執行者往往要花大力氣進行宣傳,營造“面子工程”,花大力氣在文字材料的寫作與整理上,往往造成執行過程中比排場、比材料,造成“文牘主義”、“務虛風氣”等不良現象。
第二,選擇性執行。選擇性執行就是指在執行過程中,執行者根據自身利益或者具體情況,有選擇地對決策進行執行。此類執行的特征是自利性,執行者在執行過程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決策部分進行實施,對有損于自身利益卻有利于學校整體發展的決策部分不予以執行。如,對部分決策內容進行消解或曲解,從而破壞學校決策執行的整體性,降低決策的整體執行質量。
第三,替代式執行。替代式執行即執行者以自己的“土決策”代替學校決策,制定與學校決策不相符的計劃、策略等。通常此類“土決策”表面看與學校主決策無二致,但實際上卻被執行者改得面目全非,造成“陽奉陰違”的現象。
第四,機械式執行。機械式執行指執行者在執行過程中不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計劃、策略,完全按照學校的決策來執行。此類執行的特征是機械性,不具有靈活性。學校決策往往難以顧及所有執行者的特征與發展實際,決策內容具有原則性,只是規定執行的方向與目的。這就要求執行者在執行過程中要發揮自由裁量權,制定符合自身發展的,又有利于決策整體實施的具體執行策略。
第五,對抗式執行。對抗式執行指執行者不認同學校制定的決策,認為決策有悖于自身的價值觀、行為準則等,或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要求機構、群體或個人行為的轉變等,執行者不作為,甚至公開地執行與學校決策相違背的決策。此類執行特征明顯具有沖突性、矛盾性。執行層與決策層發生消極或激烈的對抗,采取拖延、不作為、對抗等方式來抵制決策的執行。對抗式執行對學校整體決策來說具有重要的負面作用,是學校要竭力避免的。
無論是隱蔽性的執行偏差,還是明顯、激烈的沖突性執行偏差,都對學校的整體決策帶來阻滯。執行的偏差導致學校決策目標難以實現、決策資源的浪費、不必要的內耗,并影響學校決策層的權威。在學校情境中,為什么會出現執行偏差?新制度主義可能為此類現象提供解釋與分析的框架。
二、新制度主義的制度邏輯與作為制度化組織的高等學校
(一)制度的內涵
制度一詞是新制度主義的關鍵詞,貫穿于整個新制度主義的始終。新制度主義分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三種理論流派,每一種學科對制度的理解側重點都有所不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主要強調制度對人行為的約束,防止在交往互動中出現的機會主義。柯武剛(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飛(Manfred E·Streit)認為:“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它抑制著可能出現的機會主義的和怪僻的個人行為,使人們的行為更可預見并由此促進著勞動分工和財富創造。制度,要有效能,總是隱含著某種對違規的懲罰。”[3]新制度主義政治學關注制度的道德性因素對人行為的制約。馬奇(March)和奧爾森(Olsen)強調:“制度是社會組織的規則,它包括慣例、程序、習俗、角色、信仰、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知識。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程序和規范,還包括為人的行動提供‘意義框架’的象征系統、認知模板和道德模板。”[4]對于新制度主義社會學來講,制度則是“為社會生活提供穩定性和意義的規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要素,以及相關的活動與資源”[5]。在這個定義中,制度具有多面性,它是由符號性要素、社會活動和物質資源構成的持久社會結構。而且,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將文化—認知要素納入到制度框架內,擴大了制度的外延。
(二)制度的邏輯
深受韋伯的理性組織思想的影響,傳統的組織理論認為組織是一個封閉的系統。組織的生產效率、生存際遇主要受到組織內部的技術環境所影響。所以,早期的組織理論主要集中于研究如何提高組織內部的生產效率。20世紀50年代,由默頓為代表的哥倫比亞學派卻反其道而行之,專門研究理性組織的“有目的無預料后果”。塞爾茲尼克在其經典的研究《TVA與基層機構》(TVA and Grassroots)中發現組織并不僅僅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更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組織不僅受到內部技術環境的要求,同時還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20世紀70年代,新制度主義代表人物邁耶和羅恩發展了哥倫比亞學派的這一思想,提出組織不僅受到技術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
新制度主義認為,“技術環境”指的是組織的物質資源環境,技術環境強調“效率”,要求生產最大化。“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即一個組織所處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會規范、觀念制度等為人們所‘廣為接受’(take-for-granted)的社會事實”[6]。制度環境的邏輯是“合法性”(legitimacy)機制。
“合法性”是新制度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新制度主義認為“合法性是一種普遍的理解或假定,即一個實體的行為在某一社會結構的標準體系、價值體系、信仰體系內是可取的、正當的和恰當的”[7]。它主要“強調的是在社會認可基礎上建立的一種權威關系,即合法性機制可以在無形中迫使組織接受特定制度環境中所要求的具有合法性的行為模式”[8]。
對制度構成要素強調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合法性機制”,同時也影響著組織中的群體、個體的行為邏輯。斯科特認為,“合法性”包括:規制性合法性、規范性合法性以及文化認知性合法性[9]。規制性合法性,強調組織的結構、行為要符合外部法律法規的規定。那些強調規制性合法性的組織認為,組織中的個人、群體的行為是基于“回報遞增”,強調利益最大化。所以,組織中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遵循的基本邏輯是“工具性邏輯”。只有制定出強制性的規章制度,約束組織中人們的機會主義傾向,才能控制組織運行的秩序。規范性合法性則基于組織“身份”的合法性,即組織得到外部專業團體、公眾、大眾傳媒等的認可。強調規范性要素的組織認為,組織中的個人、群體基于共同的價值觀與規范等道德性范疇做出行為,即規范規定事情應該如何完成,并規定完成目標的行為方式或手段。所以,強調規范性合法性的組織認為,組織中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遵循的是“適當性邏輯”。文化認知性合法性則根據共享的意義系統、認知圖式等被人們當做“理所當然”的符號、圖式、腳本、范疇等來判斷。強調文化—認知性要素的組織認為,組織中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是基于共同信念、行動邏輯。這些信念、邏輯固化在人的頭腦中,使得組織中的人難以想到其他的行為類型。“我們之所以遵守慣例,是因為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那些慣例是‘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恰當方式。”[10]所以,強調文化—認知性的組織認為,組織中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遵循的是“正統性邏輯”。
(三)作為制度化組織的高等學校
雖然所有的組織都受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的約束,但是有些組織更容易受到技術環境的制約,另一些組織更容易受到制度環境的影響。邁耶和斯科特將各種類別的組織分為:強技術環境、弱制度環境組織(如大型企業);強技術環境、強制度環境組織(如醫院)以及弱技術環境、強制度環境組織(如學校)[11]。高等學校是典型的強制度環境、弱技術環境的組織。因為“像學校和大學這樣的組織更多地是由共享的信念——‘神話’而非技術需要或效率邏輯聯系在一起的”[12]。作為制度化的組織,高等學校受制于制度環境,其內部結構、活動受外部的規制性、規范性以及文化認知性因素的影響。所以,用新制度主義來解釋高等學校組織行為是可取的。本文將以制度的三種不同要素所強調的邏輯為分析框架,進而探索高校決策執行偏差發生的原因。
三、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的高校決策執行偏差原因
(一)源于工具性邏輯的決策執行偏差
“工具性邏輯”是源于經濟學中的“經濟人”的假設,認為行動者的行為是基于精心計算的自利目標。長期以來,新制度主義忽略組織、群體或個人的“利益”與“能動性”,然而正如古爾德納所言:“如果沒有利益群體的干預,制度是不會產生和發揮作用的。”[13]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就認為制度的產生是為了防止行動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以及最小化交易成本所制定的。所以,作為“經濟人”的決策執行者來說,其執行活動必然受到“工具性邏輯”的影響。
第一,利益誘使執行者發生執行偏差。高校決策是由高校制定的對組織內部資源的權威性分配或者是對組織內部行為的約束或改變。決策的執行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行為的改變。然而,一切改變都有“成本”。基于“工具理性”行動邏輯的執行者在執行決策過程中,必然會計算得失。如果決策執行的成本小于決策的效果,那么執行者會毫不遲疑地執行決策。一旦決策執行成本大于決策的效果時,執行者便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來阻止決策的執行。新制度主義學者奧立弗認為,組織內部執行者遇到外部制度壓力,它們會能動地采取應對策略:默認或遵守策略、妥協策略、回避策略、反抗策略、操縱策略來實現自身的利益[14]。這樣決策的執行更像是執行者與決策層的一種“博弈”過程。政策學者E·巴達馳(E.Bardach)將這種執行稱為“執行賽局”[15],執行者與決策層之間利益的博弈,每個參與者都想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這樣的行動邏輯下,利益導致執行者在執行決策過程中,出現執行偏差以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無視組織整體決策目標的實現。這樣的博弈往往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
第二,信息不對稱導致對決策執行偏差。信息不對稱是指交易雙方之間存在著信息分布的不均,一方擁有信息優勢,另一方則處于劣勢,信息優勢一方利用此種優勢,實現利益最大化。信息不對稱根據時間先后,可以分為事前信息不對稱(即“逆向選擇”)、事后信息不對稱(即“道德風險”)。信息的不對稱的發生存在主觀、客觀兩種影響因素。主觀因素是信息優勢一方蓄意利用此種優勢,從而實現自身利益;客觀因素則是由于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等因素造成的不對稱。在決策執行中同樣也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
首先,信息溝通的層級化導致“逆向選擇”。“逆向選擇產生的原因是占據信息優勢的一方隱藏了信息(或知識)”[16],從而產生的不對稱,基于委托—代理理論,高校決策制定者是委托人,高校中的各學院、職能部門等執行者是代理人,委托人委托代理人執行決策,從而實現決策目標。在執行之前,由于高等學校是典型的科層制組織,其信息的流通渠道呈現層級化。在自上而下的信息傳遞過程中,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考慮,故意刪減信息或者曲解信息。當然,也有可能會出現信息的無意流失或者曲解。但是,這些信息的不對稱最終導致執行者并未掌握完全的決策信息,或者對決策精神未能充分理解,甚至誤解,從而影響決策執行效果,發生執行偏差。
其次,“道德風險”導致對執行監督的困難。“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是占據信息優勢的一方隱藏了行動”[17],從而產生信息的不對稱。執行者在執行決策中擁有信息的優勢,他們清楚地知道執行的進度、執行的效果以及執行的反饋等信息。但是,執行者在自下而上的反饋信息的過程中,并不會全盤托出,而是基于決策制定者、監督者等的“偏好”來進行匯報。通常情況下,執行者會隱藏執行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反映執行者的“成績”,有的甚至謊報、虛報執行實情,希望通過信息的反饋來實現個人的晉升或者群體、機構的發展等。同樣,在自下而上的反饋過程中,執行者也可能出現信息統計失誤、遺漏等無意識的信息失誤。由于執行者在執行中隱藏了行動,占據著信息優勢,造成決策制定者、監督者無法有效地監督執行活動,從而導致執行偏差。
(二)源于適當性邏輯的決策執行偏差
“適當性行動邏輯”指組織、群體或個人在此種情境中的活動、行為是符合共同的價值觀與社會規范。即行動者在該情境中的行為是“適當”的。
第一,制度環境壓力導致組織內部決策執行偏差。作為高等學校的子系統,執行機構不僅受到了組織外部環境的影響與制約,同時也要受到組織內部校級層面規章制度、決策要求的制約。可以說,校級層面的決策以及學校外部的社會影響都是執行機構的制度環境。新制度主義認為在面對制度壓力的情況下,組織只有采取與制度環境相一致要求、標準等,組織才能獲得“合法性”,得以生存與發展。即此種行為的做出是在此種情境中最“適當”,否則將要面臨身份的合法性危機。作為學校的組成部分,決策執行者為了獲得“合法性”地位,必然要采取與制度環境要求相一致的行為,才能確保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另外,高等學校結構特征為執行偏差的產生提供了可能。高等學校是一種“松散耦合”組織,新制度主義學者威克(Weick)、馬奇(March)和奧爾森(Olsen)提出由于高等學校的目標、核心技術的模糊性、組織機構的獨立性,所以高等學校具有“松散耦合”性。“松散聯結,是指聯結的各方都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但是,每個被聯結的方面也保持它自身的特征,具有一些邏輯的和物質的獨特性。”[18]“松散耦合”的高校具有組織結構與組織活動、組織實際活動與組織運行效果之間的“松散聯結”的特點。所以,高校執行者為了滿足制度環境的要求,獲得合法性,同時又避免執行機構的核心技術——教與學受到沖擊,執行者便采取了“脫耦”的方式來執行制度環境要求。即執行機構從表面上采取了決策要求,然而這些活動與行為在實質上并沒有產生實際的效果,造成儀式性執行或象征性執行。
第二,“信任和善意的邏輯”使得對學校內部決策執行監督的形式化與象征性。在采取了執行活動與執行效果“脫耦”的形式后,組織并沒有出現混亂,日常工作照常進行。這是因為學校采用“信任和善意的邏輯”。“信任和善意的邏輯”假定組織內執行者在工作中都是善意的,組織的管理層以及外部人員對執行者充滿著信任,以此來維護組織的正式結構以及“合法性”地位。由于組織管理層對內部執行者的充分信任,他們將采取“儀式性管理”,即通過“回避(問題)、謹慎(行事)以及忽略(反常)”[19]對執行者表示肯定以及支持。“儀式性管理”盡量減少對組織內部執行活動的檢查與監督,即使有此類活動也只是儀式性的。如,學校要求各個學院采取教學改革,但是學校并不深入到課堂內部采取聽課等形式進行監督與檢查。而是通過學院提交的每個教師的教學改革的資料進行判斷,他們充分信任每個教師,從而相信教師在書面上呈現的“事實”。由于這樣的邏輯使得組織內部的執行偏差屢見不鮮,卻得不到有效的監督與檢查。
(三)源于正統性邏輯下的執行偏差
強調文化—認知層面的制度主義者認為,文化—認知要素即那些人們“視若當然的”的共同的信念、認知圖示以及共同的行動邏輯。“文化—認知性要素構成了關于社會實在的性質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構意義的認知框架。”[20]它強調行動的“正統性”邏輯。
高校組織中的文化—認知要素影響決策執行的方式。“文化”為組織中的個人、群體的“認知”建立了理解的框架,并提供角色行為模板以及結構模式。人們潛移默化地受到文化—認知要素的影響,認為這就是“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恰當方式。一旦有人違背了這種視若當然的行為方式,行動者的行動就面臨“正統性”身份的危機。所以,執行組織或群體的共同信念以及意義系統、認知框架等影響著決策執行的方式。在高校中,由于長期的實踐活動,組織逐漸形成了“慣例”,并逐漸“制度化”,此種“制度神話”被高度“儀式化”、“理性化”,組織內的成員將其內化為自身的行為模式以及參考框架。高校中的決策執行者必然受到組織內的“文化—認知”要素的影響,從而影響到決策執行的方式。如果決策執行部門處于一種“利益沖突文化”,那么決策執行機構很有可能在執行過程中使用“博弈”的策略,與決策層討價還價,以獲得自身利益;處于一種“學院式文化”的組織中,執行機構采用分權、民主、集體協商式的執行方式。由此可見,文化—認知要素形成了執行者的執行思維以及執行形式。
[1]劉獻君.湖北省高等教育學會第七屆三次會議暨2013-2014年度學術年會中的“關于高校決策的幾個問題”的報告[Z].
[2]石火學.教育政策執行的概念、屬性與內在價值[J].江蘇高教,2012,(5):9—12.
[3][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5.
[4]James C. March &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 Basis of Politics[M]. New York: Free Press,1989.
[5][9][10][14][20][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第3版)[M].姚 偉,王黎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56.162-164.66.179-182.65.
[6]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72.[7]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20(3):571-585.[8][19]Meyer,John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 pp345-35.
[11]Meyer, John W. and W. Richard Scott 1983a “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gitimacy Problem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edited by John W. Meyer and W. Richard Scott,Beverly Hills,CA:Sage.
[12]海因茲-迪特·邁爾,布萊恩·羅萬.教育中的新制度主義[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7,(1):15-24.
[13]DiMaggio, Paul J.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ynne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pp.3-22, Cambridge: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5]Bardach, E. The implementation gam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7.
[16][17]辛 琳.信息不對稱理論研究[J].嘉興學院學報,2001,(5):36-40.
[18][英]托尼·布什.當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強海燕,主譯.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170.
(責任編輯沈廣斌)
G640
1003-8418(2014)06-0027-05
A
10.13236/j.cnki.jshe.2014.06.006
肖京林(1986—),女,河南信陽人,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博士生,曲靖師范學院教務處講師。
湖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3年重點課題“高校領導決策制度研究”(2013A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