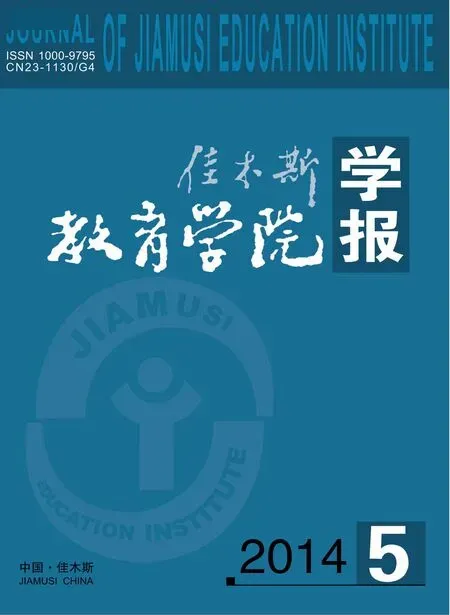丘吉爾《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演說的認同策略分析
安 昊
(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 北京 100875)
丘吉爾《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演說的認同策略分析
安 昊
(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 北京 100875)
本文借鑒新修辭學的認同理論, 以丘吉爾的演說為研究語料,分別從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誤同三方面解讀丘吉爾如何運用認同策略來贏得聽眾的支持。同時也證明認同策略有助于揭示政治演說中的修辭策略。
伯克;新修辭;認同策略;丘吉爾演說
溫斯頓·丘吉爾有很高的文學造詣,1953年他獲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這樣寫道“因為他精通歷史和傳記的藝術以及他那捍衛崇高的人類價值的光輝演說。”美國《展示》雜志將他評為近百年來世界最有說服力的八大演說家之一。學術界也對丘吉爾的演說顯示出極大的興趣,學者們從政治學、語言學、傳統修辭學和傳播學等方面對其進行分析。本文以丘吉爾《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演說為語料,試圖借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辭理論,從認同策略的角度,對丘吉爾演說中的修辭策略進行解讀,希望為政治演說中的修辭策略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一、伯克的認同理論
肯尼斯·伯克是美國當代著名修辭學家,新修辭學的代表人物。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典修辭學認為修辭學的關鍵詞是“規勸”,具體修辭策略則包括品格訴諸、理性訴諸和情感訴諸。伯克認為修辭是人類主體為使他人形成態度或誘發行為而使用語言的一種行為,其目的在于實現認同(identification)。要達到誘發他人行動的目的,說話者必須使用符號尤其是語言與聽眾取得認同,即讓聽眾感到其所思、所言、所感、所為皆合乎情理。Herrick(2005)總結伯克提出的三種認同策略,即同情認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對立認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與誤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其中,同情認同是說話者希望通過共同的情感、價值觀、風格等來與聽眾建立一種親近關系。伯克認為,勸說聽眾時,要與他們具有相同的思想或觀點,取得情感的近距離交流,產生共同情感,達到同情認同,說話者與聽眾是一種相互合作的關系(常昌富,1998)。例如,有的政治人物會親小孩。政治人物親小孩,父母也親小孩,于是父母們易于在情感上認同政治人物。對立認同是一種通過分裂(segregation)而達成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常昌富,1998)。大家由于共同反對的東西而認同聯合,美國和蘇聯本來是敵人,但在二戰中為了戰勝德國這個共同的敵人而實現認同(劉莉,2008)。誤同是一種無意識的、幻覺式的認同方式,將一個實體的屬性不自覺地投射到另一個實體上(方小兵,2009)。例如,一些產品爭相請名人代言,因為廠家相信消費者可能會把對名人的積極態度遷移到廣告產品上,對廣告內容產生誤同。
二、認同策略在《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演說中的體現
1940年納粹德國橫掃歐洲大地,英國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丘吉爾臨危受命,組建戰時內閣并出任首相。《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是他當年在英國下議院發表的就職演說。丘吉爾以詩一般的語言,鐵一般的意志慷慨陳詞,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英國將誓死戰斗!那么丘吉爾是如何說服聽眾,與聽眾達成認同的呢?背后的修辭策略又是什么?下面將用認同策略對該演說進行分析。
(一)同情認同的體現。西方代議制政府歷來存在政黨之爭,丘吉爾是英國保守黨領袖,但在當時特殊歷史背景下,他急切地需要團結英國國內一切力量抵抗納粹德國。因此,丘吉爾組建的是盡量代表各方利益的聯合政府。同情認同強調聽眾與說話者之間的共同情感,共同利益,希望借此實現聽眾對說話者的認同。在演說中,丘吉爾運用了這種認同策略,他指出:“戰時內閣已經成立,有五位內閣成員,他們同反對黨自由黨一起代表了全國上下的團結一致。三黨領導人已經同意,或加入戰時內閣,或擔任高級行政職務”①。英國有影響力的政黨達成一致,其領導者“或加入戰時內閣,或擔任高級行政職務”,這讓支持不同政黨的議員和廣大民眾感到各自利益得到了新一屆政府的尊重,使自己與新政府建立了緊密聯系,愿意支持響應新政府的號召,更有利于實現“全國上下的團結一致”。
丘吉爾演說中復數第一人稱指示語的大量使用也是其同情認同的重要體現形式。指示語是說話者與聽眾之間距離的標尺,而復數第一人稱指示語,如“we”“us”和“our”則暗示說話者與聽眾心理距離近。談到戰爭局勢時,丘吉爾說“我們正在挪威和荷蘭的許多地方作戰”,但其實無論是丘吉爾還是大部分英國民眾當時都沒有在挪威或荷蘭戰斗。丘吉爾這里用“我們”不僅來指當時在挪威和荷蘭作戰的英國軍人,還讓聽眾覺得自己也是這場正義之戰的參與者,既能使他們認識到戰爭的緊迫性又能鼓舞其備戰熱情。演說最后一段,在闡述新政府抵抗納粹德國的政策和目標時,丘吉爾使用了11個“我們”,強調抵抗德國法西斯是全體英國人民的共同使命,拉近了聽眾和自己的距離,更能取得聽眾的信任。丘吉爾的“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目標”和“我們的事業”都使聽眾不自覺地認同演說者的觀點,把演說者當成自己的代言人。
(二)對立認同的體現。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宣告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綏靖政策”的徹底破產。幾個月后,張伯倫被迫下野,丘吉爾受命組織新內閣。因為錯綜復雜的戰爭形勢,丘吉爾在幾天內組織起新政府,難免會有人質疑其程序的合法性和任命的合理性,也難免會有人在政府改組中受到影響而有所怨言。丘吉爾在演說中采用對立認同策略力爭化解這些問題。丘吉爾首先在演說的開始部分提到:“由于事態嚴峻,極其緊迫,僅用一天完成這項任務(注:組織新內閣和任命部分高級行政官員),是必要的”,隨后他又在演說中間部分開誠布公地談到:“在這危急關頭,我希望你們原諒我今天沒有在下院做長篇演說。我希望在這次政府該組中受到影響的朋友們、同事們以及昔日的同僚們諒解在所難免的禮節不周”。對立認同指的是說話者要使聽眾相信,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大家因為反對共同的敵人而相互認同,聯合在一起。在丘吉爾的演講中,同樣也通過確立對立面——“黑暗、悲慘的人類罪惡史上最窮兇極惡的暴政”——讓下議院議員支持他的舉措,讓受政府改組影響的官員體諒他的良苦用心,讓普通民眾認同他的所作所為,最大可能團結全國力量抵抗納粹德國。
(三)誤同的體現。演說末尾談及“我們的目標”——勝利,丘吉爾采用了誤同策略:“沒有勝利就沒有英帝國所代表的一切,沒有勝利就沒有世代相傳、推動人類奮勇前進的動力”。通過誤同策略,丘吉爾將英國的勝利上升到關系英國傳承乃至全人類向前發展層面,讓聽眾認識到抵抗戰爭的重要意義,似乎他們能夠英雄般拯救國家,推動人類進步。通過誤同策略的運用,丘吉爾“夸大”了英國勝利的意義,讓民眾更易于認同新政府,團結起來抵抗德國法西斯。
三、結語
本文以丘吉爾的演說為語料,運用認同理論對其進行了分析,說明了丘吉爾是如何運用同情認同、對立認同、誤同的策略來拉進與聽眾的距離,獲得聽眾的認同與支持。新修辭學對政治演講的研究突破了傳統修辭學中語言規勸的范疇,大眾傳媒時代政治人物更注重營造形象的方法,新修辭學的認同理論對解釋政治演說中的修辭策略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與方式。
注釋:
①:本文的演說詞譯文均轉引自《丘吉爾經典演講詞賞析》([英]丘吉爾,著.陳昕,郝勇,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下同。
[1]常昌富.當代西方修辭學:批評模式與方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方小兵.奧巴馬競選演說的新修辭分析:認同策略[J].廣西社會科學,2009(4).
[3]劉莉.伯克新修辭學同一理論探析[J].廣西社會科學,2008(8).
[4]Herrick J A.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J]. Needham Heights, MA. A, 2005.
Analysis of Churchill’s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add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An 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is thesis intends to analyze Churchill’s add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and demonstrate how three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were used to win the audience’s support.This thesis also proves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helps to reveal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political speeches.
Burke; new rhetoric;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Churchill’s address
H05
A
1000-9795(2014)05-0067-02
[責任編輯:董 維]
2014-03-10
安 昊(1990-),男,山東日照人,從事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寒假調研項目(項目編號2014FX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