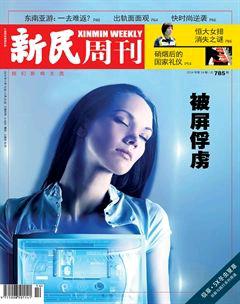殉道考
洪流
作為職業(yè)精英的法律人對(duì)于道義的堅(jiān)守,較鮮為人知,但也更令人唏噓。
有一個(gè)中國(guó)人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叫“趙氏孤兒”,講的是春秋時(shí)晉國(guó)忠臣趙氏遺孤的事。由于奸臣屠岸賈當(dāng)?shù)溃w家被滅門(mén),為了拯救趙氏遺孤,許多仁人志士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有以命相許的趙母、韓厥、公孫杵臼,還有獻(xiàn)出自己血脈、假意投靠屠岸賈、忍辱負(fù)重二十年的程嬰。這些仁人志士的犧牲,最終換得了趙家遺孤的復(fù)出和冤案的昭雪。在人性和道義價(jià)值遠(yuǎn)高于生命的先秦時(shí)代,趙氏遺孤所代表的,就是正義的一方;而那些仁人志士付出巨大犧牲所要追求的,也就是心中的道義。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wú)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同樣為了道義,這些仁人志士所選擇的方式卻截然不同,有公孫杵臼等人以性命相許的死殉,也有程嬰為了達(dá)到最終目的而獻(xiàn)出骨肉、忍辱負(fù)重二十年的活殉,大家以慘重的代價(jià),最終捍衛(wèi)了道義的價(jià)值。
是故殉道易,衛(wèi)道難;死殉易,活殉難。而道義最終的彰顯,是要通過(guò)國(guó)家或統(tǒng)治階層的敕令或旌表,即法律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法律是社會(huì)各個(gè)階層和利益群體價(jià)值觀的統(tǒng)一體,代表著社會(huì)大多數(shù)成員的利益。雖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國(guó)度,法律有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偏重的價(jià)值觀有所區(qū)別,但總的說(shuō)來(lái),公平、正義和秩序,是所有的法律都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即便這些原則的內(nèi)容在不同的時(shí)期和不同的國(guó)度會(huì)有一定的細(xì)微區(qū)別。
中國(guó)過(guò)去的一百年,是翻天覆地的一百年,整個(gè)國(guó)家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的進(jìn)化也經(jīng)歷了驚心動(dòng)魄、跌宕起伏的一百年。相對(duì)于普通民眾的赴難,作為職業(yè)精英的法律人對(duì)于道義的堅(jiān)守,則較鮮為人知,但也更令人唏噓。一方面,他們有著和普通人一樣的血肉骨脈,承擔(dān)著與普通人一樣的生存壓力;另一方面,他們以其職業(yè)精英的身份,對(duì)于法律又有著天然的守土衛(wèi)疆之責(zé)。他們當(dāng)中,慨然赴難者有之,忍辱堅(jiān)守者有之,雖殉道方式不同,但為了法律信仰的堅(jiān)守目標(biāo)則是一致的。
法學(xué)家楊兆龍,早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xué)和東吳大學(xué);后獲哈佛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學(xué)位;通曉英、法、德、意等八國(guó)外語(yǔ),對(duì)大陸、英美兩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詣;曾任推事、律師、憲法起草委員會(huì)和資源委員會(huì)專(zhuān)員、代理最高檢察長(zhǎng)等職;曾當(dāng)選為中國(guó)比較法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刑法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國(guó)際刑法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等職;被荷蘭海牙國(guó)際法學(xué)院評(píng)選為世界范圍內(nèi)50位杰出法學(xué)家之一。上世紀(jì)50年代后,因堅(jiān)持自己的“法律繼承論”觀點(diǎn),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長(zhǎng)期遭到關(guān)押,1979年不幸離世,1980年上海市高院為其平反昭雪,恢復(fù)名譽(yù)。
前輩的磨難并未嚇倒活著的勇士,法律的火種只要有一脈相傳,我們的道義就有燎原的土壤。在上世紀(jì)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劫后余生的法學(xué)家,又扛起了法律的大旗,為了這個(gè)國(guó)家的法治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擔(dān)起了法律人應(yīng)擔(dān)之責(zé)。
例如張思之和馬克昌,這兩位法學(xué)大家在“文革”中都曾被打成右派,脫離法學(xué)界一二十年,飽受專(zhuān)制動(dòng)蕩之苦,而一旦國(guó)家恢復(fù)法治建設(shè),他們又義無(wú)反顧地披袍上陣,為了心中的法律信仰而給昔日的加害人擔(dān)當(dāng)起了辯護(hù)人。
1984年,《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法學(xué)卷》正式出版,而就是這本書(shū),曾被鄰國(guó)法學(xué)界認(rèn)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在這本巨著背后,是一批中國(guó)法律界的大家——張友漁、潘念之、王鐵崖、李浩培、韓德培、江平、關(guān)懷、高銘暄、沈宗靈、吳家麟等。他們都是早在數(shù)十年前就享譽(yù)國(guó)內(nèi)外的法學(xué)精英,在動(dòng)蕩的年代里,他們都以對(duì)法律信仰的堅(jiān)守,把法學(xué)的火種保存了下來(lái)。一旦春風(fēng)拂面,他們又擔(dān)起了歷史的重任,參加到中國(guó)法治建設(shè)的進(jìn)程中來(lái),因?yàn)樗麄冎溃妥约旱膫€(gè)人經(jīng)歷而言,在他們的生命中還有比血淚和苦痛更偉大的東西。
清明至,是為祭,以祭奠為信仰獻(xiàn)身的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