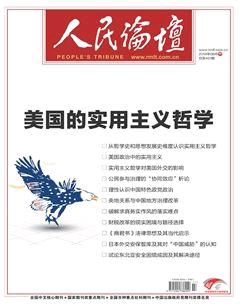房價調控面臨兩難的深層原因
周京奎
房價調控面臨兩難的深層原因
周京奎
在過去十余年間,住房市場發展承擔著推動經濟發展、城鎮化建設和改善民生的多重目標,這就使得住房調控政策面臨兩難選擇。為使住房市場走出“調控-放松-再調控”的怪圈,我們提出以下建議:以住房保有稅收政策替代限購政策,將有助于建立價格-成本調節機制;建立住房梯級供給體系,將有助于建立供給-需求調節機制;引導資金有序從住房市場流向實體經濟和創業市場,促進住房市場平穩運行;建立公共投資溢價回收機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住房政策 調控 兩難
在經歷十余年快速發展后,我國住房市場呈現“高房價、高需求、高供給”并存的特征。為使住房市場回歸理性發展,國務院于2010年4月出臺《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要求房價上漲過快城市限制家庭購房套數,被業界稱為“限購令”。隨著限購政策的實施,住宅需求增幅有了顯著下降,市場供給明顯大于需求,并成為住房市場走向疲軟的主要推動力。住房調控“松”或“緊”,這是當前我國住房市場發展面臨的一個兩難選擇。
我國住房市場發展存在多重目標
在過去十余年間,住房產業被看作是國民經濟體系的支柱產業。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對鋼鐵、水泥等制造業及眾多服務行業等生產、消費關聯產業的帶動效應約為1.5-2倍,即
關于住房調控的“松”與“緊”
當前,住房市場調控面臨“松”與“緊”的兩難問題:政府調控過“松”,容易導致房價增長過快,影響民生;政府調控過“緊”,房價下跌,又或將導致經濟增速放緩等。住房市場調控之所以出現這一兩難問題,在于住房市場發展承擔著推動經濟發展、城鎮化建設和改善民生的多重目標,但房價調節機制失靈使調控政策難以達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房地產領域過度投機帶來的高風險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考慮調控政策的后果,住房市場推動經濟增長與城市發展的重任仍然沒有消除。促進住房市場穩定是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選擇,為此,要以完善的住房制度為基礎,結合土地供應、稅收、金融等政策工具,構建長期有效的、有利于住房市場穩定發展的機制。每100元的房地產投資需求,大約帶動其它關聯產業150-200元的需求。①這說明住房產業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它也是住房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
住房市場發展的第二個目標與城鎮化建設有關。雖然,2003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40.53%,但城鎮化質量尚處于較低水平,地方政府面臨著城市增長和舊城改造的雙重任務。為從規模上和質量上提高城鎮化水平,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巨額資金,并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將籌集資金的重點放到土地財政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上。土地財政的核心是政府獲得土地出讓金收入,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通常以土地財政作為融資抵押。這就是說,兩者相互推動,并在客觀上會推高土地價格和住房價格。由此可見,住房市場發展一方面推動了城鎮化發展,另一方面其發展也是城鎮化的需要。
住房市場發展第三個目標是改善民生。在我國住房制度改革過程中,住宅需求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并呈現了三個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是以租住公房為主,私有住宅為輔,該模式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第二階段是以租住公房和私有住宅為主,該模式發生在1991-1998年間;第三階段是以私有住宅為主,租住公房和私人房屋為輔,該模式發生在1998年以后。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了全方位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住宅市場呈現出了加速發展的趨勢,城鎮居民的住房福利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多重目標下住房調控政策選擇難題
住房市場發展承擔著推動經濟發展、城鎮化建設和改善民生的多重目標,這就使得住房調控政策面臨兩難選擇,其深層次原因有:
第一,住房市場內生調節機制缺乏使調控政策難以達到改善民生的目標。限購政策是典型的行政干預政策,在強調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今天,仍然采用該政策說明住房市場缺乏內生調節機制。
存在住房價格調節機制失靈問題。在限購政策出臺之前,住房市場出現了“高房價、高需求、高供給”特征。高房價對市場沒有產生抑制效應,而高供給對于價格也沒有產生下行影響。這雖然有住房的資本品屬性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市場本身缺少內生調節機制。在住房價格上漲預期下,消費者普遍存在規避未來價格上漲風險的心理,因而提前進入市場。由于購房者無需繳納住房保有稅,使得這些提前進入住房市場的消費者獲得了較高資產增值收益。其結果是,未來會有更多的消費者提前進入市場,最終導致價格失去調節功能。
城鎮化快速推進過程中,住房價格形成機制更趨復雜。在此階段,住房價格不僅受市場交易量影響,同時更受推動交易量變化的制度(公積金制度等)與非制度(城鎮化階段等)因素的影響。對于前者來說,由于公積金貸款額度與公積金繳存余額有直接關系,而個人繳存的公積金又對其貸款還款能力有直接影響,這使得公積金繳存模式和貸款模式對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福利的影響低于中高收入家庭。對于后者來說,城鎮化過程中公共投資資本化極大地推動了住房價格上漲,從而導致市場調節機制失靈。
第二,住房市場風險規避機制尚未建立,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考慮調控政策的后果。
高房價背景下,房地產信貸規模的持續擴大必然會產生較高的信貸風險。
高房價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將面臨較高的土地抵押貸款風險。由于這部分信貸的獲得取決于土地價格,當房價預期上漲時,這些土地抵押貸款風險不高;但當房價出現全面調整時,其巨大的風險就會暴露出來。
經濟房地產化導致房地產供給和需求環節出現過度投機,并將進一步推高市場價格風險。在住宅供給或稱開發領域,大量有實力的非房地產企業涉足房地產開發。一些中小民營企業也放棄實體產業經營,轉而專門從事房地產投資和投機。在住宅需求領域出現的、類似溫州“炒房團”式的投機需求打破了原有的需求結構,并且形成了強烈的房價上漲預期,導致市場出現大量的投機需求。
第三,住房市場推動經濟增長與城市發展的重任仍然沒有消除。目前,雖已淡化了住房產業的支柱產業地位,但住房產業的前后產業帶動效應仍然不可忽視。尤其在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尚未完成時期,維持傳統產業發展,推進新興產業發展,提高高新技術產業比重,仍需要住房產業的適度發展。
有關住房調控政策選擇的若干建議
為使住房市場走出“調控-放松-再調控”的怪圈,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以住房保有稅收政策替代限購政策,將有助于建立價格-成本調節機制。長期實行限購政策不利于建立有效的住房市場內生調節機制,而最有可能替代限購政策的是住房保有稅收政策。住房保有稅收政策的實施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達到限購政策效果,二是有助于建立市場內生調節機制。為此,住房保有稅收政策制定時需要同時考慮價格因素和持有成本因素。具體來說,就是計算稅率時既要考慮住房面積,也要考慮住房價格,最終以此建立住房市場價格-成本調節機制。
第二,建立住房梯級供給體系,將有助于建立供給-需求調節機制。目前的住房供給體系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商品房梯級供給體系和保障住房梯級供給體系沒有形成聯動效應。住房消費群體是在這兩個供給體系中進行分配的。屬于商品房供給體系的消費者,在住房支付能力下降后將被劃歸為保障住房供給體系的消費者。也就是說,住房消費群體類型是動態變化的,而現在的住房供給體系則是靜態運行的,因此,需要在兩種類型的住房供給體系間建立動態聯系,這將有助于建立供給-需求調節機制。
第三,引導資金有序從住房市場流向實體經濟和創業市場,促進住房市場平穩運行。住房市場運行不穩定會將居民財富暴露在高風險之下,使得那些具有創業傾向的潛在創業者面臨較強的流動性約束,不利于創業群體的擴大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目前,政府實行的限購、限價等行政手段都帶有“堵”的性質,并不能真正解決住房市場中的問題,需要更多采取疏導性的經濟政策,引導資金有序流出房地產市場,流向實體經濟和創業市場,避免住房市場和宏觀經濟出現大幅波動。
第四,建立公共投資溢價回收機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我國城鎮化需要大規模公共投資推進,而這些公共投資必然要資本化到所投資區域的土地價值中,從而導致土地增值。美國知名經濟學家Henry George曾指出,所有土地價值以及由此產生的任何增值,都是由公共活動而非個人勞動產生的。可通過稅收途徑把公眾活動帶來的土地增值從土地所有者那里收回,以供全社會使用。上述理論表明,在我國快速城鎮化時期,需要建立公共投資溢價回收機制。地方政府可將溢價收益用于投資回收期較長的城市建設項目,并以此逐步消除其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導)
【注釋】
①徐繼英、鄧業軒:《房地產業發展對地方政府收入的影響分析——以安徽省為例》,《調研世界》,2013,07:17-20。
責編/劉瑞一 美編/李祥峰
F29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