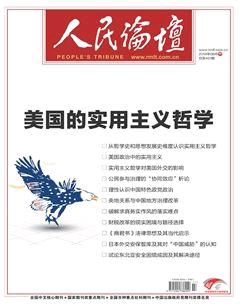轉型期央地權力分配難題待解
燕繼榮
轉型期央地權力分配難題待解
燕繼榮
我們要走出中央與地方“統-分-統”這樣的怪圈,就要對權力的類型和內容做更加科學、細致、合理的劃分。“分權”既可以表現為縱向結構的分權,又可以表現為橫向結構的分權。一個良好的政府公共權力的架構、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力間的權力分配是一個國家進行治理和開展改革的基礎。在未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究竟何去何從,這還要取決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取決于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取決于中央和地方的一個均衡的狀態。
央地權力 轉型期 橫向分權 權力細分
關于政府治理的“統”與“分”
權力分配的“統”與“分”這一矛盾體,在中國轉型社會中煥發出新的歷史變化與時代要求。傳統層面上,在政府治理中“一統就死,一分就亂”的怪圈循環往復,構成一個始終困擾著中央和地方權力分配的兩難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平衡狀態還未達到,所以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狀態一直處于變動之中。我們應該設計一套穩定、成熟的制度,這套制度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時中央又應有更大的自主性,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應該呈現相對均衡的態勢。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有一個兩難的問題會凸顯出來,到底是分權好,還是集權好。在一般意義上來說,分權是一個方向,就是把政府的權力下放給社會,把中央的權力下放給地方。為了激活社會的活力、激發地方的自主性,做了很多市場化、分權化的改革。但是,過去幾十年,我們這樣的分權改革也暴露出很多問題。比如說,地方的差異性造成了國家的很多方面不統一、不一致、不均衡等。這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問題。而另一種聲音認為,政府應該集權。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對政府集權化的呼聲越來越強,到現在更加強調“頂層設計”,集權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方向。到現在,我們實際上還在討論一個久遠的話題:“統”和“分”的關系。過去總有一個觀點,即中國治理的特點是“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總是在“統-分-統”這樣的怪圈中循環。我們今天的兩難實際上就是政府還沒有跳出“統”和“分”這樣的怪圈。
細化權力類型、偏重橫向分權有助于擺脫央地兩難怪圈
走出這個怪圈,要對權力的類型和內容做更加科學、細致、合理的劃分。首先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關系方面,什么要“統”,什么要“分”,政府的功能要體現出來;在大政府的概念上,“統”和“分”主要更多地體現在“各盡其職,各盡所能”,能保證各個功能既是獨立,又是協調運作的;在小政府的層面,主要表現在上下層級之間的協調性,不同地區和政府間的配合;社會建設方面,也涉及政府與社會間的良好的關系。哪些屬于公共服務,需要讓渡出去,怎么讓社會處于自我運行的狀態中,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如果把這些關系處理好的話,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走出“統-分-統”惡性循環的怪圈。原來,我們的思路是“統”和“分”二者擇一,現在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如果我們對權力不同的類型和不同的組合形式進行進一步科學、合理的研究,就會發現一個合理的政府應該對有些權力進行統一和集中,有些權力必須要下放,而且下放到哪一級要有更加合理、合法的說明。就像在美國的聯邦制度中,哪些是聯邦政府的責任、應由聯邦政府出錢、出力、出人,哪些是地方政府的責任,這些都是很清晰的。當然,中國比較復雜,地方上又分得很細,這樣就形成一個權力結構的多層次分類的架構,如何才能走出這個怪圈呢?具體地說,還是要回答政治學的基本問題,什么屬于國家的權力,什么屬于地方的權力,什么屬于機構的權力,把這些要區別開來。國家的權力是屬于整個共同體的,涉及整個利益共同體的結構,屬于國家的權力應該是統一的、一致的,當然要由最高權力機關來行使、掌控;進一步來說,什么樣的權力才屬于國家的權力,我認為軍隊、司法(統一的法律體系下,不同地方可以有差別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公民權利等應該是全國范圍內都得以統一。就地方而言,經濟發展采取哪種方式,應有地方自主地來做選擇。當然,中央可以出臺一個整體的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基于這個規劃、戰略,各地政府要做適當的選擇,不能違背這樣的一個戰略,我想這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具體而言,說到“分權”,在縱向方面,我們傾向于等級制這樣的結構,這是基本上保持不變的。因此,在橫向的方面,應該有更多地考慮。“分權”既可以表現為縱向結構的分權,又可以表現為橫向結構的分權。我們一直認為“分權”僅僅是指縱向層面的,所以就一味地將中央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可能會下放得過頭了,比如說司法的地方化顯然是不合理的。就橫向的分權而言,我們在同一個層面上把黨委書記的權力做得很大,導致其他橫向的權力弱化。所以,要進一步做一個區別,才有可能走出這個怪圈。一味重視縱向分權就容易造成一個問題,即地方權力的集權化和中央權力的分權化該如何平衡。只有同樣重視橫向的權力架構,才能讓地方間的權力形成一個平衡的架構,可以實現互相制約,而我們在這方面欠缺考慮。這樣就造成把中央的權力分化得越多,地方所截留的權力就越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造成這個問題真正的原因還是沒有考慮橫向的分權。中央將權力下放給地方黨委的同時,也應該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人大等機構或組織。在地方上完全可以進行權力制衡,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合理的架構。假設中國是一個董事集團公司,30幾個省、市、自治區也就是30幾個分公司。那么中央就是一個董事會,董事會可以采用集權的方式,但是分公司可以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一定程度的分權架構。因此,怎么把分權的原則更好地體現出來,怎么在制度的架構上有更好的設計,這是最關鍵的。分權必須發揮其不能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下,把改革總的方向界定為分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關鍵的問題是,對分權要有一個制度性的架構,要有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的考慮,這也符合政治學理論本身的學科邏輯。
權力分配是國家治理和改革的基礎
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都架構在良好的權力分配的基礎之上,我們現在就把良好的架構通過憲法的方式規定下來。憲法的體制被認為是一個國家基礎的架構,憲法的質量取決于憲法的原則,憲法的原則里都是關于公民權利、關于政府權力架構的基本約束。這么看來,一個良好的政府公共權力的架構、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力間的權力分配是一個國家進行治理和開展改革的基礎。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國家“統-分”的權力結構如果不能處理好的話,國家發展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比如現在分離主義、分裂主義,包括某些集團、某些人群恐怖主義的行為,說到底也是和權力架構、權力分配有很大的關系。這些問題的存在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統和分”的關系,什么領域是中央該管的,什么領域是地方可以自治的,什么領域是要必須承擔義務的,什么領域是地方和個人能夠來治理的,如果這些權力有一個明確的規則和界定的話,那么這些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換句話說,權力結構優化也是一個治理結構的問題。權力結構如果不能很好地得以架構,國家治理也會存在各種各樣的隱患。
在未來,理想的權力分配應該是國家有完整的領土權力,貨幣是統一的,司法是一致的,公民權利是一致的,選擇的道路是統一的,外交是統一的,軍事是統一的,中央政府應該對以上領域進行統一的管轄;地方的權力則屬于經濟、社會生活、地方秩序的層面和范疇,這是基本的原則。就現實層面來說,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究竟何去何從,這還要取決于國家處于哪個發展階段,也取決于中央地方的一個互動的狀態。所以,這是一個變動的過程。像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制度,已經把地方和中央的權力架構相對固定化了,它采用聯邦制將其穩定下來。我們現在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變動期,還沒有探索出一條很理想的制度性的框架,所以一些地方才會表現出不滿情緒。極個別的傾向或不滿情緒有的比較激烈,表現出分離主義的傾向;比較溫和的,就產生出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隱晦的說辭。這些現象都說明,我們這一個合理的“統-分”制度架構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平衡狀態還未達到,所以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狀態一直處于變動之中。我們應該設計一套穩定、成熟的制度,這套制度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時中央又應有更大的自主性,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應該呈現相對均衡的態勢。而且,這套制度在縱向與橫向的權力平衡中,更應該偏重橫向的權力分配。下放權力之前實際上都要考慮到橫向的分權,中央任何權力的下放不希望促成地方的“諸侯”,所以考慮到地方承接權力的主體是誰,以及地方的權力誰來制約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未來我們尋求央地關系平衡的一個努力方向。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主任,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民論壇記者譚峰采訪整理)
責編/劉建 美編/李祥峰
D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