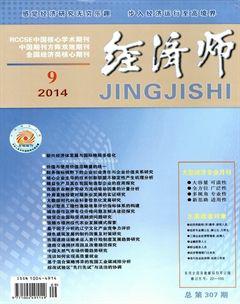山西經濟與全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相關性分析
●王迎紅
山西經濟與全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相關性分析
●王迎紅
經濟周期即繁榮—蕭條周期,整體上反映了各大經濟變量的周期性變動,是與我們的經濟生活緊密相聯,也是國家在對經濟宏觀調控時非常重要的經濟現象與經濟指標。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表現為周期性的波動。且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的經濟周期性波動也有著中國的特色。而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里,帶有中國特色的周期性波動的相關指標也成為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文章以山西省建國后經濟周期性波動狀況為例,簡要分析、總結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宏觀調控的特點和趨勢,并提出減緩經濟周期波動、保障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相應對策與建議。
經濟周期 宏觀調控 山西經濟 波動
經濟增長是一個持續不斷變化的過程,但其變化卻并非穩定。大量的統計數據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往往出現峰值和低谷的反復循環,即形成周期性的波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過程歷經多次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動,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全國性的經濟現象中,更是在地方性的經濟增長中被反應出來。國家性的經濟增長率的波動集中表現了地方性增長率的特性,而地方性的增長率受國家宏觀調控影響,具有一定特征。本文從山西省經濟周期性波動狀況出發,收集我國經濟發展的一些相關數據,旨在分析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周期波動的特點與趨勢以及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時采取的手段,進而簡要研究山西省與全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相關性。
一、山西省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概述
經濟周期指經濟體在運行過程中出現周期性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相互更替、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回顧改革開放的30多年,山西經濟的運行軌跡呈明顯的周期性運行趨向。根據往年GDP增長率作為變量和體現經濟波動的指標,總結30多年來GDP增長率的波形變化來研究其經濟變化的規律。從波動周期的變化看,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省的經濟增長明顯地表現為4個周期,其每個經濟周期大約為10年,分別為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08年、2009年至今四個經濟周期。在第一個經濟周期中,1981年山西經濟增長是該周期的波谷,增長率為0.8%;1984年年中達到周期的波峰,峰值為21.6%,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增長率的最大值;1991年又以4.2%增長率回落至波谷。在1991—1999的第二輪經濟周期中,接第一輪周期的波谷,1991年底經濟增長處于波谷,在次年達到周期的波峰,其峰值為13.8%,到2000年時落至該周期谷底,谷值為7.3%。2001—2008年為第三輪周期,這輪周期接1999年的波谷,開始逐漸回暖,2004年到達該輪周期的波峰,峰值為15.2%,2004年后進入平穩回落階段,2008年回落到8.3%,同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的影響,下降幅度進一步被體現,2009年山西GDP增長5.4%,再次到達周期底部。根據已有各項宏觀數據顯示,山西經濟已經度過第三經濟周期的尾部,即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第三個較長經濟周期的“底部”,逐漸步入當前所處于的第四經濟周期。
隨著基礎建設的逐步完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水平逐漸成熟,山西省經濟增長的潛力呈現出逐期加快的趨勢,具體在數據上體現為:第一個經濟周期中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8.7%,第二個經濟周期提高到10.3%,第三個經濟周期進一步提高到13.1%。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山西省經濟增長的趨勢逐漸呈現出波幅縮小、速度加快、總體運行穩定性增強等特點。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經濟連續五年以上兩位數高速增長的時間段有兩個,第一個是1992年到1997年,其年均增長12.0%;第二個是2001年到2007年,其年均增長達13.1%,比起1992年—1997年的增長期,2001年—2007年的增長期時期長,且增速更快。其原因在于基礎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和政府彈性投資和新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等經濟舉措的實行。在基礎建設基本完善的前提下,經濟波動處于不同階段,實施不同的政府投資和政府采購政策,能夠在短期內調節山西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波動幅度,并將其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長期實施這種經濟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經濟結構和指導發展模式。當下山西正處于當前經濟周期的中間階段,也是經濟周期中實施調控的關鍵時期,因此這是山西經濟實現轉型、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宏觀調控政策將直接決定山西經濟能否實現平穩快速發展,以及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時期。
二、山西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全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對比與分析

圖1 山西及全國GDP增長率(1978—2012)
回顧改革開放的30多年,山西經濟的運行軌跡呈明顯的周期性運行趨向,事實上,山西經濟波動與全國經濟波動有直接聯系。如圖1所示,兩者波動周期大體相同,但山西經濟在同一周期內波動大于全國經濟。山西作為全國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全國大部分地區相比,具體經濟情況較為獨特。與全國經濟增長率對比,山西經濟波動在總趨勢與全國保持基本一致。在此前提下,山西經濟波動情況相比于全國的經濟波動有如下特征:(1)山西經濟的波動強度明顯大于全國經濟波動。山西經濟波動系數達到45%,遠高于全國28%的波動水平。(2)在同一經濟周期內,山西經濟的擴張期明顯短于衰退期,而全國經濟在同一經濟周期內處于擴張期的比重都已超過50%。(3)山西經濟進入增長型波動階段較之于全國經濟比較落后,從1978年—2012年的經濟數據分析,時滯大約在六個月至一年,因此會有“沿海已熱晉未熱,沿海已冷晉未冷”的說法。
通過對山西經濟數據與全國經濟數據的初步對比可以看出,山西經濟波動與全國經濟波動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選取一部分觀測值計算進行相關性分析,山西GDP增長率波動幅度明顯大于全國的GDP增長率波動幅度,而全國的經濟波動只是山西經濟波動的一部分相關因素。近年來,山西經濟的增長速度加快,波動幅度變小,經濟運行也逐漸平穩,并且從整體上看,增長速度有逐漸加快的趨勢。分析其形成原因,隨著宏觀調控的能力不斷增強,山西省的經濟波動在調控下也變得平穩,波動率降低。由此可以得出,當前的穩定發展得益于山西省近期轉型跨越發展的大環境。“綜改型實驗區”的實施與“十八大”后為建設小康社會努力的階段相得益彰,使得山西省在經濟發展階段保持平穩增長的勢頭。其次,山西作為我國能源與原材料中心,其省際間的外貿依存度在全國處于最高水平,即過于依賴外省需求。因此,山西經濟表現出“沿海已熱晉未熱,沿海已冷晉未冷”的形態。由于山西省貿易結構不均衡、產業結構也較為單一,因此造成了作為經濟支柱的能源型工業材料的產業一旦出現波動,隨即會產生經濟運行整體出現大起大落的失控性。山西經濟在全國經濟大環境變動的情況下表現出極強的依賴性,導致山西省的經濟波動幅度較大、抵御經濟波動影響的能力較差,降低了應對外部沖擊經濟后的調控能力。
三、對比分析結果的啟示
山西作為全國典型的能源性省份,一直以來為全國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從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能源發展戰略的變革來看,山西能源重化工業的發展,為我國北方的國民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工業化速度進一步加快,對煤炭等能源需求猛增。2007年山西實現GDP5733.4億元,達到2000年的2.4倍,山西煤、焦、冶金、電力等主導產業均為2000年的2倍以上。但以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基本標準人均一萬美元計算,山西經濟實現現代化的GDP規模還需增長5倍。但事實上,受資源、環境等因素的制約,這些產業再增長5倍的可能性極小,其中煤焦產業已接近量的極限,個別地市由于資源枯竭導致經濟增速下滑,有的地市由于高能耗、高污染受到“區域限批”,能源結構性超耗現象嚴重。因此在今后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山西主導產業的主要任務逐漸轉變為產能的集中及效益的提高,這也導致這些產業對GDP規模的作用將逐漸弱化,故向其它新興產業轉移成為山西今后發展的主要目標。山西省委、省政府從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出發,將“轉型發展”作為“三個發展”的首要目標,給山西這樣一個資源型省份宏觀調控指出了明確的目標。
與山西省的貿易依存度相比,全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受供給約束,而不是需求的約束。因此,當投資需求擴大,生產的急速擴張導致社會的總供給不足時,短期內最為有效緩解產品短缺的辦法就是進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供給不足,延長經濟波動的循環期。而山西省的貿易增長主要受到需求的影響,產業結構初級化,食品、紡織等輕工業產業明顯不足,無法通過自身市場來拉動經濟,為資源型產業的波動起到緩沖作用。經濟波動幅度大容易引發經濟和社會風險,宏觀管理的難度加大。
山西經濟波動幅度明顯大于全國經濟波動幅度的比對結果表現出,在以煤炭為主導的能源工業單一產業結構下,幾個主要支柱產業產生波動就足以導致整個省的經濟運行出現大起大落的波動狀況。相對于其他產業結構相對平衡的省份如山東、江蘇而言,山西省抵御宏觀經濟波動所產生的不良影響的能力較弱。根據世界市場經濟的經驗來看,雖然經濟體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因波動產生的副作用不可避免,但在經濟波動較大的地區,其經濟周期(衰退期)出現的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的問題更加嚴重和難以解決,政府在這類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也頗感吃力,難以迅速做出對策緩解問題。實際中,每個經濟體都是獨立的,其產生的周期性波動也會根據市場經濟的變化而變化,并非可根據人為需求而發生相關的改變。換句話說,這種波動的產生是必然的。所以調控經濟周期波動的目的并不是從根本上消除它,而是通過相應的經濟政策,影響這種周期性的波動,即適當減小其波動幅度,減慢其周期頻率,以及抑制因周期波動產生的社會經濟負效應,以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和社會和諧穩定。經濟波動又可以根據人為因素對其的影響大小,分為非自然波動和自然波動,上文所述經濟波動不可消除的意義在于自然波動不可避免,但政府可以通過制定適合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調整產業結構等相應措施,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因非自然的經濟波動導致的總體經濟情況的大起大落,以減少波動對公民社會發生災害性影響的可能性。這也是近年來中央政府提出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逐步完善,我國調節經濟波動的能力有所增強,從而使經濟波動有所減緩。這也凸顯出宏觀調控的重要性。就我國現階段整體經濟趨勢而言,政府宏觀調控的重點應該落在如何實現經濟的均衡、平穩發展和適度快速增長上,即如何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步入新世紀,我國經濟運行情況的波動呈現出新趨勢,因此新的調控政策也呼之欲出。現階段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于追求經濟波動的“高谷底、低峰值、長平臺”,即在經濟增長的回落階段時需要進行有效干預以避免回落過于明顯而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在經濟增長過快時要適當降低經濟增速以避免增長過猛所出現的高峰影響產業結構的平衡,并使總體經濟增長在適度擴張和適度收縮中保持一個相對長時期的穩定運行。這一點的成效已在第三個經濟周期的經濟運行數據中有充分的體現。改革開放后的第三個經濟周期的8年中,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一直保持在10.5%左右,上下波動幅度不多于2%,國民經濟平均增長率為9.7%,波動系數為0.11,這些數據進一步說明了全國的經濟增長在總體上已步入平穩和適度快速增長正確軌道上,而這一切與國家實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是密不可分的。
綜上所述,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合理運用宏觀調控政策調整產業布局、加大機制體制創新、逐步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努力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對于保持山西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步健康發展十分重要。
[1]李永升,劉浩.經濟周期理論與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系統考察.當代經濟,2009(7)
[2]詹新宇,孫晨正.經濟周期波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動態關系研究——以山西省為例[j].經濟問題,2011(7)
[3]山西統計年鑒.2013
(作者單位:太原市經濟信息中心研究室 山西太原 030002)
(責編:李雪)
F127
A
1004-4914(2014)09-0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