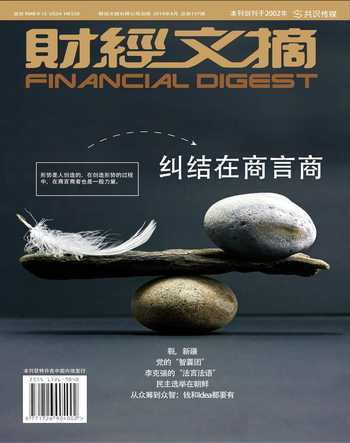美國文學里的中國隱喻
Helen G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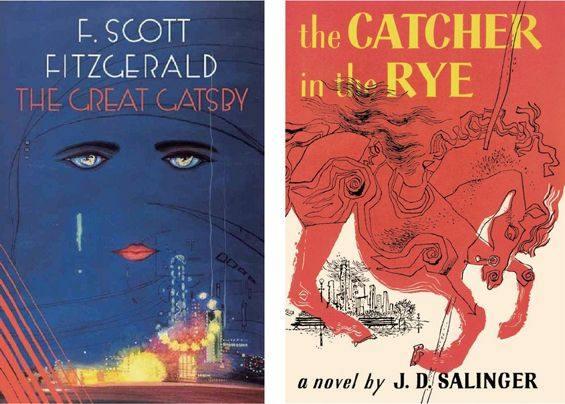
1963年冬,北京,中國剛從一場饑荒中恢復過來,厭惡了圍繞在周圍空洞的共產黨宣言的一群大學生決定開始一項危險而大膽的行動:談論西方文學。
在那些關于存在性焦慮、中產階級幻滅和特別是戰后美國社會中的叛逆等敘述中,學生們找到了靈魂家園。就如文學作品里他們的英雄一樣,學生們在一個同樣令人窒息的社會中日漸頹廢,“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愛,更沒有個性。”他們中的人回憶說:“《在路上》里面角色的精神世界是最接近我們的。”
從1979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已出版的外國文學中,美國文學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比如,在譯林出版社2012年的十大暢銷外國小說中,美國作家的作品就占了四本。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變化,美國文學的共鳴沒有減弱,而在每個時代改變和更新。
《麥田里的守望者》是一個關于青少年存在性焦慮的經典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攻擊保守社會觀念的小說與新開放中國的自由主義和反傳統的思潮共鳴;在九十年代早期,其憤世嫉俗和失望的語氣讓中國青年找到表達自己態度的方式。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和社會不平等賦予了這本書新的意義。《麥田里的守望者》主角霍爾頓和激烈競爭的上海高中里緊張的學生、不滿于老板的農民工、富二代的表達詭異地相似,他們都在為過有意義的生活而努力。
角色塑造以及講故事是美國文學散發持久吸引力的一個原因,因為它們“善于表達人類的情感”。
另一個可以共鳴的角色是蓋茨比——《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中的主人公。他野心勃勃并不懈進行自我創造的奇妙故事可以兼伴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范式。現實中,無數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有著蓋茨比的堅定。他們認為非常的手段才能獲得非常的成功,而蓋茨比的失敗源于他所處的環境而不是他個人的失敗,這些都預示著當代中國的物質主義和騷動。
蓋茨比所在的社會和中國社會之間有著相似之處,富人的浮華、權力的冷漠和愛的脆弱。一些讀者把蓋茨比和唐駿相比,給他貼上了“鳳凰男”的標簽。蓋茨比從出身卑微的人上升到平流層的高度,挑逗著中國奮斗者的勃勃野心,他的悲慘命運符合社會是多變的這一常識相符。他所處的時代,盡管法律禁止,但在民間享樂主義統治著社會。同樣在今天的中國,報紙上充滿了道德教育,現實中的人們卻失去了道德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