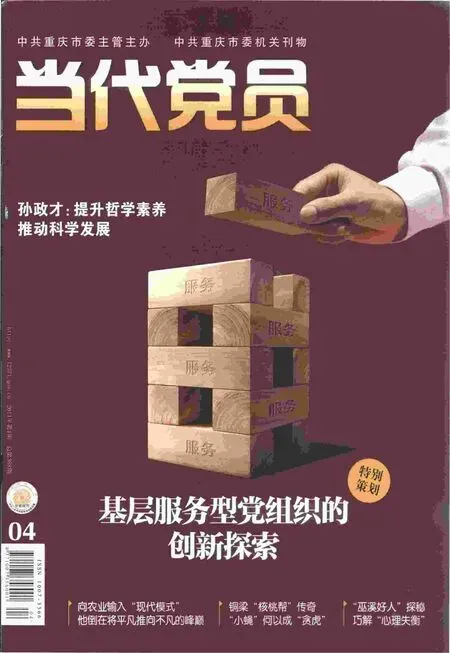一個“非遺”傳承樣本的三級跳
陸睿

2013年12月31日,巴南區接龍鎮。
鄉場外莊稼地里,53歲的唐佑倫身著天藍色對襟祥云衫,腳蹬圓口黑布鞋,手拿包銅竹嗩吶。
旁邊,九名漢子與他一般打扮,手中各持鑼、剎、笛、鼓、哨等樂器。
一陣風起,草葉飄搖。
“起!”唐佑倫迎風吆喝。
剎那間,樂器齊鳴——打擊音密集緊湊,如暴雨拍擊湖面;吹奏音昂揚激越,如鷂鷹翻飛長空。
傳承已逾百年的經典曲牌《將軍令》,響徹云霄。
唐佑倫的心緒,隨著古老樂曲穿越了久遠時空。
典型矛盾
1969年,唐佑倫八歲。
他有了一件新“耍事”——站在自家院壩里,看父親教徒弟接龍吹打。
在過去500年間,以接龍為核心的地區盛行著一種吹打藝術形式,被稱作“接龍吹打”。當地人但凡遇到婚喪嫁娶、年節喜慶,就會邀請樂班到家里演奏,以示破舊立新、祈福呈祥。
唐佑倫的父親,就是“唐家樂班”班主。
不演出的日子里,父親會率領樂班到院子里、田坎旁,研習《將軍令》《丫溪調》等傳統曲牌。
看著父親手拿戒尺教徒弟的威風模樣,唐佑倫漸生羨慕之情。
高中畢業后,他也加入了樂班。
2006年,接龍吹打成為全市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當時,全市評定了兩名國家級接龍吹打傳承人,唐佑倫就是其一。
捧回“金字招牌”,唐佑倫卻高興不起來。
30年前,唐家樂班成員上百。而近十年來,樂班人手開始不敷使用。
盛行五個世紀的接龍吹打,為何突現青黃不接?
“老樂手們不少已過世,剩下的年事已高,而年輕人又不愿干這行。”唐佑倫說。
年輕人為啥不愿意干?
“現在都喜歡請西式樂隊了——搞吹打找不到錢了,誰愿干?”唐佑倫說。
隊伍老化,藝術形式和市場脫節——一個傳統藝術傳承的典型矛盾,出現在接龍吹打面前。
如何解開矛盾?
政府包干
2007年7月,李長川覺得找到了人生方向。
他和15名少年加入了“接龍民間藝術專業班”。
對學習接龍吹打,李長川熱情高漲——每天放學后,他都堅持練習三個小時。
這些年輕人為何對接龍吹打產生了熱情?
“畢業后,我們能進入鎮政府藝術團,或者到小學當藝術老師。”李長川說。
這個“包辦就業”的專業班,是接龍吹打傳承的第一次探索。
“掙錢難,是造成接龍吹打傳承難的一大瓶頸。”接龍鎮文化站時任站長陳朝友說。
如何突破瓶頸?“讓傳承人能穩定就業。”陳朝友說。
于是,接龍鎮鎮政府聯合巴南區計算機職業學校舉辦了專業班,希望通過政府調控對接民間文藝市場。
然而,事與愿違。
2009年11月,李長川和同學們開始實習。
按計劃,他們將獲得政府提供的演出機會,并藉此掙錢糊口;政府還將提供每月300元的生活補貼。
可實習八個月,學員們僅參加了四五場演出,且出場費非常低。
“加上生活補貼,月收入不到600元。”李長川搖頭。
“事實證明,僅靠政府包干行不通。”一位鎮領導說,“專業班費用由鎮政府提供,每年支出近20萬元,長此以往,鎮財政難堪重負;同時,除少數政府活動外,我們很難提供穩定的演出需求。”
2010年7月,專業班三年培訓期滿,16名學員大都另謀他就。
李長川加入了一個民辦樂班,繼續堅持從事吹打。
“有夢,就有希望。”他說。
很快,希望真的來了。
回歸民間
2011年的一天,接龍鎮中心小學。
操場上,一群小學生整齊列隊,人手一支嗩吶。
隊列前,李長川一聲吆喝:“起!”
嗩吶聲起,聒噪雜亂。
李長川直搖頭。
“身要挺、氣要足!”
“雙吐要沉、滑音要準!”
…………
“起!”他又吆喝。
嗩吶聲復起,整齊了些。
這一年,巴南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推出了“接龍吹打進校園”行動,在全區40所中小學推廣接龍吹打課程。
李長川很快深受其益——他被當地小學聘為藝術教師,月薪3000元。
“傳統藝術究竟靠什么存續——是靠政府包干,還是別的?”“接龍民間藝術專業班”效果不佳,迫使巴南區相關部門不得不另尋出路。
經過深入分析,巴南區文廣新局給出了答案:回歸民間。
“傳統藝術形式是‘花,社會普及程度就是‘根——沒有群眾接受和認可,再優秀的藝術形式也不會有市場。要傳承傳統藝術瑰寶,建立全民普及體系至關重要。”巴南區文廣新局黨組書記、局長鄭麗娟說。
于是,巴南區推出三條突圍路徑——
首先,將接龍吹打、木洞山歌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編進教材,在全區中小學普及教學。
其次,從接龍吹打藝人中挑選74名骨干,牽頭負責相關“非遺”項目,給予資助并進行考核。
再次,以大學生“村官”為主體,到村和社區推廣吹打藝術,實現基層普及從“點”到“面”。
沿著三條路徑,一個覆蓋全區的接龍吹打推廣體系初步形成。
對接市場
2013年11月,唐佑倫被選舉為接龍吹打藝術團團長。
這個藝術團由鎮政府發起,全體吹打藝人參與,統籌當地吹打藝術培訓、創作和演出活動。
在接龍吹打發展史上,這是一種全新組織形式。
“長期以來,民間吹打能手分散在各個樂班,造成力量分散甚至內斗;現在,藝術團整合了這些資源,增強了承接大型高端演出的能力。”唐佑倫說。
這個藝術團,僅僅只是接龍吹打產業化的嘗試之一。
“‘非遺傳承的核心,就是深度對接民間演藝需求。”巴南區文廣新局副局長呂勇才說。
如何對接?
“走產業化道路,實現供給與需求的積極互動。”呂勇才說。
產業化道路,如何走?巴南區給出了三個答案——
一是健全不同層次的演出能力。
“以吹打藝術團為核心,傳統吹打樂班為基礎,我們健全了高中低不同層級的演出體系,具備了對接細分市場的能力。”呂勇才說。
二是建立吹打衍生產業。
“我們在接龍鎮自力村建立了嗩吶生產基地,年產值14萬元。”接龍鎮黨委書記李萍說。
三是推動接龍吹打從文化名片向旅游名片轉變。
“近兩年,接龍吹打參加國家、市、區縣等各級演出近百次——每次出場,都堪稱驚艷全場。”呂勇才說。
“巴南區接龍吹打,已經具備了申報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潛力。”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秘書長烏丙安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