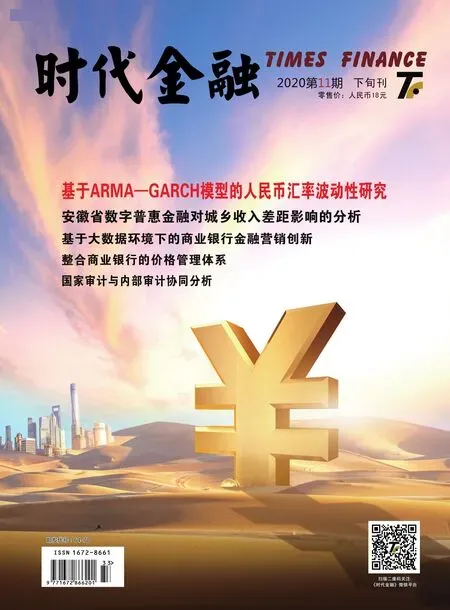影子銀行:風險與未來
一、定義
“影子銀行”最初是源自美國,被定義為具備近似于銀行效用,卻沒有國家信用擔保支持的金融中介機構。銀行由于獲得了政府的支持,促使它們越發的向高風險高回報的產品偏移。作為國家金融體系的核心,銀行有足夠的影響力來迫使國家用納稅人的錢為自己的失誤負責。因此,政府對于銀行采取的是監管與支持平行的手段,這樣才有了金融監管部門。然而為了繞開監管,解放自己的盈利能力,銀行將某些業務移交到了監管部門無法顧及的行業,從而誕生了現在的“影子銀行”。
作為一個中間體系,影子銀行也被劃分為三大板塊:信用中介、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這三個功能互相連接,形成了一條業務鏈,打通了儲蓄與借貸之間的聯系,扮演著一個金融中介的角色。相比美國,由于我國的資產證券化還不成熟,影子銀行仍然只是停留在雛形階段——為了規避利率的管制。在中國體系中,商業銀行以龐大的資源優勢,主導著影子銀行,并將現持有的資源轉移出受限的傳統存貸系統,從而達到規避監管的效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子銀行與傳統商業銀行共享了信用資源。
二、風險
自從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開始,金融界對于“影子銀行”的評價褒貶不一,并且普遍都持有消極態度。一般來說,所謂“影子”,它的風險源自于兩個層面:系統性和監管套利兩種風險。就系統性風險而言,由于影子銀行與傳統商業銀行錯綜復雜的關系,同時又結合影子銀行過高的杠桿率,潛在的違約風險會連帶的波及到傳統的金融體系中,造成信貸風險的轉移,而這種負面的影響會在高杠桿的催化下,放大內在的破壞力,最終引發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監管套利風險則偏重于規避監管規則,以相對傳統存貸更低的融資成本來獲取資金,擴張規模。監管的空置,低額的準備金等一系列因素提升了杠桿率,膨脹了社會信貸的體積。
隨著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樓市和經濟增長都趨于下降,作為資產抵押的影子銀行業務確實存在的極大的違約風險。樓價的下調,將導致抵押品的價值流失,投資者和企業都可能面臨重大的經濟損失,金融中介將要面對的風險也隨著凸顯。很多人聯想到美國的次貸危機,擔憂中國的影子銀行也會讓中國經濟重蹈美國的覆轍。然而,就拿中國的信托和美國的次級借貸進行對比,他們之間有很多區別。同樣作為高風險高回報的理財產品,美國的次級債投資群體大多是金融機構,而在中國,大部分投資者是以個人身份參與。當投資資產價值下滑時,中國與美國的投資者都可能在遭受損失的情況下進行贖回操作,可是當進入去杠桿化階段時,歧義就顯現了。當金融機構遭遇財務損失時,資產的變賣可能是唯一可以用來彌補負債所帶來的壓力。可是在中國,理財的投資大部分源自于儲蓄資金,不存在杠桿投資,所以拋售的幾率會很小。
再者,次級貸款本身的風險就高于中國的信托。原則上,當房價停止上漲的時候,次級債就可能演變為不良貸款,也就是說次貸的崩潰的導火索是時間。反之,信托的風險取決于資產價格的波動,而這些主要牽制于市場和政策。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他們的整個金融體系癱瘓,透析出其資產負債表風險的影響。在中國式的金融機構和體系下,信托的崩盤可能會造成家庭損失,但應該不會對傳統銀行體系造成直接沖擊。
三、是非
我們判斷影子銀行的是非對錯,需要將現代的金融理論和客觀的規律結合起來分析和研究。在價格面前,資產的高度敏感和負債的欠敏感會促使凈值被市場的波動而影響。當資產價值平穩上漲時,凈值會呈現增長趨勢(資產效益高于負債利息)。反之,當價格下調時,資產損失加劇,凈值逐降,從而可能導致財務杠桿的飆升。綜上,資產價格上升,凈值、負債和消費都會呈現增長趨勢,儲蓄會相應下降,儲蓄率也會系統性下調。反之,財務杠桿激增,金融風險劇增。影子銀行成為了信用總量放大和收縮的誘因。
影子銀行規模之所以擴張得如此之快,歸功于它對于金融體系改革和進步所作出的積極貢獻。首先,影子銀行顛覆了傳統金融單位的收益和利潤觀念。極少的準備金規定大幅度的降低了融資所需要的成本,增強了收益率。其次,由于影子銀行靈活和復雜的聯系網絡,一方面提升了金融機構的競爭意識,優化金融系統的服務效率。此外,復雜的業務鏈可以促使金融單位間的合作,拓寬金融領域與其他行業的業務交集。作為投資者,影子銀行提供了高收益的投資渠道,例如理財產品,基金。與此同時,高風險的影子銀行體系可以更好的培養和鍛煉投資者的風險意識。
從融資角度分析,影子銀行填補了傳統商業銀行之外的融資業務,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無門的窘境。對于欠發展的小規模中小企業而言,由于短期很難提供可信賴的抵押資產或者信用擔保,因此傳統的銀行體系無法對類似單位提供借貸支持。影子銀行作為靈活的金融中介體系,它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多元化的融資服務。同時,通過對借貸者的盡職調查,影子銀行可以收集到更詳細的市場資料進行分析。
四、未來方向
綜合來看,中國的影子銀行并非流傳中的“二次次貸”與“龐氏騙局”。當存貸等傳統業務統治中國商業銀行時,其他的金融單位在資源劣勢的環境下發展創新業務,運營和體系改革的呼聲連綿不絕。隨著銀行表外資產管理業務的逐步成熟,直接融資也逐漸進入發展的快軌。假如過分的強調表外風險,夸張影子銀行發展的負面影響,現代的金融體系很有可能會停滯在曾經的運營模式。創新與監管之間的博弈長久以來都難以權衡,可是如果在一邊擠兌傳統運營模式的商業銀行同時,一邊又干涉新勢力的發展,中國商業銀行的成長路將變得迂回曲折,進退兩難。
對于影子銀行體系,中國宏觀金融監管機構應該適應創新機制的發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首先,應該致力于增強對于影子銀行信息的捕捉能力,增強其信息的透明度。當政府有足夠的能力跟蹤影子銀行信息的時候,才能在影子杠桿率飆升之前,監管部門對其及時進行調整,縮小風險的波及面。其次,貨幣政策需要從數量政策轉變成價格政策。影子銀行是為了規避傳統的負債和資產等數量政策而產生的。再者,對于“監管”的誤區往往領著部門徘徊于巨大成本和命令禁止兩種極端,政府應該適當的讓市場自身去監管市場。對于創新頻出的新型金融體系,監管部門很難通過一己之力去監管多元化的理財業務。
作者簡介:張杰(1988-),男,漢族,湖北孝感人,任職于金譽投資擔保公司,研究方向:金融風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