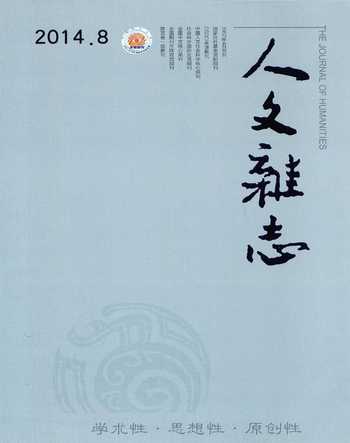清代中俄恰克圖貿易的歷史作用
豐若非 燕紅忠
內容提要 有清一代,中俄恰克圖貿易是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章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指出,中俄恰克圖貿易不僅優化了中俄雙方的貿易結構,推動相關產業及邊貿城市迅速發展,更為關鍵的是,其已成為以恰克圖為中心的中、俄、蒙國際性區域市場得以良好運行的一股重要力量。
關鍵詞 清代恰克圖貿易作用
〔中圖分類號〕K2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8-0092-08
清代中俄恰克圖邊關互市在中俄關系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尤其是自乾隆間,“中俄商務集中于恰克圖,遂日漸繁盛,蔚為兩國通商之咽喉;與廣東之壟斷貿易,可謂南北輝映也。”①作為清代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重要組成部分,中俄恰克圖貿易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俄兩國、特別是兩國邊境地區的商業發展,有力推動部分邊貿城市的興起、繁榮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促使以恰克圖為中心的中、俄、蒙國際性區域市場得以良好運行。有關中俄恰克圖貿易的相關研究,囿于資料限制,以往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定性敘述,定量分析的成果則稍顯薄弱。近年來,隨著部分有關中俄貿易的俄文材料逐漸被國內學者翻譯成中文,②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資料的進一步整理與利用,為我們繼續深入而客觀地分析和評價中俄恰克圖貿易提供了更為豐富且具有可信力的史料基礎。本文將主要運用其中的部分譯著材料以及北部邊疆的關稅檔案,從貿易結構的變更、產業及邊貿城市的發展以及在國際性區域市場中的地位等角度對清代中俄恰克圖貿易的歷史作用予以相關量化闡釋。
一、貿易結構的變更
在中俄恰克圖貿易發展過程中,由于金銀被禁止在恰克圖市場當作貨幣使用,因此在雙方交易中,市場中的暢銷貨長期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角色,并以其確定各種商品的價值。發揮這種作用的貨物,起初是中國的棉布(一種黃色土布,俄商稱之為“南京小土布”),之后則是茶葉,這種演變過程印證了中國出口俄國貨物結構的變更及優化。
在整個18世紀,俄國進口的中國貨物一直以中國棉布和絲綢為大宗,中國的棉織品不僅在西伯利亞,而且在俄國的歐洲部分也得到了廣泛普及。[俄]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系史》,宿豐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92頁。土布甚至在中俄易貨貿易中充當了價值單位:每件商品都按被換成的土布包數或塊數來估價。③④[俄]特魯謝維奇:《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系》,徐東輝、譚萍譯,岳麓書社,2010年,第152、152、150頁。俄國人對中國棉布的重視,也激發了中國棉布生產者和批發商的積極性。18世紀中葉,恰克圖市場出現的織有俄國雙頭鷹徽記的中國布匹,就是中國商人為進一步擴大產品銷量而采取的一種手段,恰克圖商人同手工工場也保持著長期訂貨。1751年,棉布料已占恰克圖總交易量的595%(257,000盧布),而1759~1761年則占60.4%(509,000盧布)。此外,在1762~1785年間,大布進口數量增加了約4倍多(由70,000塊增加到380,000塊),其他布料也增加了1倍。總而言之,從1760年至18世紀末,棉布料的進口價值由509,000盧布增加到1,601,000盧布,增加了2倍多。③與此同時,絲織品在俄國的進口額卻在逐年下降。1751年,其占俄國進口中國總額的235%,1759~1761年則下降為205%。雖然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由于宮廷奢侈,俄國對中國絲綢料子進口額出現了真正增加,但其在中國貨進口總額的比重卻進一步下降為124%。④
俟至19世紀,中國輸往俄國的貨物結構又出現新的變化。表1列出了19世紀前50年中國輸往俄國的5種主要貨物額。其中,棉織品和茶兩者所占的比例之和達到5種貨物額總和的95%以上,成為中國在恰克圖貿易中最主要的貨物。圖1呈現出5種貨物所占份額在19世紀上半葉的具體變化趨勢。棉織品和茶所代表的兩條曲線在圖中的變化最為明顯,分別呈現出逐漸下降和不斷上升的走勢,且基本呈對稱分布。從具體數值來看,棉織品的輸出額僅在1802~1807年間略高于茶的輸出額,其余時間段內均未超過茶的輸出額,且二者間的差距愈來愈大。
圖1
對于茶而言,在18世紀末以前的俄國市場上,消費中國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亞人。輸俄茶葉以磚茶為主,西伯利亞人混以肉末、奶油和鹽飲用。19世紀,由于需求日增,市場廣闊,茶葉逐漸成為中俄恰克圖貿易的專寵物,并逐漸取代棉布,成為衡量商品價值的等價物。“磚茶在外貝加爾邊區的一般居民當中飲用極廣,極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當錢用。”在西伯利亞的布里雅特人等土著民中,“在出賣貨物時,寧愿要磚茶不要錢,因為他確信,在任何地點他都能以磚茶代替錢用。”[俄]瓦西里·帕爾申:《外貝加爾邊區紀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俄語編譯組譯,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47頁。
表2顯示,1755~1850年之間,除1792年由于恰克圖貿易閉市造成的茶葉貿易額有所下降之外,中國輸俄茶葉量每年都處在增長之中。最明顯的變化是,1802年俄國輸入茶葉45,032普特,③[俄]阿·科爾薩克:《俄中商貿關系史述》,米鎮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72-73、200頁。1850年即上漲到296,618普特,③增加了約56倍,其價值也已達到6,527,000盧布,約占俄國輸入商品總值的94%。[蘇]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貿易經濟關系史(1917年前)》,宿豐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31頁。更為具體的記載是:“(俄國)在道光十年(1830年)買去(茶葉)563,440磅,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買去6,461,000磅,皆系黑茶。由喀(恰)克圖旱路運至擔色(托木斯克),再由水旱二路分運娜阿額羅(下哥羅德)。”魏源:《海國圖志》卷49,“澳門月報二·論茶葉”。此外,1837~1839年每年茶葉輸入(俄國)數量,平均為8,071,880俄磅,約值800萬盧布左右。1838年,除大小茶磚71,950塊及60,430塊外,還有茶葉43,070箱(每箱100磅)運至恰克圖交易。⑦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1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664、664-665頁。此外,茶葉也逐漸成為俄商賺錢的重要渠道。19世紀上半葉,俄商以700萬元在恰克圖購買的中國茶葉,可在下哥羅德集市上賣得1,800萬元,⑦足見俄商在恰克圖貿易中獲利之豐厚。有人為此斷言:“恰克圖貿易是俄國獲利最大的貿易,大概俄國人所從事的任何一種貿易都無法與它相比。”[蘇]卡巴諾夫:《黑龍江問題》,姜延柞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頁。
中俄恰克圖貿易不僅改變了中國輸俄的貨物結構,其對俄國輸華貨物結構的影響亦同樣意義深遠。表3列出了19世紀上半葉俄國輸華重要貨物的貨值及其所占比例。顯而易見,從貨物結構來看,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的貨物結構彰顯出兩國顯著而獨特的區位優勢,具有強烈的互補性。也就是說,俄國更加注重本國毛皮類以及毛織品等耐寒、御寒貨物的輸出,而中國的茶葉、絲綢則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俄國人對于飲食健康以及流行時尚的追求。當然,為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對貿易過程的客觀要求,俄國輸華貨物的產品結構在半個世紀內也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
圖2顯示,在19世紀初的20年內,毛皮類產品在各種貨物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且一直保持上升趨勢。毛皮貿易也給俄商帶來巨大利潤,海貍皮在堪察加售價為:一等每張60盧布,二等每張40盧布,三等每張25盧布。但是,這些貨物在恰克圖市場上的標價卻為90~100盧布,有的甚至高達140盧布。[俄]阿·科爾薩克:《俄中商貿關系史述》,米鎮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2頁。直到1820~1830年間,毛皮類產品所占份額開始出現下滑趨勢,代之而起的毛織品與棉織品輸送額則逐漸增多,且毛織品表現得更勝一籌。這種貿易現象真實反映出當時俄國工業的發展狀況。據統計,僅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咸豐元年(1851年)之間,俄國輸華工業品就占其工業品出口總額的477%。[蘇]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貿易經濟關系史(1917年前)》,宿豐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93頁。
圖2
二、相關產業與邊貿城市的發展
在中俄雙方貿易結構得到不斷變更的前提下,中俄恰克圖貿易也促使與貿易相關的部分產業發生了積極轉變。具體而言,廣闊的茶葉市場對商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豐厚的利潤,許多商人(尤其是晉商)分赴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臨汀,湖北崇陽、蒲圻、通城等地辦茶(后期主要在湖北羊樓洞和相鄰的湖南羊樓司),這直接推動了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植茶業的發展。“漢口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多由水路經洞庭湖入長江,然后匯集漢口。由于運輸方便和‘紅茶利興的刺激,平江縣凡山谷間閑地向種紅薯之外,悉以種茶;瀏陽以素植麻,攏而植茶。茶區面積擴大了,茶莊林立,植茶業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就平江而言,上自長壽、下至西鄉之晉坑浯口,茶莊數十所,揀茶者不下二萬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囂擁擠。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的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光緒初年,每年都有茶莊七八十家……兩湖茶區面積急劇擴展。到1871年,幾乎較十年前增加了50%。”同治朝《平江縣志》第20卷,第3頁;參見陳鈞:《十九世紀沙俄對兩湖茶葉的掠奪》,《江漢論壇》1981年第3期。
山西茶商開設制茶工廠,既推動了當地農民以追求價值為目的的茶葉生產,又對其他手工業生產產生了重要影響。磚茶要用紙包裝,裝箱離不開竹木箱,這必然帶動當地造紙、木竹器等手工業的發展。蒲圻縣南山之東,有一地方名曰“紙棚,左有洞,右有泉,其居人曰鄭氏。凡40余戶,除數耕者外,悉以造紙為業”。“治棚下者,約百余人,每歲值可獲五六千金。凡此數十戶,一切食用皆取給于此”。道光《蒲圻縣志》卷4《風俗》。崇陽縣也因為茶葉生產發展,帶動了“木工、錫工、竹工、漆工”等行業的不斷發展。同治《崇陽縣志》卷4《物產》。
與此同時,中國市場的巨大利潤也刺激了俄商極大的興趣。1733年,西伯利亞的第一家制呢廠開工。在18世紀90年代,這家工廠在中國對俄國呢絨需求擴大的拉動下,產品產量開始迅速增長。1790~1797年間,該廠共生產32,200俄尺呢絨,其中大部分被運往恰克圖。⑤[蘇]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貿易經濟關系史(1917年前)》,宿豐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90、200頁。另外,俄國工業企業的數量,從1804年的2,423家增加到1825年的5,261家和1854年的9,994家。在工業企業做工的工人數量也同樣增加。1804年工人總數為22.48萬人,1825年為34.06萬人,而到1860年則增至86萬人。⑤
中俄恰克圖貿易對我國北部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力促進了草原、大漠城鎮的興起和交通運輸路線的開拓。邊境地區除恰克圖外,塔爾巴哈臺、伊犁均被開辟為中俄互市的新商埠;而國內的貿易城鎮張家口、歸化城、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不僅是大漠南北的交通要道和旅蒙商人活動的據點,而且也成為邊境貿易輸出入商品的集散地和供給線。
1728~1762年間,俄國國家貿易商隊自開辟恰克圖口岸入境,經庫倫、張家口(或歸化至張家口)來京貿易的商路后,“張家口買賣城可以說是中國對俄貿易的集中點,幾乎全部俄國呢絨和各種絨布以及俄國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運張家口買賣城的貨棧,然后批發給下堡,最后再運到中國本土”。[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劉漢明等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0頁。位于張家口的商號在雍正年間已增加到90余家,乾隆后期約有190余家,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達到230余家。袁森坡:《康雍乾經營與開發北疆》,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第528頁。其中,專作磚茶貿易的大泉玉、祥發永、廣全喜、恒隆廣、大升玉、公合泉等商號每年運往庫倫、恰克圖、科布多等地的磚茶多達約40萬箱。盧明輝:《清代北部邊疆民族經濟發展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0頁。當時的外國人評論“像張家口這種極為活躍的商業往來,甚至在中國本部也是罕見”。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1291-1292頁。
伴隨北部邊疆商貿活動的不斷拓展,諸多商人在歸化城開始從事各種貿易經營活動。雍正五年(1720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后,歸化城日用百貨的貿易范圍逐漸擴及于俄國境內,其中茶葉、大黃、煙草為輸俄大宗。盧明輝:《恰克圖買賣城中俄邊境貿易的興衰變化》,《經濟·社會》1990年第4期。同治六年(1867年),大盛魁聯合歸化城的商民,呈由綏遠將軍裕瑞、歸化城副都統桂成等奏準,由恰克圖假道與西洋通商。從此,歸化城的商號活躍在中俄邊境,輸出入各種中俄商品。《旅蒙商大盛魁》,《內蒙古文史資料》(12),第48-49頁。大盛魁更以自己的駱駝隊馱運茶葉等貨深入俄國內地銷售,取得厚利。同時也進口俄產的羽翎緞、羽毛紗、大絨、毛毯和俄國標布、鏡表、銅器等,大部分運到歸化城,由其小號“天順泰”設有專柜展售。《旅蒙商大盛魁》,《內蒙古文史資料》(12),第49-50頁。
另外,作為連接中國與俄國邊境貿易城市恰克圖——買賣城交通樞紐的庫倫,至清代后期,共有內地旅蒙商號約400余家,約10萬人,其中有50家為資金雄厚、貿易興隆的大商號。這些草原城鎮的興起及邊境貿易的擴大,對于我國北部廣大牧區經濟的開發,對于畜牧業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聯結乃至轉化,對于游牧民族生活條件的改善,都有著積極作用。
三、對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積極影響
伴隨中俄恰克圖貿易的不斷發展,諸多商業機構開始以恰克圖為據點不斷向俄國腹地輻射,不僅鞏固了以恰克圖為中心的商業區域的繁榮,也促使清代北部邊疆商品流通不斷向縱深發展。
清人何秋濤曾提到:“蓋外國人初同內地民人于市集交易,一切惟恐見笑,故其辭色似少遜順。經恰克圖司員諭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羅斯歡喜感激,信睦尤著。所有恰克圖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前往易換各色皮張、氈片等物。初立時,商民俗尚儉樸,故多獲利。”何秋濤:《朔方備乘》卷46《考訂綏服紀略》。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山西商人在買賣城的商戶已有140多家,有400多常住人口,其中資本較厚者60余家,稱為票商;另有散商(又稱朋商)80余家依附于票商。在眾多的商號中,涌現出幾大家,首推曹氏,次為常氏,還有喬氏、牛氏等。葛賢惠:《商路漫漫五百年——晉商與傳統文化》,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0-71頁。如太谷曹家“錦泰亨”將經營的主要商品曲綢用駝、騾運往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等地經銷,每年約可運銷12,000余匹,價值白銀36萬余兩。當時做此項生意的商號有一二十家,而“錦泰亨”是資本最雄厚的一家。“錦泰亨”在運銷曲綢的同時還兼運各地所產的花素綢、緞、綾、羅、絹、紗以及半兩茶等,回頭則運銷俄國的金沙、呢絨、哈喇、俄毯等貨。聶昌麟:《太谷曹家商業資本興衰注》,載《山西文史資料》(12),1965年,第161-162頁。又如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通事”是古代北方人對翻譯人員的稱呼。“通事行”是清代對會說蒙古語、專門從事對蒙古和對俄國貿易之商行的稱呼。“大盛魁”有職工6,000~7,000人,駱駝16,000~20,000頭,其活動范圍包括喀爾喀四大部落、唐努烏梁海、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庫倫、恰克圖、內蒙古各盟旗和新疆烏魯木齊、庫車、伊犁、塔爾巴哈臺以及俄國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由此可見,中俄恰克圖貿易的確帶動了諸多商號貿易活動范圍的擴展,而這勢必為清代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繁榮注入不竭動力。
如前所述,被稱為“東口”的張家口是清代中俄大宗茶葉貿易直接相關的關口,而與之對應的“西口”殺虎口和歸化城在北部邊疆也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事實上,商人正是通過這兩個關口同時兼以與新疆、蒙古地區的貿易。在此,我們通過清代殺虎口的實征關稅,來管窺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波動狀況。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表4所呈現的143個殺虎口年征關稅并非表現為完整且無間斷的序列,但這些數據卻占據了所考察的182年的長時間段內大約4/5的數據,因此完全能夠用以表現相應的貿易活動波動狀況。
圖3繪制出從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之間長達182年的時間段內的殺虎口實征關稅的變化趨勢圖,具體表現為:從乾隆年間輕微波動中的逐漸上漲至咸豐四年之前,始終保持穩定的高位運行;排除咸豐四年至八年之間的關稅下降及恢復階段,同治年間再次表現為較為穩定的態勢;光緒年間則出現了較為劇烈的波動,但往往能夠回到正常的關稅水平。且不論殺虎口關稅出現明顯下降及劇烈波動的具體原因,需要關注的是維持穩定高位運行的嘉道年間,其背后必定會對應著一個較為穩定的商品流通市場。以往在談到稅關衰落的時候,一般以鴉片戰爭為界,并強調“實際上榷關稅收的減少早在嘉道年間就顯露出來了”,主要表現為歷年缺額的淮安、滸墅、揚州、臨清以及間有缺額的九江、南新、鳳陽、蕪湖、西新等稅關在核減其盈余數額,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5-256頁。但殺虎口的實征關稅卻證明其與國內其他多個稅關的稅收變化趨勢并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足見其當時貿易活動的特殊性。
相比之下,由于各種客觀原因所導致的中俄恰克圖貿易逐漸衰退,卻直接影響與殺虎口并行的“東口”張家口自同治初年開始就出現了關稅大幅削減的情況。“伏查張家口稅務向以南茶并恰克圖皮毛等貨物為出入兩大宗,次則進口牲畜。均系內地商賈往來興販,是以從前稅課豐旺。及至俄國通商后,所有大宗查獲具有俄商自行販運,悉皆照章免稅,內地商賈漸多歇業,因之每歲額征均屬短絀。”軍機處檔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編號124086、131046、132777、138403。事實上,中俄于同治元年(1862年)簽訂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于同治元年二月四日在北京簽訂,共21款,最重要的是第一款“兩國邊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稅”等。參見《清初及中期對外交涉條約輯》,國風出版社,1964年,同治條約。俄商自此可自行深入中國內地采辦,而同樣的商品經由華商卻與從前一樣課稅,競爭力大不如前,華商自然裹足不前,關卡能得到的稅收自然遽減。尤其是同治八年(1869年)《改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改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于同治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北京簽訂,共22款。參見《清初及中期對外交涉條約輯》,國風出版社,1964年,同治條約。允許俄商在蒙古地區的銷售全部免稅,更讓張家口的稅課雪上加霜。與此同時,殺虎口關雖不如張家口關的壯麗,清晚期也不是個涉外口岸,但對照張家口因外在大環境的變遷而大起大落,殺虎口稅關的稅收相對算是較為持續而穩定的。
上述史實清晰地表明:中俄恰克圖貿易的確構成了清代中國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有力推動了包括蒙漢貿易在內的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的繁榮,而北部邊疆商品流通不斷壯大在一定程度上也積極推動以恰克圖為中心的國際性區域市場得到不斷成熟與擴張。顯而易見,這個相互影響的大市場內部即便出現局部危機,也不會對整個北部邊疆商品流通產生災難性的打擊。
作者單位:豐若非,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燕紅忠,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責任編輯:黃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