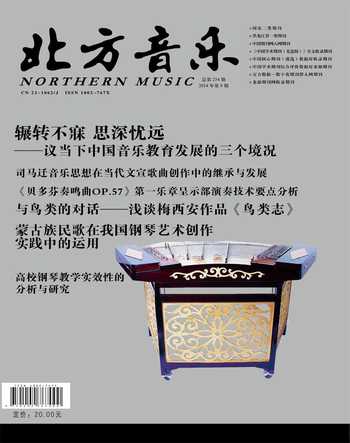漢語歌曲演唱中的字腔關系
回微
【摘要】漢語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豐富多彩的聲、韻、調、情、美,因此也極富音樂性,也因此而存在漢語歌唱中的變化多端的“字”、“腔”關系問題。通過對不同作品中的不同字腔關系的透析,漢語歌唱中每每會相對地出現:字正腔圓;字不正腔圓;字正腔不圓;字不正腔不圓等等復雜的實情。
【關鍵詞】漢語歌唱;字腔關系;字正腔圓;字不正腔圓
漢語歌曲演唱中的字腔關系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歌唱界孜孜以求的學術課題,老生常談即“字正腔圓”。其實在漢語藝術歌曲演唱中,由于漢語作為曲文,有著“聲、韻、調、情、美”的千變萬化,便絕非籠統的“字正腔圓”所涵蓋。中國傳統歌唱理論中的所謂“字”、“腔”,其“字”并非僅指書面上的漢字,更包括從歌唱角度所指的“四聲”、“五音”、“四呼”、“十三轍”……其“腔”主要指(因四)聲(而產生的音樂)腔(調)。更包括咬字中的“腔”、單字的
行腔、字后的拖腔。現代聲樂藝術已進入多元化的時代,故對漢語藝術歌曲演唱中的字腔關系,似乎也應另眼看待。即在“字正腔圓”之外,還常見“字不正腔圓”;“字正腔不圓”;“字不正腔不圓”;“字歪腔破”……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就有“陰、陽、上、去”四種調值。
一、“字正腔圓”的有意識追求
在聲樂作品的創作和演唱過程中,很多字和腔的流動都是相協調的。字的“正”與腔的“圓”都是比較順暢的。
在漢語普通話的四個聲調中,聲調變化最大的要數“上聲”字,它是先降后升,有一個曲折回旋的變化。“上聲”是“2-1-2-4”走勢,屬“三聲”,又稱“折調”——從“2”降到“1”后,再經過“2”升至“4”級(漢語字調被學界共識為五級分制)。在漢語音韻學大師趙元任先生所創經典實驗性歌曲名作《賣布謠》中,對曲調與字音的聲、韻、調、情、美等的關系的處理極佳。他根據漢語音律來處理好樂調與字調(字腔)關系,從而達到“字正”的創作歌曲典范。如其間的“買、賣“二字,均為m-ai二個音素。字頭m是雙唇濁鼻音(閉唇、空腔)、字腹a是舌前不圓唇半低元音(半開腔)、韻尾i是舌前不圓唇高元音(開腔),字的運動狀態從閉到開再到半開,但語調不同,“買”為折調的上聲,“賣”為高降(51)調的去聲,如二字所配旋律處理不好,就容易產生倒字,“買”、“賣”不分,從而導致詞義不清。“買”字均配用兩個上行三度的八分音符來與“賣”字相區別,從而使詞義清晰、一聽了然。對語調和樂調關系的認識和成功實踐,給人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中國歌曲創作典范。
再如歌曲《黃河怨》中的“就在岸上住”,其五個全是“去聲”字。“去聲”字的聲調走勢為“5-1”,此類“5”直降到“1”的高降調,一般發音短促,旋律大都向下滑行,有自上向下直滑的動勢。從字的“四呼”、“五音”上來看,“就”字的口型因韻尾ou而“撮唇”,而口腔內部相對較空,與“在”字相連時,前字的韻尾ou與后字的字頭z是從閉到開的運動狀態,此時聲腔不易行圓,會有短暫的噪音;但轉換到“在”字的字腹和字尾上時,口腔的開口度逐漸變大,使得聲腔再一次圓響;而與“岸”字的銜接時,因為其口腔的開度本身較大的原因,故此時不但口腔的開度可保持,且對歌曲的“情態”體現上也是很有幫助的;接下去的“上”字與“住”字的銜接,因為前字的韻尾(ang——傾向閉口)與后字的字頭(zhl的閉口,故可相對減少口腔的運動負擔。較容易使行腔暢達。從“四聲”上來看這五個“去聲”字中只有“就”與“住”兩個字符合降抑字調的特點,其他三個字之中“在”字是降升,基本上屬于降抑平升沒有超過起音“6-la”,而“岸”字與“上”字則是上揚接近陽平字,但聯系上下曲文并不太影響詞義的明晰。如果硬要把五個“去聲”字的曲文,都一律按降抑的曲調,必然會使得曲調呆板,沒有起伏變化。何況,從作為載體的曲調與曲文關系的角度來考量,旋律的“腔圓”必然是唱家的首選,之后方考慮“字正”。更何況“字正”的細微末節,多要靠歌者在二度創作中去微調,這便是一、二度創作中的分工合作。去聲字既可以低唱也可以高唱,要根據歌詞具體內容以及字在詞組與句子中的旋律音區地位而定。五個全是“去聲”字的曲文,作曲家不可能也不會用曲調去跟著曲文去亦步亦趨——曲調死跟著漢語而自然音調化,因為即使是平時說話,五個全是“去聲”的字,話說起來,因人、因時、因地、因情……也是會有諸多變化的。盡管曲調是曲文的載體,但曲調也本該是有體的——歌曲藝術。
二、“字不正腔圓”的有意識微調
在漢語歌曲演唱的二度創作過程中,也經常會發現“字不正”的問題,這其中包括演唱者在咬字吐字時的字頭不清、字腹不引長、收聲不歸韻。曲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因顧及旋律旋法必然會產生語調和樂調不一致所造成的“倒字”現象。而演唱中的“字不正”現象嚴格來說,主要是指漢字語調與音樂腔調未能和諧。在這種“字不正”的情況下要達到“腔圓”,演唱者在二度創作中就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有意識微調。
在漢字的四聲中,陰平字由于處于其五級調值里的高位,且無升降,始終保持平衡狀態其發聲特點,故一般并無嚴格意義上的“字不正”現象,只存在旋律走向上時值的長短、相對音域內的音區高低等變化。由此歌者在演唱陰平字時,可以相對忽略其四聲的“正”或“不正”,而把注意力重點放在字的“發聲”、“引腹”、“收聲歸韻”——口腔形態變化的規律與運作的方法方面,做到相對準確的咬字、吐字,從而解決雖“字不正”但“腔可圓”兩難問題。
如歌曲《黃河頌》中“啊!黃河!啊!黃河!”與“祖國頌”中的“一條大河”中的“啊”和“一”,這類字沒有字頭和字尾,母音就是它的字腹。歌唱時在發“啊”字的時候只要把母音平直送出,口腔打開,唇呈自然狀態即可;發“一”字時,口腔要適當打開些,嘴角展開,舌前部高抬,舌尖抵下齒背,唇形呈扁平狀。
陽平字的“字不正”情況較之陰平字要復雜的多,或腔句前,或腔句中,或腔句尾,由于陽平字在腔句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加之它與陰平字的相類似之處(都屬平聲),微調的方法是比較具體的。
如歌曲《紅豆詞》中“流不斷的綠水悠悠”,“流”字為陽平字,由l-i-ou三個音素組成,字頭1是舌尖中濁邊音(閉腔)、介母i是舌前不圓唇高元音(半開腔)、韻尾ou為舌后圓唇高元音(撮口、半開腔),這三個音素組合在一起時口腔的運動狀態從閉到半開再到大半開,運動幅度不算大;再看字的音高為“3-mi”,與它后續的“的”字的音高相等——處于局部高位,加之它的時值短,就好象是把“流”唱成了“溜”,照理說應該算是“字不正”(“倒字”)現象。但在實際演唱過程當中既可以把它作“陽平高唱”,也可以把“流”字前面加以上滑的裝飾——這涉及到歌者的案頭工作。但不管怎樣唱,樂調的連貫和圓滑不應被破壞,所以即使是“字不正”也要使“腔圓”。漢語歌唱中“字不正”而“腔圓”司空見慣,實在無須大驚小怪,但要盡量注意微調到位,這畢竟是歌唱藝術……同樣的一組漢字曲文,即使變為話劇臺詞、詩歌朗誦與平時說話,因情之所至,也絕非千篇一律,而是千變萬化的。所以聲樂作品中的此類“字不正”,為了使“腔圓”,似把本屬折調的上聲字“里”,唱成高升調的陽平字為妥——自然之“語態”必須符合于“‘地態、‘心態、‘語態、‘樂態、‘情態、‘美態遞為反映”之生態規律。
透析上述,極其鮮明地折射出在漢語歌曲演唱中,漢語的聲、韻、調、情、美有多么豐富多彩的變化,其音色變化便也必然如此。從作為載體的曲調與曲文關系的角度來考量,旋律的“腔圓”必然是唱家的首選,之后方考慮“字正”。更何況“字正”的細微末節,多要靠歌者在二度創作中去微調,這便是一、二度創作中的分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