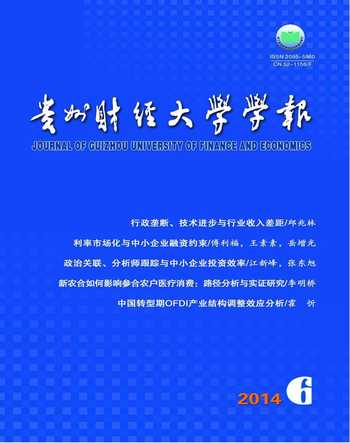新農合如何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路徑分析與實證研究
李明橋
摘 要:新農合可通過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誘導需求來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當CHNS調查數據排除掉新農合逆向選擇問題時,道德風險和誘導需求則共同決定了參合農戶醫療消費,那么,系統地研究新農合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就可以間接推導出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一方面,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降低了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導致患病率略有上升,醫療服務需求小幅上升;另一方面,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能夠及時就診,其避免小病拖成大病所降低的醫療消費量,相當于農戶因新農合承擔部分醫療消費而增加的醫療消費量,由此可知,參合農戶增加醫療消費的幅度較小。因此,大幅上漲的醫療消費歸因于醫生誘導參合農戶消費更多醫療服務,并且誘導需求主要發生在醫治小病(門診治療)領域。
關鍵詞:新農合;參合農戶;誘導需求;醫療消費
文章編號:2095-5960(2014)06-0075-08;中圖分類號:R197;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進入新世紀后,在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市場化改革的價值取向下,我國居民“看病貴看病難”十分普遍,令人更為不安的是,醫療費用上漲使得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極其嚴重,這不但損害了前期的扶貧效果,而且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鄭茂偉、方俊良,2013)。[1]為了扭轉這種不利局面,中央政府于2003年投入大量資金啟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和建設工作,新農合應運而生。眾多學者圍繞新農合推廣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關于新農合推廣問題的研究。理論上新農合難以有效規避“逆向選擇”問題,因為投保者風險無法逐個識別,建立在平均概率上的保費將使風險低于平均概率的人退出市場,從而導致保險市場風險不斷增加,形成一個典型的“檸檬市場”(朱信凱,2009)[2],導致新農合參保率不斷下降,從而難以有效推廣。然而,新農合存在政府補貼、較少繳費金額、較高風險規避以及較低醫療支出傾向是導致新農合逆向選擇問題較小的主要原因(封進,2007)[3]。與此同時,新農合主要“以戶為單位”、“干部動員保證參保率”的方式進行推廣,從而使新農合避免了逆向選擇問題(高夢滔,2010)[4],這有利于新農合在農村全面覆蓋。
其次,關于新農合補償模式的研究。各級政府在新農合政策實施初期,一方面要考慮新農合資金收支平衡問題,另一方面要求新農合能提高農戶抵御重大疾病風險的能力,因此,實施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這種只保大病的政策效果受到質疑,一方面,僅補貼重大疾病不利于農戶在健康出現問題時及時治療,容易導致小病拖成大病(封進,2007)。[3]另一方面,只補貼大病的政策僅能分攤農戶33.3%的重大疾病風險和24.2%的“因病致貧”風險,農戶健康風險依然比較嚴重(張廣科,2010)。[5]新農合只補償大病的政策實施過程中導致新農合資金累計盈余不斷增加,在此背景之下,為進一步提高農戶抵御健康風險的能力,各地區逐步實施小病補償(門診補償)政策。
最后,關于新農合與農戶醫療消費的研究。新農合提高了農戶醫療服務利用率,使得農戶年就診次數平均增加0.29次(高夢滔,2010)[4],從而明顯改變了農戶健康水平,但實際醫療支出和大病醫療支出并未顯著下降,因此,新農合在改善參合者健康狀況的同時,并未明顯降低醫療消費(程令國,2012)。[6]
現有文獻表明研究新農合問題的成果豐碩,但是很少有研究新農合如何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文獻。了解新農合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內在機制,一方面有利于控制不必要的醫療消費,從而降低新農合統籌資金的支出;另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提高新農合疾病補貼效率,從而提高農戶健康福利水平。因此,研究新農合如何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新農合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路徑分析
(一)新農合與參合農戶醫療消費
本文根據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CHNS)中2006與2009年兩輪數據繪制出的農戶人均醫療消費,如圖1和圖2所示,其中,縱坐標表示醫療消費金額(元),橫坐標由人均醫療支出、人均門診費用和人均住院費用構成。本文利用CHNS調查數據構建了同一樣本在2006和2009年都同時被調查的面板數據,這些樣本在2006年都沒有參加新農合,在2009年部分樣本參加了新農合(參保農戶),其余樣本仍然沒有參加新農合(非參保農戶)。圖1描繪了2009年參保農戶和非參保農戶醫療消費對比情況,圖2描繪了參保農戶參保前(2006年)和參保后(2009年)醫療消費對比情況。值得強調的是,本文參合農戶醫療消費不但包括農戶自身醫療支出,而且還包括新農合承擔的相應醫療支出。
由圖1可知,無論是人均醫療支出、人均門診費用還是人均住院費用,參保農戶醫療消費都小于非參保農戶,并且參保農戶人均住院費用僅為非參保農戶的59.62%(4348/7284),說明新農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農戶大病風險,該結論與張廣科(2010)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5]
由圖2可知,就農戶參加新農合前后而言,無論是人均醫療支出、人均門診費用還是人均住院費用,農戶參保后(2009年)的醫療消費明顯高于參保前(2006年)。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可知居民醫療保健價格指數2009年比2006年高出5.6%,表明即使扣除醫療服務價格上升因素,2006(參合前)到2009(參合后)年間參合農戶的平均醫療支出年增長率高達35.71%(環比)。由此可知,農戶在參合后(2009年)醫療消費比參合前(2006年)大幅上漲,這不僅不利于新農合資金的收支平衡,還有損新農合的可持續性。因此,本文試圖發現新農合導致參合農戶醫療消費上漲的原因,為抑制參合農戶醫療消費不合理上漲而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二)新農合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三條路徑
新農合可通過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誘導需求來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如圖3所示。首先,就道德風險而言分為事前和事后兩種情況。其一,事前道德風險是指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忽視了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使得患病率上升,從而增加了醫療消費。如表1所示,2009年參合農戶在沒有參加新農合以前(2006年)發病率為11.3%,而參合后(2009年)上升為15.38%,表明農戶可能存在事前道德風險行為,從而導致患病率上升。其二,事后道德風險是指新農合改變了農戶醫療需求行為。如圖3所示,一方面,新農合激勵農戶積極就診,避免小病拖成大病,從而降低了醫療消費,即為積極醫療需求;另一方面,新農合承擔了農戶部分醫療費用,使得農戶醫療需求的邊際成本下降,農戶根據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來決定醫療消費時,傾向于過多消費醫療服務,即為過度醫療需求。事后道德風險對醫療消費的影響取決于積極醫療需求和過度醫療需求的相對大小。
圖3 新農合影響醫療消費的路徑其次,逆向選擇是指投保者風險無法逐個識別,使得高風險的投保者更愿意投保。就本文而言,如果新農合存在逆向選擇問題,那么2009年參合農戶健康狀況在參合以前(2006年)應該比非參合農戶更差。然而,根據表1可知,2009年參合農戶在沒有參合以前(2006年)的發病率(11.3%)低于非參保農戶(14.11%),表明參合農戶在參合前的健康狀況比非參合農戶更好,因此CHNS調查數據的新農合樣本不存在逆向選擇問題,該結論與封進(2009)[7]和高夢滔(2010)[4]的研究一致,因此,新農合并沒有通過逆向選擇影響農戶醫療消費。
最后,由于病患信息不對稱,醫生可以根據農戶是否參加新農合而制定不同的治療方式,誘導參合農戶消費更多醫療服務,從而增加了農戶的醫療消費,即為誘導需求。經濟學領域很少有估計誘導需求的研究,原因在于:一方面,醫學領域難以界定不同疾病的最優醫療消費水平;另一方面,估計誘導需求既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經濟學理論背景,又要有淵博的醫學知識。
綜上所述,排除逆向選擇后,新農合通過道德風險和誘導需求來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雖然本文沒有研究新農合誘導需求問題,但是只要研究出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就能夠推導出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從而全面了解新農合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原因。
(三)道德風險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模型設定
實施新農合政策的時間和地點相對于農戶而言是隨機的,因此,新農合對農戶是一種“自然沖擊”,在此背景下,可用政策因果效應方法來估計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無論在理論領域還是實證方面,政策因果效應方法都日益成熟和完善,具體采用哪種方法估計政策因果效應取決于數據結構(Imbens,2009)。[8]若已知政策前的樣本數據(事前組)和政策后的樣本數據(處理組和控制組),則可用倍差法(DID)進行估計。
本文數據來源于CHNS2006年(新農合實施前)和2009年(新農合實施后)兩輪調查,數據結構符合倍差法要求,因此采用該方法來估計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由上文可知,道德風險又分為事前道德風險和事后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也有相應兩種情況。事前道德風險是指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忽視了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使得農戶患病率上升,從而增加了醫療消費。因此,估計事前道德風險就是估計新農合對參合農戶患病率的影響。本文估計事前道德風險的方程如(1)式所示,其中,因變量SICKit表示i農戶在t時期是否患病或受傷的虛擬變量;自變量NRCI i 和POST t分別表示i農戶是否參加新農合和新農合政策實施前后的虛擬變量;Xit為控制變量。估計系數Β13即為事前道德風險影響參合農戶患病率的因果效應。如果估計系數Β13>0,那么表明存在事前道德風險,經濟學含義為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忽視了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導致患病率上升。如果估計系數Β13≤0,那么表明估計結果與經濟理論預測不一致,農戶不存在事前道德風險。
SICKit= Β10 + Β11×NRCI i + Β12×POST t +Β13 NRCIi ×POST t+ γ1 X it + ε it (1)
估計事后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應注意兩個問題:其一,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變化取決于積極醫療需求和過度醫療需求的共同作用,因此,只有估計出事后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才能識別出積極醫療需求與過度醫療需求的相對大小;其二,患病后進行治療是農戶存在醫療消費的前提條件,即是說是否存在醫療消費取決于農戶是否就診,由此可知,農戶醫療消費可能是樣本自選擇(sample selection)的結果。
本文使用Heckman樣本自選擇模型來估計事后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Heckman模型由回歸方程(2)式和選擇方程(3)式構成,其中,Log(EXPENSE) it和TREATit分別表示i農戶t時期的醫療消費(對數形式)和i農戶t時期是否就診的虛擬變量。農戶是否就診同樣取決于潛在的或者說是預期的醫療消費,也就是說是否就診和醫療消費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為了解決這種雙向因果問題,使用Heckman模型時選擇方程中必須至少有一個自變量不影響農戶醫療消費,但是影響農戶是否就診的行為,這個變量類似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中的工具變量。農戶就診的交通成本對農戶是否就診產生影響,但并不影響農戶的醫療消費,故選擇方程自變量TRACOST i表示農戶就診的交通成本,X 1it和X 2it分別為(2)和(3)式的控制變量。估計系數Β23就是事后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該系數取值有三種情況:首先,如果Β23>0,那么事后道德風險增加了參合農戶醫療消費,表明積極醫療需求作用小于過度醫療需求;其次,如果Β23=0,那么事后道德風險沒有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表明積極醫療需求和過度醫療需求作用相當;最后,如果Β23<0,那么事后道德風險降低了參合農戶醫療消費,表明積極醫療需求作用大于過度醫療需求。
三、數據和變量說明
(一)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來源于北卡羅來納大學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合進行的國際合作項目——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CHNS數據涵蓋九個在地理位置、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和健康狀況都存在較大差異的省份,至今進行了八輪調查,其中,2003年之前和之后分別進行了五輪和三輪調查。該項目旨在調查中國居民健康和營養狀況以及相關影響因素,因而包含了較為詳盡的關于農戶健康、醫療消費和醫療保險方面的數據。2003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要求從2003年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至少要選擇2—3個縣(市)進行新農合醫療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開(王紹光,2008)。[9]隨即,國務院按照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區差異,首先選取了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四個省份進行試點,后才陸續在全國開展試點工作。
由此可知,CHNS的數據只有2004年、2006年和2009年最后三輪的調查涉及新農合方面的信息,而 2004年涉及新農合的調查數據主要來自于湖北省,不具有代表性。從2005年開始新農合逐步普及,CHNS關于新農合的樣本數據地域更加廣泛,并且最后兩輪調查數據排除了逆向選擇問題。因此,本文使用2006和2009年的調查數據來估計道德風險對醫療消費的影響。
(二)變量選取及樣本描述
根據估計方程(1)式、(2)式和(3)式來選取所需的變量。首先,就事前道德風險而言,選取“過去四周是否生過病或受過傷”作為估計方程(1)式的因變量。就事后道德風險而言,選取過去四周的醫療花費(對數形式)作為估計方程(2)式的因變量。值得一提的是,農戶醫療費用既包括農戶自付的醫療費用又包括新農合承擔的醫療費用。選取是否到正規醫療機構就診作為選擇方程(3)式的因變量,由Heckman模型可知選擇方程中必須有一個自變量影響農戶是否就診,且不影響農戶醫療消費,故選取到達正規醫療機構的時間作為選擇方程就診交通成本(TRACOSTi)的代理變量。
根據國內健康經濟學文獻中常用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作為控制變量。由表2可知樣本特征如下:首先,參合農戶(處理組)和非參合農戶(控制組)的年齡、性別和健康狀況(BMI)變量的差異不明顯;其次,就已婚比例而言,參合農戶高于非參合農戶;最后,農戶受教育程度都較低,受教育水平在大專及以上的農戶比例不超過5%。
四、新農合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事前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患病率的影響
方程(1)式實證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首先,年齡對患病率的影響表現為U型特征,即農戶處于青壯年時健康狀況較好、患病概率較低;當農戶處于幼年階段時免疫功能不強、容易患病;當農戶處于老年階段時免疫功能下降,患病率上升,這與實際情況相符。其次,女性患病率明顯高于男性,這與“性別悖論”理論一致。“性別悖論”是指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似乎表明女性健康狀況比男性更差,然而女性期望壽命反而高于男性。最后,受教育程度越高、患病率越低。如果農戶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對健康保健和疾病預防就越了解,患病率就越低。上述實證結果與健康經濟學理論預測一致,表明估計方程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說明估計出的事前道德風險對患病率的影響可信度較高。
為確保事前道德風險對農戶患病率的影響具有穩健性,使用了不同的控制變量進行多方程回歸估計。如表3所示,無論是哪個估計模型,事前道德風險(變量NRCIi ×POSTt的估計系數)都始終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影響農戶患病率,且估計系數相對穩定。由此可知,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忽視了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從而使得農戶患病率上升,也就是說新農合引發的事前道德風險使得參合農戶患病率上升了5%。因此,現有文獻(高夢滔,2010)[4]發現新農合增加了農戶的醫療服務利用率,這歸因于新農合事前道德風險提高了參合農戶患病率,從而增加了醫療服務利用率。
(二)事后道德風險對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
Heckman回歸方程(2)式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當控制變量逐漸增加時,逆米爾斯比值的置信水平不顯著逐漸變得顯著,說明農戶醫療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是樣本自選擇的結果,即是說,是否存在醫療消費取決于是否就診的決定。其次,由POST變量的估計系數可知,醫療支出在新農合實施前后差異較大。最后,受教育程度越高,醫療消費越小。就病患信息而言,醫生和患者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當醫生比患者掌握的病患信息越多時,醫療消費就會越高;反之亦然(盧洪友,2011)。[10]因此,患者受教育程度高低決定了對病患信息的了解水平,從而對醫療消費產生影響。
為確保事后道德風險影響農戶醫療消費具有穩健性,使用了不同的控制變量進行多方程回歸估計。如表4所示,無論是哪個估計模型,變量NRCIi ×POSTt的估計系數始終大于0似乎說明事后道德風險增加了參合農戶的醫療消費,但是任何一個模型的估計系數都不顯著,說明事后道德風險沒有顯著影響參合農戶醫療費用,即是說事后道德風險引發的積極醫療需求與過度醫療需求作用相當,醫療消費無明顯變化。
(三)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
雖然本文沒有研究新農合誘導需求問題,但是只要研究出了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就能夠推出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分析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步驟如下:
首先,由表2可知,參合農戶的平均醫療消費從2006年(參合前)的328元增長到2009年(參合后)的821元,說明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導致醫療消費年增長率為35.71%(環比)。其中,參合農戶門診醫療消費從2006年的204元增長到2009年的600元,年增長率為43.26%(環比),說明參合農戶門診消費(小病治療費用)增長幅度較快;2009年參合農戶住院消費從2006年的3491元增長到2009年的4348元,年增長率為7.44%(環比)。
其次,新農合事前道德風險使得農戶患病概率上升5%,表明農戶醫療消費因事前道德風險而增長5%;新農合事后道德風險對農戶醫療消費沒有影響;再次,分析2006年至2009年居民醫療保健價格上漲幅度;最后,參合農戶醫療消費增長率扣除新農合道德風險和醫療保健價格上漲因素之后,就是醫生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
如表5所示,扣除道德風險和醫療價格上漲因素后,醫生誘導參合農戶消費醫療服務導致醫療消費年增長率高達28.88%,由此可知,誘導性需求是新農合導致醫療消費上漲的主要原因。詳細分析可知,誘導需求行為使得參合農戶門診消費和住院消費分別增長了36.43%和0.61%,表明醫生誘導參合農戶消費醫療服務主要發生在醫治小病(門診治療)領域。
產生誘導需求行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醫療體制在不斷改革過程中卻沒有合理地提高醫務人員勞動報酬價格,使得醫務人員尤其是醫生勞動報酬價格被嚴重低估,催生了通過誘導參合農戶消費醫療資源,來間接提高勞動報酬價格的行為;另一方面,門診治療相對于住院治療而言,不但患者人數眾多,而且醫療管理機構更難以有效監管,使得醫生在醫治小病時更偏好于誘導參合農戶過度消費醫療服務。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借助CHNS調查數據,運用倍差法和Heckman樣本自選擇模型研究了新農合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新農合可通過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誘導需求來影響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當CHNS調查數據排除了新農合逆向選擇問題時,那么道德風險和誘導需求共同決定了參合農戶醫療消費。本文系統地研究了新農合道德風險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間接推導出了誘導需求對參合農戶醫療消費的影響。
研究發現:一方面,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降低了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導致患病率略有上升,醫療服務需求小幅上升;另一方面,農戶因參加新農合而及時就診,避免小病拖成大病所降低的醫療消費量,相當于農戶因新農合承擔部分醫療消費而增加的醫療消費量,由此可知,參合農戶增加醫療消費的幅度較小。因此,大幅上漲的醫療消費歸因于醫生誘導參合農戶消費更多醫療服務,并且誘導行為主要發生在醫治小病(門診治療)領域。
研究結論的政策建議:首先,加強健康知識宣傳力度、增強參合農戶健康保健與疾病預防意識,降低農戶事前道德風險行為;其次,重點監控參合農戶門診治療是否存在誘導需求行為,嚴厲打擊過度醫療消費行為;最后,提高醫務人員勞動報酬以降低醫生誘導需求動機,從而降低醫療消費。
參考文獻:
[1]鄭茂偉,方俊良.農村居民健康支出與人均純收入的相關性分析[J].財經理論研究,2013(4):47-53.
[2]朱信凱,彭廷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的“逆向選擇”問題: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9(1):55-66.
[3]封進,宋錚.中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一項基于異質性個體決策行為的理論研究[J].經濟學季刊,2007(4):843-860.
[4]高夢滔.城市低收入人群門診服務利用的實證分析[J].南方經濟,2010(1):35-43.
[5]張廣科,黃瑞芹.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目標及其實現路徑[J].中國人口科學,2010(4):15-24.
[6]程令國.新農合:經濟績效還是健康績效?[J].經濟研究,2012(1):87-118.
[7]封進,李珍珍.中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補償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9(4):25-37.
[8]Guido W.Imbens and Jeffrey M.Wooldridge,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etrics of Program Evalu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9:5-86.
[9]王紹光.學習機制與適應能力:中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變遷的啟示[J].中國社會科學,2008(6):54-65.
[10]盧洪友,連玉君,盧盛峰.中國醫療服務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測算[J].經濟研究,2011(4):31-42.
責任編輯:吳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