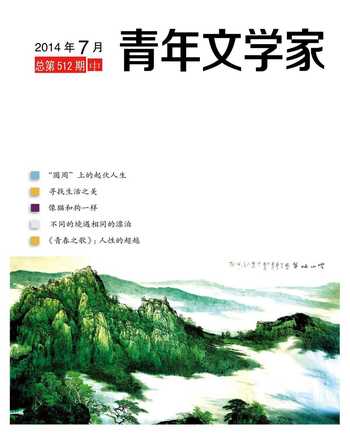《青春之歌》:人性的超越
摘 要:《青春之歌》是一部革命文學,但是文學的復雜性,使得楊沫在文本中實現了對革命文學的超越。這種人性對政治性的超越,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價值所在。人性是永恒的,是不為任何東西所掩蓋的,盡管經歷時間的滄桑,但人性本質的東西從未改變,這也是《青春之歌》能夠在距文本創作幾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保持價值的原因。
關鍵詞:青春之歌; 細讀法
作者簡介:孫嘉慈(1992-),女,漢族,山東省濟南市人,學生,單位: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 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20-0-01
《青春之歌》是一部革命文學,“革命敘事雖然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下不得不裝裹了一層厚厚的紅色油彩,但這油彩下面卻依舊潛藏了文學的全部復雜性,這是由作者的‘個體無意識決定的”。[1]作者在潛意識的敘述中透露出人性超越政治性,愛情超越革命的傾向,是《青春之歌》跨越了時間空間,依舊被人們所喜愛的原因所在,也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價值所在。
一、人性的暴露
林道靜一生最愛的人應該是盧嘉川,她的心底一直存有他的位置。她曾經與余永澤和江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近距離地感受過真實的他們,而對于盧嘉川,她的感情卻是停留在精神層面,可以說,她愛的是臆想出來的盧嘉川,而不是真正的盧嘉川,盧嘉川的許多缺點她并沒有見過,因為保持了距離,所以愛情才可以保持神秘新鮮。盧嘉川是一位理想型的革命者,他領導學生運動,游行示威,張貼傳單,卻沒有江華那樣豐富的底層實踐經歷,作者有意賦予了他許多意識形態的東西,使他的形象變得高大。但因為作者對于盧嘉川的描寫包含了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感情,所以卻在潛意識里暴露了一些情感的真實。
小說第一部第十三章,盧嘉川到林道靜家里去找她,與林道靜短時間的交談,卻總是在有意無意間傳遞愛意。“‘你現在并不老,怎么能夠再年輕?盧嘉川瞇著眼睛看著道靜。頑皮的微笑又浮在他的嘴角。”[2]話語中透露著調皮,作者又用了“瞇著眼睛”和“頑皮”,這樣的輕浮和一個高大的革命者的形象不符。當林道靜提出要上戰場,盧嘉川“剛剛可以覺察到的調皮的微笑又浮現在他活潑的眼色中”[3]。又是“調皮”和“活潑”這樣輕快明朗的詞語。后面兩人的對話中也出現“輕輕的、意味深長的微笑”。短短的一章,盧嘉川幾次在微笑,而且都是調皮的微笑,這很值得回味。顯然,盧嘉川在表達對林道靜的好感,這種好感遠遠超過了革命者之間的友誼,而且包涵了他有意制造出的曖昧。
與此同時,林道靜也在表達對盧嘉川的好感。盧嘉川一走進院子,林道靜就“立時扔下手里的煤球和簸箕,不管火柴正在熊熊燃燒著,慌忙地要領老盧進屋去”。為什么她要連做飯都不顧,直接過去呢,難道為了革命同伴的到來就連生活也不要了嗎。林道靜給出的理由是怕“盧嘉川看見自己做這些瑣細的家務勞動而感到羞怯”,這一方面顯示了林道靜思想認識上的不足,她以為談革命就要轟轟烈烈,革命者就不能做瑣碎的家務;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女子在心儀男子面前的羞怯,她不想自己灰頭土臉做飯的樣子被人看到。她小心翼翼地對待盧嘉川,像是戀愛中的人一樣敏感。面對盧嘉川的關心,“一種油然而生的尊敬與一種隱秘的相見的喜悅,使得她的眼睛明亮起來”。“油然而生的尊敬”可以解釋為對于一個革命引路人的敬仰之情,“隱秘的相見的喜悅”則顯示了見到自己仰慕的人的興奮。
二、人性的超越
《青春之歌》又是一部青春成長小說,但林道靜最后到底有沒有實現真正的成長,這值得探討。表面看來,她在盧嘉川、江華等人的幫助下提高了自身的覺悟,加深了對革命的認識,小說最后她轉身加入浩浩蕩蕩的隊伍中,不停地前進,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林道靜的這種前進是迷茫的,她只是追隨大家的腳步,亦步亦趨。林道靜心里對革命和戀愛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她分不清愛的是黨還是個人,從一開始她就混淆了革命和愛情的界限,她認為“像江華這樣的布爾塞維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熱愛的”,所以接受了江華的表白。后來她又說“我能夠有今天,我能夠實現了我的理想——做一個共產主義的光榮戰士,這都是誰給我的呢?是你——是黨。”她的話語中把江華和黨畫上了等號,其實江華只是一個個體,他不能代表黨。難道每一個革命者都代表黨,然后每一個革命者都要愛嗎?小說里林道靜的最終歸宿是江華,但如果故事繼續進行下去,會不會出現第四個男人,我們誰也不知道。
林道靜認識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作者認識的缺陷。林道靜的人物塑造不是完美的,但這并不影響文本的經典性,因為文學作品需要的從來都不是掩飾而是真實。正是因為它在字里行間呈現出作者的真實情感,曲折地反映出特定時期的革命運動,所以才可以在距文本創作幾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保持價值。“革命敘事也是會有非常‘異類的因素,會有超出道德樊籬的縫隙,會有隱秘的人性傳達與敏感的無意識內容。”因為人性是永恒的,是不為任何東西所掩蓋的,盡管經歷時間的滄桑,但人性本質的東西從未改變。
參考文獻:
[1]張清華.《青春之歌》:革命文本的潛結構及無限歧義的可能性[J].長城,2011(11)
[2]楊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張清華.《青春之歌》:革命文本的潛結構及無限歧義的可能性[J].長城,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