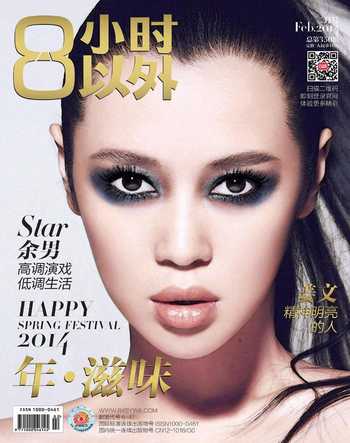《易經(jīng)》不神秘
舒容

提起《易經(jīng)》,人們往往想到“歪門邪道”,就是舞臺(tái)上那些身穿八卦道袍、呼風(fēng)喚雨的妖道,還有江湖上那些算命的、看風(fēng)水的招搖撞騙的人。這真是對《易經(jīng)》的天大誤解。事實(shí)上,《易經(jīng)》代表了中國文化最高的智慧,“是哲學(xué)中之哲學(xué)”。
但《易經(jīng)》實(shí)在太難懂了。《易經(jīng)》最初只是一幅圖,為伏羲氏所作,當(dāng)時(shí)還沒有文字。后來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等為它加注,那“注”也是高深莫測。所以當(dāng)我讀到“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時(shí)”這個(gè)美麗的句子,很不以為然,認(rèn)為是一種炫耀——那樣枯燥的東西,也能讀到廢寢忘食?然而,南懷瑾先生的《易經(jīng)雜說》,讓我有了這種感覺。
南懷瑾著作等身,其《論語別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說》、《禪話》、《禪宗與道家》、《中國文化泛言》、《歷史的經(jīng)驗(yàn)》,等等,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引進(jìn)大陸后,立即風(fēng)靡。南懷瑾飽讀詩書,所以能旁征博引,諸子百家、釋迦、耶穌、穆罕默德,天文地理、星相養(yǎng)生,無所不包。他說他著書的目的,是啟發(fā)讀者“在進(jìn)退失據(jù)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中”,如何避免“在紛紜混亂中忙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適從”。這正是現(xiàn)代人所需要的。
《周易》是南懷瑾 “研究了大半輩子”的書。“我們?nèi)寮业奈幕兰业奈幕磺兄袊奈幕际菑奈耐踔髁诉@本《易經(jīng)》以后,開始發(fā)展起來的。所以諸子百家之說,都淵源于這本書”。南先生說,讀懂了《易經(jīng)》,再讀《老子》《孟子》就迎刃而解了。
《易經(jīng)雜說》引人入勝處,是南懷瑾以淵博的學(xué)識(shí)、小說的筆法,將人事與自然法則、歷史規(guī)則結(jié)合為一,并以極為嚴(yán)肅的治學(xué)態(tài)度,輕松的口吻,網(wǎng)羅逸聞,探玄尋秘,透露出《易經(jīng)》的秘密。
“我們看古文的‘易字,上面是日的象形,下面是月的象形,把上面太陽和下面月亮合起來,便是‘易字了。《易經(jīng)》這本書,是敘述我們?nèi)祟愡@一個(gè)太陽系統(tǒng)的宇宙中,日月運(yùn)行的一個(gè)大法則。”南先生說,《易經(jīng)》一點(diǎn)都不神秘,因?yàn)椤白罡叩牡览恚彩亲钇椒驳牡览怼薄?/p>
“八卦”,并非如今日所用,指名人明星的飛短流長,而是宇宙間的八種現(xiàn)象。“卦者掛也”,這八種現(xiàn)象被畫成圖掛起來。每個(gè)卦有三畫,卦中的畫“—”稱為爻。“爻者交也”,宇宙間萬事萬物,時(shí)時(shí)都在交流,不停地發(fā)生關(guān)系,引起變化,所以叫“爻”。后來,三爻卦不夠用,就有了六爻卦。之所以是六爻,因?yàn)椤坝钪骈g的事情、物理,沒有超過六個(gè)階段的”。《易經(jīng)》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四千九十六卦,無一不為人事而設(shè),告訴占者得此卦此爻如何如何。這些屬“象數(shù)之學(xué)”,即近代所謂心靈學(xué)、神秘學(xué)之類。
孔子說,《易經(jīng)》是“潔靜精微”的思想,但“其失也,賊”,學(xué)了《易經(jīng)》的人,如不走正路,就成了旁門左道、賊頭賊腦。南先生引用古人的話說:“善《易》者,不言卜。”真正懂《易經(jīng)》的人,一看現(xiàn)象,就了然于心了,不必再去算卦。這就是《易經(jīng)》“義理之學(xué)”的神奇之處。
唐朝一位宰相說,不讀《易經(jīng)》,不可以為相。作為普通人,《易經(jīng)》則可以使我們趨吉避兇、智慧生存:當(dāng)我們?yōu)檫^去的事情懊悔,或擔(dān)心未來的變化,《易經(jīng)》告訴我們,世間事,世間人,乃至宇宙萬物,沒有一樣?xùn)|西是不變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當(dāng)我們抱怨自己懷才不遇,《易經(jīng)》告訴我們兩個(gè)重點(diǎn):時(shí)與位,即時(shí)間與空間。時(shí)位不屬于你時(shí),就不要?jiǎng)樱瑫r(shí)位屬于你時(shí)才可以行事。孟子所說的“窮則獨(dú)善其身,達(dá)則兼濟(jì)天下”也是這個(gè)道理;有時(shí)我們身處逆境而絕望,《易經(jīng)》告訴我們,“否”的下一卦是“泰”,否極泰來,是規(guī)律,挺住就是了;你作為領(lǐng)導(dǎo),為“啥事都瞞不過你”而得意,然而讀了《易經(jīng)》你知道:察見淵魚者不詳,有一雙銳利的眼睛,啥都能看到,這樣費(fèi)神,必短壽,還是適當(dāng)胡涂點(diǎn)好;生活中的煩惱一個(gè)接一個(gè),心安為啥那么難?《易經(jīng)》最后一卦是未濟(jì)卦,告訴我們,自宇宙開始,人生最后永遠(yuǎn)是未濟(jì),有始無終,沒有結(jié)論……
《易經(jīng)》的影響不僅在義理上。我們中國人平常說的話,也常常來自《易經(jīng)》。比如“錯(cuò)綜復(fù)雜”這個(gè)詞,錯(cuò)、綜、復(fù)都是卦名,分別由另一個(gè)卦變來,比較“錯(cuò)綜復(fù)雜”。從一個(gè)卦變成另一個(gè)卦,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于是又有了“變卦”這個(gè)詞。又如“不三不四”,為啥不說“不五不六”呢?《易經(jīng)》的道理,第三爻和第四爻最重要,在卦的正中間,中心位置,所以三、四之外不正當(dāng)?shù)亩冀胁蝗凰摹C韶允侵鹘逃模髞肀阌辛恕皢⒚伞边@個(gè)詞。還有“亂七八糟”“恩生于害”“定數(shù)”“變數(shù)……都是從《易經(jīng)》來的。
南懷瑾說,所有經(jīng)典必須刻苦研讀,唯有《易經(jīng)》,可以玩。《易經(jīng)雜說》還教了我們玩《易經(jīng)》的技巧與要領(lǐng),讓我們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