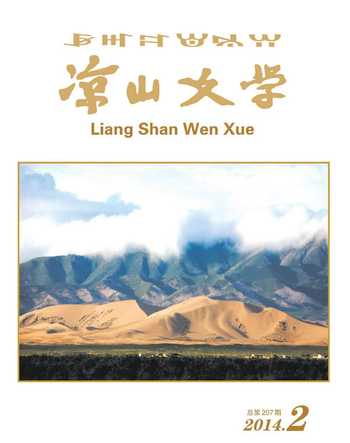1996年的假牙(外一篇)
美樺
祥子事后想起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根本沒有半點先兆。
那一個深秋的午后,秋風輕柔,陽光很好。祥子剛超過一輛車,回到大車道,耳邊就傳來了破鑼樣的聲音:
“師傅,停一下!”
“師傅,停車呀!”
破鑼樣的聲音不高,但顯得急促,容不得半點商量。
祥子飛快地瞥了一眼,是一個老太婆。
老太婆身體單薄,佝僂著腰,棕色的帽子下面,幾綹散亂的白發,把老核桃樣的臉襯托得更加焦躁。老太婆大張著嘴,一手拉著車上的扶手,一手夸張地扯著嘴巴,露出癟下去的牙床:
“牙齒,牙齒!我的牙齒掉了!?”
“牙齒?牙齒……怎么會掉?!”祥子緊緊握著方向盤,雙眼直視前方,嘟嚨了一句。活了四十多歲,祥子實在想像不出,老太婆的牙齒,怎么平白無故會掉到外面去。
“剛才吐痰呀,不小心假牙掉到外面去了!這一口假牙,我一直都很小心的,今天這鬼運氣是背時了……”老太婆松開扯著嘴巴的手,那嘴馬上就癟進去,差不多都貼在鼻子上了。
老太婆深刻地作著自我檢討,蒼老的臉上滿是自責和羞愧。看著車窗外呼呼直往后退的風景,老太婆急促地叫起來:“師傅,麻煩你停一下嘛!”
“干啥?”祥子覺得有些滑稽。
“下車去找找!”
“啥啥啥?你開什么玩笑?這車是不能停的!”
“不能停,啥車這么霸道喲?我這副假牙一千多塊呀,你賠我?”老太婆急了,聲音一下高起來。
“又不是我把你弄掉的,憑啥我賠你?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祥子沒好氣地說。
“咦,我的假牙在你車上弄丟的,要你停車你不停,這帳不該算在你頭上?要是你不停車,今天你賠我的假牙賠定了!”老太婆大著嗓門,氣呼呼地沖著祥子直嚷嚷。
“你嚇唬三歲小孩還差不多!你以為高速路上這車你想停就能停的?”高速路一開通,祥子就在上面跑。十多年過去,什么樣的人沒見過?當然,對鬧出中途要停車笑話的乘客,他還從來沒有滿足過這方面的要求。這不是他愿不愿意停的問題,事實上車上的乘客就絕對不會答應。
正如祥子預想的一樣,剛才懨懨欲睡的一車人,這個時候全部睜開了眼睛,外星人一樣盯著老太婆。
按理說來,出門在外,在這種時候是不會有人出來管閑事的。可是,這車停與不停,除了耽誤大家的寶貴時間外,更重要的是事關每一個人的安危,這就不再是簡單的閑事了。因此,很快就有人忍不住開了口:
“老太婆,啥假牙有這么金貴,高速路上是不準停車的,你知道嗎?”
“老太婆,高速路上停車,出了安全事故,你負得起這個責任不?”
“老太婆,你要讓車停下來,全車的人都得等你,耽誤了大家寶貴的時間,你賠我們的損失?”
一連串的責問,其核心內容不言而喻。老太婆有些招架不住,扯開嘴巴,從嘴里摳出一塊假牙來:“這是下牙,上牙不見了!沒上牙,我沒法吃飯喲……”
老太婆可憐兮兮地說。老太婆顯得有些心虛,底氣就沒有剛才那么足。
“你吃不吃飯關我們屁事?!”
“就是!”
又是七嘴八舌的聲音。一車的人都很激動,沒有一個是她的同盟軍。
老太婆耍魔術一樣在大家面前晃動著她的假牙,咂咂癟進去的嘴,嘆了一口氣:“曉得不,這假牙是我老三給我裝的。那是1996年秋收過后,我忙著請人把小春種下去,老三把我帶到省城,找口腔醫院看醫生。人家那醫生才叫把細喲,頭個星期叫我去咬牙印做模子,第二個星期才裝的假牙。我老三當過兵,見的世面多,他知道疼他娘。老頭子死得早,我四十多歲滿口牙就掉光了,受了20多年罪,才享了這副假牙的福。”
老太婆絮絮叨叨,說得上氣不接下氣。一車的人都在聽,但大多數表情木吶。老太婆剛才那一番話顯然是對牛彈琴,根本沒有引起大家的共鳴。
“過了一年,我才曉得,這副牙花了1500塊。我老三在外面幫人打工,工資不高,除掉開銷,那是他差不多一年的積蓄吶!唉,我那老三啊……”
老太婆咂著那癟下去的嘴,長嘆了口氣,輕輕地搖著頭,帽子下面那幾綹花白的頭發就更加散亂。老太婆微瞇著眼,那一臉的幸福,仍然沒有引起人的共鳴。因為,車上有人撇著嘴,甚至還有人在嗤嗤嗤地笑。
車上這些人的冷漠,并沒有影響老太婆的情緒。老太婆還沉浸在那樣的幸福里,眼里淚光閃閃,一時無語。
車里一時靜下來,但沉默的時間并不長。老太婆用袖子擦擦眼,把假牙塞進嘴里,又開始了剛才的話題:
“師傅,停一下!”
“師傅,麻煩你停一下,我去看看呀!”
在停不停車這個關鍵問題上,祥子是用不著操心的。祥子還沒有表態,一車的人就緊張起來,有人在嘀嘀咕咕,有人在交頭接耳,很快大家又達成了共識。于是,幾個人幾乎同時嚷起來:
“不能停,不可能在高速路上開這種玩笑喲!”
“我們不可能等你一個人!”
“這么快的車速,你上哪去找嘛?簡直是亂彈琴!”
聲音雜七雜八,但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和剛才是完全一致的。
這些話仍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老太婆的眼里滿是幽怨,一手抓著欄桿,那只空出來的手在空中狂舞著,聲音急促而有力:
“停一下!停一下!!”
車窗外,山啊樹啊防護啊欄根本不理會老太婆焦急的心情,唰啦啦啦飛快往后退,從車窗呼呼灌進來的風格外剌耳。
要說讓老太婆假牙掉到外面去,還得怪公司。祥子已經找公司老總說過多次,這臺老式車沒空調,熱天弄得汗流浹背,冬天凍得人直打哆嗦。要是全部換成空調車,車窗全封閉,哪里會出這樣的洋相?可是,老太婆的假牙已經掉了,現在說這些還有啥意思。不過,即使是這樣,祥子也很坦然,一說到停車,車上的人都比他急。
“老太婆,剛才聽你說,那副假牙是1996年裝的對不對?”一個中年男人高聲問。
老太婆停止了剛才在空中狂舞的那只手,警惕地看著這個說話的人,沒有說話。
“我給你講,老人家!假牙一般的使用年限,最多是3到5年。你這副假牙已經足足用了15年,已經超過使用極限,早就該淘汰了!更重要的是,你剛才拿出來那副假牙,一看就是用熱凝樹脂材料做的基托,上面種上了塑料做的人工牙。這些都是特殊的化學材料,長時間放在嘴里,超負荷的使用,會損傷你的牙齦,引起口腔癌變,血小板減少,神經紊亂,帶來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
祥子一聽就知道,這個文質彬彬的人是一個醫生。他說的道理并不深奧,但誰都聽得出其中的潛臺詞,那副該死的假牙早就該扔了。
“瞎說,老婆子都用了15年了。怎么不見我得啥病?”
有人在起哄:“老太婆,找不到了!丟了算毬!”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下了車讓眼鏡重新給你裝一副,價格上讓他給你打點折!”
“就是就是!眼鏡,你就按進價給老太婆配一副哈!”
祥子暗暗好笑,誰說世間缺少愛?一車好心腸的人說的說,勸的勸,該給的人情給了,該作的主也作了,熱心得就像對待自己的親娘老子。
可是,這一切根本就沒有收到實質性的效果。老太婆張著無牙的嘴,堅決地搖著頭:
“1500塊,說扔就扔了,哪有這種事?你們錢多舍得,我是舍不得的。那是我老三一年的辛苦錢喲……”
老太婆聲音哽咽起來。她轉過頭去,對祥子叫起來:
“師傅,停車呀!”
祥子還沒有開口,車上又有人說開了:
“老大娘,看你一大把年紀了。按理說,只有你訓導我們小輩的,但是,今天我實在忍不住要開導你幾句!”說話的是一個黑臉漢子。漢子濃眉大眼,聲音洪亮,身子往前傾,盡量讓老太婆聽清他的話:
“老大娘,你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受了這么多年的社會教育,你應該是一個明理人。不管是啥事,凡事得講政策,按政策辦事吶,你說對不對!”
老太婆口氣明顯軟下來:“政策?啥政策?”
“國家政策有規定,為了保證旅客的安全,客車在高速路上是不能停的。你怎么要讓駕駛員做出違反政策的事呢?”
“這,我的假牙就這樣扔了?”
“那是你個人行為,應該由你自己負責。你看嘛,政策規定得清清楚楚……”黑臉漢子站起來,指著車窗上面帖著的一行字,一字一頓念道:“‘不準將頭手伸出窗外!你自己把車窗推開,把頭伸出去,不符合乘車安全要求,是你違背政策,做得不對喲……”
“我只是吐了口痰,又沒把頭伸出去。”老太婆大概知道自己理虧,說話聲音顯然沒有剛才急促。
“問題是你現在又要駕駛員違反規定停車,那就更不對了嘛!”
“這這……難道我的假牙就白白扔了?那是我老三……”
“假牙是你自己不小心弄出去的,你怎么能怪人家駕駛員呢?”
“我哪里在怪駕駛員,我是讓他停車,我自己下去找呢!”
“這不是停不停的問題,開車有開車的規矩,乘車有乘車的規矩,這就是政策!如果想怎么著就怎么著,都不按政策辦事,這個世界就亂了套。大家說,是不是這個理?再說了,大家都在趕車,各有各的事,一車的人在這兒等你,大家也不會答應嘛!”
“對的,不能停!”
“就是不能停!要我們一車人等你,沒門!!”
一車的人都倒向了中年漢子這一邊,成了他最忠實的支持對象。
老太婆不吱聲了,那張老核桃樣的臉顯得更加憂郁。
“哦,對了,還是人家鄉長有水平!老太婆,你聽鄉長的沒錯!”
見大功告成,和中年漢子坐在一起的人,也在旁邊幫腔。
沒想到就是這一句話,老太婆一下不干了:
“呸!當官的話都聽得,耗子藥都吃得!!”
老太婆胸口劇烈地起伏著,溝壑縱橫的臉上灑了一層霜,眼睛里冒著火。這一瞬間的變故,讓中年漢子覺得無比尷尬,但又找不到更好的道理來說服老太婆,只好怏怏地坐下來。
老太婆扭過頭去,氣呼呼地對祥子吼:
“停車!你到底停不停喲!”
祥子沒想到老太婆的情緒變得這么快。跟生命和時間相比,那副假牙算什么?盡管老太婆情緒激動,但祥子相信,車上的人不可能輕易讓老太婆的陰謀得逞。
“不能停!”
“不準停!!”
車上的人異口同聲地說。
在大家的聲討中,一個胳腮胡應聲站起來,低著嗓門兇巴巴地吼:“老太婆,你橫啥?告訴你,這車不能停!”
“為啥?”
“不為啥,這車就是不能停!”
“這車是你家的?你不讓停車,下車你賠我的假牙!”老太婆從前邊挪過來,就要往胳腮胡身邊擠。
“好啊,我賠你的假牙,你等著吧!”胳腮胡的鼻音很重,他哈哈一笑,眼睛直直地盯著老太婆。胳腮胡半睜半閉的眼睛里閃爍著一股邪光,讓人不寒而栗。
一車的人被震住了,幸災樂禍地等待好戲開場。
老太婆愣了一下,道:“你小子兇啥?老娘活了這一輩子,啥樣的人沒見過?我告訴你,你也是人生父母養的,要是別人對待你家老娘,你會怎么樣呢?別以為你在人前人后耀武揚威,你舍得像我老三樣,給你老娘買假牙不?!……”
老太婆看著胳腮胡,聲音變得更加急促有力,口氣咄咄逼人。胳腮胡沒有說話,只是用鼻子哼了一聲,以示不屑。
老太婆嘆了口氣,搖搖頭:“可惜我老三走了。老三在給人家打工,沒白天黑夜的干,到頭來老板不給工錢,老三帶著人去找老板討帳,不明不白讓人給打死了,我那苦命的兒呀!……”
老太婆喋喋不休,嘴巴里像塞進了什么東西,幽幽的聲音變成了嗚咽。祥子明顯感覺到,那聲音好像硬生生地從老太婆的嗓子里擠出來,一字一句咯得人的耳膜發脹,卻異常清晰:
“我老三就這么走了。這假牙是我老三留給我的唯一的東西呀,你說,我咋舍得就這樣把它扔了……”
老太婆聲音酸澀,一串淚從嵌滿皺紋的臉上滾下來。
肋腮胡腮幫上的肌肉有節奏的收縮了幾下,悄無聲息地坐下來。胳腮胡的目光早已從老太婆身上收回來,移到車窗外,專注地看著呼呼往后退的風景。
老太婆淚流滿面,嚶嚶抽泣起來:“我去市里省里找了十來年,他們你推我,我推你,把我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結果……”
車里很靜。除了兩個熟睡的孩子在均勻地打著酣外,一車人的目光都齊刷刷地集中在老太婆身上。
老太婆用袖子抹抹眼睛,臉上的皺紋里全是淚水,高聲叫道:
“快停車!不停車我就跳下去了!!”
老太婆從駕駛臺邊擠了過去,一只手扯著方向盤,聲嘶力竭地吼:
“停車!”
就在這一剎那間,車體發生了輕微的晃動,車上的很多人都驚叫起來。
祥子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看著淚流滿面的老太婆,樣子只覺得心里悶得慌,看樣子今天這例是得破一回了。當然,祥子這時候還不可能知道后面發生的事。要是這樣,他一定會說服老太婆放棄這種想法。
祥子緊緊握著方向盤,平靜地說:“你要干什么?等一下,我找個寬點的地方靠邊……”
祥子在應急車道上選好一個停車位,把車停了下來。
“去吧,去吧,你自己小心哈!”祥子呼地打開車門,高聲對老太婆說。
“唉,這老太婆!”
“瘋了,死老太婆!!”
車上的乘客顯然被老太婆的情緒感染了,但沒有人站出來阻止她的行動,只是小聲地嘀咕著。
在一車人埋怨的目光中,老太婆顫巍巍地下了車。
在高速路上停車,畢竟要承擔安全上的風險,還要付出時間上的代價。因此,老太婆下了車,有人就對祥子高聲嚷叫起來:“憑啥要在高速路上停車?簡直是拿這一車人的生命當兒戲!你讓這一車人等她一個,搞啥名堂?!”
“你們沖我發火,我沖誰發去?”
祥子顧不了這么多,兇巴巴地吼道。祥子拉開車門,跳下車去,把車門摔得山響。
祥子在車后五十米和百米處設置了兩道警示標志,回到車上和鬧嚷嚷的乘客簡單交代些安全注意事項,也跟在老太婆后面往前走。
車門一開,售票員秀兒就跟在老太婆后面。秀兒是祥子的侄女,大學畢業后沒找到合適的工作。祥子找到公司老總,讓秀兒給他打起了下手。
時值深秋,天藍藍的,太陽柔柔的,風也柔柔的。秋風像一把大梳子,吹得村上的葉一片片直往下掉。田里地里的莊稼都已經收割完,幾個農民正在扶梨趕種小春。見高速路上停了一輛車,都停下手中的活,伸長脖子希望能發現些稀奇事。
老太婆身體有幾分單薄,一手按住帽子,不讓風逞強;一手作自然擺動,一路小跑著。畢竟是上了年歲的人,老太婆沒有跑多大一會兒,就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吁吁地對秀兒說:
“閨女,閨女,跑不動了!”
“哎喲,累死老娘了!”
老太婆堆起了一臉討好的笑容,那氣喘吁吁中多少有幾分老女人的嬌羞。
“你要下來找呀?又不是我們讓你這么累的!”
“那是那是。”
“這么遠的路,上哪去找嘛?真是的!”
“找不到是我的事,我不要你賠!下來找一找,也算了了當娘的一樁心愿。我那老三,不易呀……”
“你就知道你家老三。你家老三關我們屁事!”剛出社會的秀兒非常善良,心里有啥說啥。秀兒嘟著嘴,沒好氣地說。
秀兒這樣一說,老太婆就沒話說了。
高速路上車真多。轟——,一輛過去了,轟——,一輛又過去了。見有人在高速路上逆向行走,過往的車輛老遠就按起了喇叭。有幾輛車從她們身邊過去的時候,駕駛員還扭過頭大聲向她們說著什么。車速太快,加上有風,什么也聽不到,但是秀兒知道一定是提醒她們注意安全什么的。
老太婆顯得很興奮,雙手輪換著按住帽子,盡最大努力擺著手臂,巔著腳一路小跑著。老太婆一心想著往前趕路,不管彎道直道,走著走著,就走到路中間去了。每每這個時候,秀兒就會拉住老太婆,把她往路邊推:
“危險!只能靠邊走,不能往中間去!”
到了最后,秀兒不得不攙扶著老太婆,讓她老老實實順著應急車道往回走。這樣一來,老太婆高興了。老太婆吧嘰著嘴巴:“閨女,你好像我們村里的菊兒。”
“瞎說。”
“你和咱菊兒一樣,長得又標致又水靈。”
“瞎說。”
“知道不,她爹是縣上的領導。她一直跟著她爹在城里讀書,都考上名牌大學了!每年跟她爹回來,看他的爺爺奶奶。那閨女和你一樣,好福氣喲!”
“瞎說,我哪有人家那樣的福氣。”秀兒只想早一點陪著老太婆了結她的心愿,根本沒心思和老太婆磨閑牙。
祥子一路罵罵咧咧,很快就越過了她們,遠遠在前面等著。看著綿延的公路,祥子很無奈:“這么遠的路,上哪去找嘛!”
祥子腦袋搖得像風車。祥子嘆著氣,求救似地看著老太婆。
“不怕,就在前面有棵大樹那一段,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先是有些咳,想吐痰……”老太婆非常肯定,一說又是打不住。
祥子拍著大腿,心急火燎地說:“天呀,你說那地方少說還有一公里!我那里還有一車人在路上等著吶!”
“嘿呀,這不都已經下來了嗎?就當我老婆子這輩子欠他們一個人情,求求你行行好,行行好!”老太婆滿是皺紋的臉上全是討好的笑。
“你不看看這路上的車流量。就是我們到了那里,你那寶貝東西肯定早讓車輾碎了,你還找個啥嘛?”祥子指著那一輛輛從身邊呼嘯而過的車說。
“就是碾成碎片,我也要撿一塊回來。要不,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心安喲!”老太婆神色嚴峻,一字一句地說。
“你去找你去找!!”
面對這個固執的老太婆,祥子搖搖頭,揮揮手。
祥子倚在防護欄上,扭過頭去,不再看這兩個人。祥子真后悔剛才做出停車這個錯誤的決定。可是事情到了這一步,大家就會預感到,故事快要結束了。
老太婆和秀兒在他的眼里越來越小。午后的太陽依然燦爛,走了這一段路,老太婆早已氣喘吁吁,額上掛滿了汗珠。
總算挪到了幾棵大樹那兒。老太婆低著頭,像電影《地雷戰》中鬼子探雷一樣,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趟著。
當然,老太婆什么也沒有找到。老太婆除了失望還是失望。
看著老太婆蹲在地上就不愿起來,祥子不得不趕快追了上前去。耽誤時間不說,老太婆這個舉動實在是太危險了。
祥子跑得氣喘吁吁,老遠就說:“老人家,這下心愿了結了,趕緊往回走,高速路上危險呀!”
“怪,怎么啥都不見!”老太婆全神貫注,只差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搜索了。
“幾百輛車過去了。你還想找你的假牙,做夢吧!”
祥子想著一車人在路上苦苦等著,心里多少有些幸災樂禍,巴不得老太婆早一點離開這是非之地。
“回吧!”秀兒說。
“回吧。”老太婆說。
“了掉這個愿,這下沒牽掛了吧!”秀兒說。
“了掉這個愿,這下心安了。”老太婆說。
老太婆嘆了口氣,那雙昏花的老眼卻一直在公路上逡巡著。
路邊有兩片剛吹落的樹葉,秀兒輕輕踢了一下樹葉,一塊暗紅色的東西就滾了出來。
“假牙!”
秀兒趕緊過去,拿出一張紙,包住假牙,遞給了老太婆。
老太婆一點沒有猶豫,拿起那塊假牙就要往嘴里塞。
“臟呀!”
秀兒跨過去,往老太婆手里奪。就這一瞬間,只聽見呯地一聲悶響,秀兒隨著呼嘯而過的車,轟一下飄了起來。
老太婆的眼前騰起一陣血霧。老太婆啊了一聲,那張嘴張成了一個大大的○。
假牙從老太婆手里落下來,啪——,成了兩截。
這一瞬間,祥子腦海里一片空白,嘴巴里不由自主地蹦出了這樣一個字:
天——!
夜診
竇一平醫生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關手機。
按理說下班和關機沒有關系,至少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在竇醫生看來,這是頭等大事,下班必須得關機。
其實,除了一下班就關機外,竇醫生還有一個特殊的嗜好:下午回家就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就連窗戶也用厚厚的遮光布緊緊捂住,生怕外面看見半點光亮。
對于這些怪異的舉動,當事人自己是不會在意的。可是別人就不會這么想了,別人往往會從這個舉止怪異的人身上找原因,從性格、愛好乃至家庭等方方面面展開聯想,進行分析論證,最終得出與遺傳個性修養乃至夫妻感情等有關的結論。
然而事實恰恰不是這樣。
竇醫生的性格非常開朗。讀醫學院的時候竇醫生一直是學生會成員,他會拉小提琴,尤其口琴吹得不錯。竇醫生除了喜歡看書外,特別喜歡體育,是他們系里為數不多的幾個籃球名星。只是參加工作后,體育項目大部分被國碎麻將所代替,同事們都熱衷于在牌桌上博弈,他的競技體育也就沒有無用武之地。工作之余,竇醫生喜歡帶著魚竿到水庫里釣釣魚,更喜歡帶著相機到處逛。盡管竇醫生照了成千上萬張他認為不錯的照片,但這些照片一張也沒有獲過獎,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在他的電腦里。
竇醫生的婚姻也很美滿。妻子和他是大學同學,兩個都在學生會,為了學生會的事一起搖旗吶喊,在一次次策劃和實施活動的過程中,就產生了愛情的火花。竇醫生和妻子說不上青梅竹馬,并且已經過了風花雪月的浪漫歲月,但二十多年的風雨歷程讓他們愛情的大堤異常牢固。竇醫生還有一個非常懂事非常優秀的女兒,還在京城一所名牌大學讀書,每天父女倆都會在QQ上留言。
縱觀竇醫生的人生軌跡,也有遺憾的地方。竇醫生當初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放棄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帶著他的妻子回到縣城,到縣醫院當上了一名醫生。風華正茂的竇醫生,自然很快就成了醫院的骨干。后來縣上鄉鎮搞改革,并鄉建鎮,竇醫生被組織上安排到一個中心鎮醫院當院長,為當地的老百姓服務。和同學比起來,竇醫生多少覺得有些窩囊。人比人氣死,驢比馬累死。當年大學同學大多都成了省市醫院的專家或骨干,很多人還走上了領導崗位,自己卻只是鎮醫院一個小小的院長,天天和灰頭土臉的農民打交道,這是竇醫生唯一的遺憾。
但窩囊也好,遺憾也好,和竇醫生的特殊嗜好關系不大。
準確地說,竇醫生的這些特殊嗜好,和一件看起來芝麻綠豆大的小事有關。
這一天晚上,當地村民送了一個危重病人到醫院來。人命關天,作為救死扶傷的醫生自然不敢怠慢。當時的竇院長立即帶著醫生搶救了三個半小時,還是沒有保住病人的生命。生老病死在職業醫生眼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因此,病人家屬在醫院里哭在醫院里罵,竇院長都沒有放在心上。可是,疲憊不堪的竇院長天還不亮就被病人家屬吵醒,幾十個人氣勢洶洶向他討要說法,他才感覺到問題多少有些不妙。
其實,這有啥好說的?病人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當時搶救的話還有一線生還的希望;從鎮醫院到縣上有兩個小時的車程,要是轉院在路上老人百分之百挺不過去。作為醫院,他們已經竭盡全力,并無半點過錯。
事情恰恰沒有這么簡單。人多嘴雜,病人家屬的情緒迅速發酵。他們用尸體作為籌碼,在醫院搭設了靈堂,問題不解決就不處理尸體。病人家屬從鎮醫院鬧到衛生局到縣上再到市里,再加上有好事者在網上一攪和,簡單的事情就復雜了。最后醫院賠了錢,竇一平被免職,調到這個偏僻的鄉醫院當上了一名醫生。
這樣的經歷讓人感到后怕感到委曲,作為當事人的竇醫生更是感到無比的寒心。
為這事,竇醫生想過不要這份工作,準確的說來是不想再干這個職業,不論是公立醫院還是個體醫院。但是,竇醫生畢竟是接近五十歲的人,這個職業畢竟干了二十多年,離開這個行當他已經一無所長,不干這個職業對于他來說就等于失業。因此,對這個神圣的職業,竇醫生除了厭倦,還是厭倦。
竇醫生下班就關機最簡單的動機與其說是圖個耳根清靜,還不如說是為了逃避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這個醫院不大,陳設也異常簡陋。這個名叫紅山鄉的地方,至今還沒有摘掉貧困的帽子。醫院就三個醫生,除竇醫生外,另外一個姓孫,本地人,當年頂班進醫院穿上白大褂的。盡管孫醫生是醫院的院長,但村民都知道他的底細,十天半月難得有人找他看病。孫院長也落得清閑,上班的時候主要是在醫院處理行政事務,實際也就是打打雜,下了班也就回家了。孫院長下了班比上班還忙,他已經有了三個孫子,家里老婆根本就顧不過來。還一個醫生姓陳,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大學生。陳醫生的女朋友在縣城,兩人正處于熱戀階段,他也就騎著摩托到處溜經常不在醫院。
當初縣里調竇醫生下來的時候,領導明確說過,這只是權宜之計,那場風波平息過后就把他調回縣醫院。可是,后來縣上要調他回去,竇醫生死活不愿意離開這個地方。竇醫生覺得這里遠離塵世的喧囂,是一塊難得的世外桃源。竇醫生自然成了這個偏僻鄉醫院的頂梁柱,開處方,拿藥,打針,甚至做一些小手術,全是他一人包干。好在鄉下病人不多,他一個人也完全對付得過來。
對于這些病人,竇醫生是完全有把握處理的。病人即看即走,偶爾需要輸點液,那也是在下班前處理完畢。稍有疑慮或病情危重的病人,竇醫生都會毫不猶豫地作出決定:
轉院!
竇醫生下班吃過晚飯,做的事就是到醫院后面的山上散散步,遇上干農活的老漢或放牛的牧童,也會湊上去和人家搭搭話,吹吹閑龍門陣,偶爾開幾句無關緊要的玩笑。竇醫生下午散步回來,遮光的窗簾唰地一拉,就把自己和整個世界隔絕開來。竇醫生這時候就專心致志地做兩件事:練書法和在網上下圍棋。醫院里訂了一份省報兩份市報和一份醫藥報,全讓竇醫生練習書法派上用場。天長日久,竇醫生的書法技藝大有長進,盡管開出的處方外人仍然無法看懂,但對那一手飄逸灑脫的狂草他自己還是滿意的。竇醫生喜歡上網,在網上看看新聞,和女兒聊聊天,但更多的時候是在網上下圍棋。等他下完一到兩局棋,已經是午夜時分,到該睡覺的時候了。當然,竇醫生也不是將手機一關了之。每天睡覺前他也會開機給老婆和在讀大學的女兒發發信息,報報平安,編一些晚安祝福一類的短信。
不過,即使如此,也難保下班后就沒有來打擾他。
比如今天,他正在網上下圍棋,醫院大門外就有人叫門:
“竇醫生,竇醫生!”
是一個女人。女人的聲音尖而細,聽起來非常急迫,幾近哀求:
“竇醫生,我媽不行了,麻煩你去看一下!”
“辛苦你一下嘛,竇醫生,竇醫生!!”
這幾天到處都灰蒙蒙的,一連幾天都在下雨。下午雨停了,但路上仍然泥濘難行。加上入冬后溫差大,一下雨外面就冷嗖嗖的。竇醫生吃過晚飯哪里也沒去,關上門練練字,就躲在屋里上網。
外面的女人顯得異常有耐心,一聲接一聲,不依不饒地叫著:
“竇醫生!竇醫生!!”
竇醫生連大氣都不敢出,眼睛盯著電腦屏幕,一聲不吭。
外面的女人大慨覺得主人不在,叫了一陣終于停下來。
竇醫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農村人大都是這樣,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愿意到醫院來的。這個時候來請醫生,說明病人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甚至已經到了生死邊緣。一旦出診,萬一發生意外就糟糕了!按理說,醫生只要盡了力,生也罷死也罷責任就不在醫生頭上,可是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怎么和病人的家屬扯得清呢?畢竟已經不是赤腳醫生的年代,死個把人很正常,現在要是出了問題,誰來承擔這樣的責任?……
一想這到些,竇醫生就覺得頭皮發麻。
可是,僅僅過了五分鐘,女人的聲音又從醫院后面,也就是竇醫生寢室旁邊清晰地傳了過來。
看來女人對他的行蹤掌握得一清二楚。這一次,女人的聲音顯得更加清晰,更加急迫:
“竇醫生!竇醫生!!”
“竇醫生,我媽快不行了,求你行行好,去看一下我媽!你就是去看一眼,我們一家人也記得你的大恩大德呀!竇醫生——!”
女人急切的聲音像鋸子一樣鋸著竇醫生的神經,讓竇醫生覺得異常痛苦。竇醫生眼睛雖然還盯著電腦屏幕,但此時他早已亂了方寸,讓對方找到漏洞,使得他連失幾子。不用說,這一局棋是輸定了!
女人哀求的聲音一聲比一聲高。
盡管竇醫生的心里非常矛盾,但他始終咬著嘴唇,不敢應聲。
理智告訴竇醫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有事。再混十來年就可以退休拿養老金了,自己何必再冒這樣的風險呢。何況被蛇咬過一次,還希望被咬第二口嗎?
女人急切的聲音在靜寂而空曠的大山里跌來蕩去。
夜,死一般的靜寂。女人明顯感覺到就這樣叫下去也不會有什么結果。絕望之余,女人把滿腔的怒火一下發泄了出來:
“姓竇的,我操你祖宗,你還是個醫生嗎?!”
“呸,我操你竇家十八輩祖宗!你狗雜種裝聾作啞,你枉自背了個醫生的皮!你死了算了,狗雜種!!”
女人拖著哭腔,連哭帶罵的聲音漸漸遠去。
醫院又恢復了往常的寧靜,可是竇醫生的心卻無法平靜下來。其實,每到這個時候是竇醫生最難受的。一旦晚上有人叫門,盡管他沒有去出診,他必定失眠。
那局棋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竇醫生關了電腦,從床頭柜上拿出安眠藥,吃了兩顆,靜靜地躺在床上想心事。
自己是醫生,卻在病人最需要醫生的時候,作為救死扶傷的白衣使者,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出現在病人面前,這到底是為什么?!竇醫生感到無比的痛苦,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望著天花板發呆。
夜,靜得磣人。外面起了風,冷風呼呼地從破窗欞里刮進來,讓竇醫生連打了幾個寒噤。
時針已經指向凌晨一點。竇醫生雖然吃了安眠藥,還是半點睡意也沒有。就在這時,大門外又有人在叫門。
這一次是個男的,聲音低沉渾厚,但仍然顯得十分急切:
“竇醫生,竇醫生!”
“竇醫生,請你開開門,幫幫忙啊!”
老天爺,這天晚上是怎么了?竇醫生痛苦地搖著頭,用手緊緊捂住了耳朵,他只覺得雙腿因為緊張而微微有些發抖。
可是,這一切都無濟于事。醫院的房子太舊,外面有什么響動都能清晰地傳進來。男人叫了幾聲后,開始用力地啪門:
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
醫院的大門是鐵皮做的,在空曠的夜里那響聲震耳欲聾。
竇醫生的內心感到無比的煎熬。竇醫生的腦子里像一團亂麻,怎么也理不出頭緒:病人和病人家屬是弱勢群體,該保護;但是醫生誰又來保護呢?問題是再出一回事,自己可能就連飯碗都保不住了!竇醫生痛苦地想,與其這樣折磨自己,這樣的飯碗拿來干什么呢?!
男人拍了半天不見動靜,又放聲喊起來:
“竇醫生,竇醫生!”
“竇醫生!竇一平,竇一平!!”
竇醫生一下坐起來。這聲音萬分熟悉。不錯,是趙大友的聲音。趙大友是竇醫生高中同學,年長他幾歲。那時趙大友是班長,大哥哥一樣照顧著竇醫生。趙大友高考落榜,回到老家烏地吉木務農。時至今日,趙大友那憨厚質樸的形象還深深地烙印在竇醫生的腦海里。
“一平,一平,我是趙大友,你開門,老哥有事求你啊!”
果然,趙大友報出了自家姓名。
竇醫生被貶到鄉醫院,趙大友聽說后專程到醫院看過他。二十多年的風雨滄桑,昔日的同學已經找不到過去班長的蹤影了。趙大友看上去比竇醫生至少蒼老20歲,天天和土地打交道,早已讓太陽曬得黑不溜秋,和當地農民沒有什么兩樣。因為地位的懸殊,兩人已經有了很深的鴻溝,更找不到合適的話題。趙大友拿出一包煙,撕開,抽出一支遞給竇醫生。在遭到竇醫生的回絕后,趙大友把那只煙塞進煙盒,自己抽起旱煙來。兩人擺談了一會兒,趙大友留下兩只自家養的雞就回去了。
外面趙大友那急切的聲音仍然在夜空中回蕩。
竇醫生再也躺不住了,他翻身起床,趿上鞋,手扶在門把上。竇醫生只覺得呼吸急促,那顆劇烈跳動的心像要從胸腔里蹦出來。
理智又一次告誡竇醫生:不能沖動,更不能去!就在去與不去的選擇之間,竇醫生居然硬生生地憋出了一通毛毛汗。
外面,趙大友呯呯呯拍打鐵門的聲音又響了起來,惹得遠遠近近的狗也跟著狂吠個不停。
竇醫生長嘆一口氣,終于拉開了門。
作為一個職業醫生,他實在無法忍受這樣的折磨。
天陰沉沉的,刺骨的寒風中還夾雜著細碎的雨星。竇醫生一出寢室就連打了幾個寒噤,他打開鐵門,把趙大友讓了進來。
這一切,都用不著解釋。
剛才的女人是趙大友的姨妹。趙大友的岳母得了急病,要請他夜里出診。竇醫生問了問病情,直截了當地說:
“怎么不打120,送縣醫院呢?”
“下了幾天雨,到縣城的路斷了,120急救車無法到鄉上。只能來麻煩你了!”趙大友苦著一張臉,連連嘆著氣。
竇醫生不好再說什么。竇醫生到鄉醫院已經有幾年了,但準確的說來在夜間出診他還是頭一次。過去無論晚上病人把醫院的門拍得多么響,他都不會搭理的,因此那只急救箱早已閑置不用了。竇醫生一邊問著老人的病情,一邊找出早已經閑置的急救箱,飛快地把急救的藥品和器械往里面塞。
竇醫生加了件毛衣,和趙大友一道上了路。
趙大友和岳父岳母都住在一個名叫烏地吉木的寨子。彝漢雜居,山高坡陡,晚上泥濘的路就更加難走。
竇醫生深一腳淺一腳趕到烏地吉木,已經是凌晨3點半了。
竇醫生冒著一頭熱汗,一進門就直奔房間徑直到了病人的床前。
老人已經深度昏迷,氣若游絲。憑經驗,病人已經游離于生死邊緣,不立即施救,隨時都有可能停止呼吸。
竇醫生退出病房,立即拿出藥具。
在那盞白熾燈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竇醫生的身上。屋里很靜,靜得連竇醫生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聽得清清楚楚。
竇醫生神色嚴竣。他一邊做著準備,一邊對滿臉堆笑的趙大友說:“大友,我一定盡自己所能。咱先說斷后不亂,老人病情十分嚴重,萬一有啥閃失,你可不能怨我!”
“那是那是。”趙大友一個勁地點著頭。
“你找紙筆來,咱們先簡單寫個協議。”竇醫生只覺得嗓子發干,說話異常費力。
“一平,你信不過咱?”趙大友一臉的疑惑,外星人一樣盯著竇醫生。
“哪里話?我也是沒辦法!”
竇醫生說的是實話。前段時間鄉下有家媳婦得了急病,請街上的個體的醫生晚上出診,結果病人沒搶救過來,家屬卻扭著醫生鬧了幾個月,到現在那家診所的門還是關著。作為醫生,誰也不敢保證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得好,一旦出了事,誰又來保護醫生呢?
“唉,你還是信不過我們。”
趙大友有些失望,那顆花白的腦袋搖得像風車一樣,無助地看著竇醫生。
“你沒見病人要上手術臺前,醫院都得讓病人家屬簽字么?”竇醫生總算找到了這樣一個理由。
孩子在鎮上讀初中,平時住校,周末才回來,家里哪有現成的紙和筆。竇醫生有些后悔,來的時候就應該帶一本信箋來。他甚至還想,今后還得印些現成的文本材料,到時候簽名按手印多方便。
竇醫生麻利地做著各種準備。竇醫生已經開好處方,取出針筒,拿出針水,用手術鉗卟卟卟一陣敲,吱吱地吸進針筒。手術鉗上也夾好了酒精棉球。一切都已經就緒,就等著簽協議了。
要命的是找不到紙和筆。趙大友在屋里找了一陣,從柜子里箱子里抽屜里騰起一陣嗆人的煙塵,就是找不到這兩樣寶貝。
“算了,就用處方箋吧!”
此時,竇醫生也很急。可是理智再一次告誡他,千萬不能亂,該走的程序必須得走到!
竇醫生把剛才寫的那本處方箋,連筆一起遞給了趙大友。
就算是文思敏捷的人,到了這個緊要關頭也不一定寫得出來,何況是天天和土地打交道,20多年幾乎沒有摸過筆的趙大友,那筆好像千斤重,不知道該如何下筆。竇醫生已經急出了通毛毛汗,在他的口述下,趙大友才歪歪扭扭寫好那份內容非常簡單的協議。
這是一份名副其實的生死狀。
沒有印章,不可能按手印。趙大友哆嗦著手,吃力地簽著他的名字。
問題是趙大友還沒寫完他的名字,房間里已經響起了一片哭聲。
首先反應過來的是趙大友,他把手中的筆一扔,就往病房里奔過去。
里面的哭聲一聲高過一聲。
下半夜的氣溫更低,冷嗖嗖的風從破舊的門里灌進來,讓人感覺到無比的冷。屋里異常安靜,除了病房里有哭聲外,仿佛世界都已經凝固了。
突然,病房里的門一下扯開了,趙大友一步跨了出來,瞪著血紅的眼睛,直直地盯著竇醫生。趙大友什么也不說,掄起巴掌,就給了竇醫生一記耳光。
啪——!
空曠的夜里,那一記耳光異常響亮。
趙大友喘著粗氣,哆嗦著嘴唇,整個世界似乎就這樣凝固了。
竇醫生一下怔住了。竇醫生只覺得身子一矮,眼淚一下涌了出來。
“你以為我想這樣嗎,我也是沒辦法呀!!”
竇醫生踉蹌著走進病房,跪在老人的床前,號啕大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