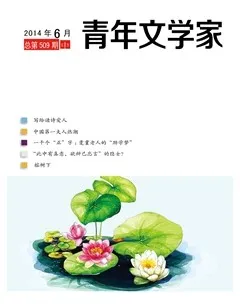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隱士?
姚丹丹
他,仰面長吁“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成為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一個精神歸宿。然而,紛繁混亂的時代及個人性格等因素,使得他終究不能如愿而選擇辭官歸隱。喜歡魯迅先生對他的評價:“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歷朝歷代的文人雅士、掮客學者把他贊頌,予以真隱士的美譽,只是,陶淵明也不過是個凡人而已,有著凡人的喜怒哀樂。讀他的詩作,我并未聽到所謂的真隱士的自豪聲,相反是一陣陣將內心繾綣的戀仕思緒隱藏于“采菊東籬,悠見南山”背后的哀嘆。
陶淵明的思想頗為復雜、矛盾:他既熟諳儒家學說,有著積極入世的精神;又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安貧樂道、崇尚自然。用一句話概括——通過泯去后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兩種不同思想的交織、糾纏,以及晉宋易代之際復雜的政治環境,使得他在進退中做著艱難的抉擇。從“猛志逸四海”到“猛志固常在”,可以看到陶淵明也曾胸懷建功立業之志,但仕途的挫敗以及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讓他倍感失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他看到了百姓的疾苦,但無力改變;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挽救的途徑。他企圖開出一劑醫治社會的良方,可他哪里知曉詩境里的藥方對現實世界的治愈是無效的。《桃花源記》展示了美好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的烏托邦,但那只是一個幻境,救不了陷入苦難中的自己,更救不了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于是,退隱歸耕,這何嘗不是先生對社會黑暗統治表示不滿和反抗的異樣方式?
一著“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讓《歸去來兮辭 并序》成為陶淵明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詩人憑借豐富的想象,描繪了歸途、享天倫之樂、躬耕勞作等情景。倘若說這些是詩人運用高超的藝術手法來表達對自由的向往,我則不以為然。在我看來,這不過是詩人理想被現實阻隔、擊潰而進行自我寬慰的華麗借口。盡管“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的自然景觀令人憧憬,可我更愿思考:景致如此美好,詩人內心的苦楚到底有多沉重?對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落差到底有多失望?那“恨晨光之熹微”“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中的“恨”“復”二字究竟隱匿了先生多少撕心裂肺的苦苦吶喊?
《歸園田居》五首大約是先生辭彭澤令歸田次年的作品。歷來讀過這幾篇作品的人士都不約而同地下著結論:辭官歸田后的陶淵明居清靜平淡的農家生活,享天倫之樂,心情是愉快、閑適的。可我并不認同。若先生真如那般,又何須反復詠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難道先生不懂這“韻”或許是適合世俗的性情?難道先生不懂這“塵想”或許是世俗的念頭?又難道是先生不懂這“衣沾”或許是棄官歸耕必然會遭到一定困難的象征?我想先生是懂得,而他之所以如此高聲地吶喊,是內心的不甘、失望及不敢面對現實、逃避現實的恐懼。如果沒有一顆入世、建功立業的心,他又何曾苦苦掙扎于“一去三十年”的塵網不能自拔?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飲酒 并序》其一)看似借用秦東陵侯邵平不相同的兩種處境來說明人生的衰榮不定,用以勸誡世人應達觀對待富貴禍兮,實則是他借飲酒抒寫情懷,將那不能實現的愿望同失望隱匿于清靜、安適的田園生活畫卷中。又如《詠荊軻》中,荊軻“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的不可戰勝的氣魄與無畏精神,“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的視死如歸的氣魄,都是先生對他不畏強暴的俠義行為所作的歌頌,荊軻甘愿犧牲自己救燕,只因遇到知恩太子丹。先生又何嘗不想效仿荊卿,然而他的太子丹又在哪呢?他悲嘆,他退出仕宦的洪流,只便將那份崇高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對荊軻的贊頌中。再如“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如果說顯示了解記述古代神話傳說及海內外山川異物的《山海經》是出于興趣,那么讀《周王傳》呢?僅僅是出于自己的一番興趣而已?追憶周穆王駕八駿西征,是先生對當時政治的別樣審視和評價。那個紛亂的時代需要有人來終止,那個暴動的社會需要有人來整頓,他渴望有一個“周穆王”的出現,更渴望被這樣一個“周穆王”所賞識、任用,以實現自己的“留有后世名”。然而,先生又是多么“笨拙”的一個理想主義者,現實與理想的對比帶給他巨大的沖擊,對現實、現世的徹底失望,迫使他不得不將美好的政治理想和情愫寄于歸園田居的生活中,埋葬于自己的詩篇里。
再觀陶淵明的詠懷、詠史詩,也有著其獨特之處:始終圍繞著“出仕”與“歸隱”的中心,矛盾心理隱蘊其中更是不言而喻。《雜詩》其二中,將素月分輝、秋風微涼的清景與歲月拋人、有志未騁的悲慨打成一片,從而展現自己人生境界復雜的一面。“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更是他思想中非靜穆、不平衡一面的深刻顯現。“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如果真如詩句所言般淡泊明志,那么早已心平如水的他何必多此一舉,向世人反復聲明自己的“無仕之心”?
一個在官場中失意的落魄文人;一個有文采、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一個在生活上有情趣,懂快樂的人。陶淵明,作為身處亂世的士人,盡管有著恬淡靜穆的外表,但他也曾心懷鴻鵠之志,渴望建功立業。可惜,處于朝代更替之際復雜的政治環境,處于那個重視門閥的社會,他無法讓自己跟隨時代前進的步伐,無法讓自己在保持本質真的同時又適應社會的風云變幻,他的仕途結局注定是失敗的、失望的、傷感的,他也只能選擇歸隱田園。而那些所謂的閑適的、愉悅的歸返自然的歡暢,何曾不隱隱透出一絲哀傷、一絲凄涼?
當耳畔再次響起“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等陶詩時,誰能覺察與體會到先生那隱于詩背后的無奈與繾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