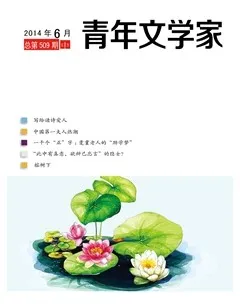文革時期的“豬”與“麥兜”豬
摘 要:王小波和馮唐都是北京當代作家。二者有很多有趣的相似點,如都在體制外游離,追求文字的趣味和對寫作以及對歷史獨特的態度。王小波的雜文名篇《一只特立獨行的豬》通過對文革時期“豬”的描寫體現了作者的大膽、叛逆以及思想的鋒芒;馮唐在雜文集《豬和蝴蝶》中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審美體驗,面向世俗給我們呈現了“麥兜”豬的生存哲理,提升到了“道法自然”的境界。
關鍵詞:王小波;馮唐;雜文;“豬”意象
作者簡介:董曉霞(1987-),女,云南騰沖人,臨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助教,西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敘事文學。
[中圖分類號]: 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02
一、特立獨行的意象選擇
提到文學中的“豬”形象,自然會想到《西游記》中的豬八戒,它貪食、貪睡、貪色、貪利,這些都是凡人本性。如果說,明代創作者吳承恩在作品中表達了對豬八戒凡人本性的嘲諷。然而在當代社會尤其是后現代思潮所宣揚的解構崇高,消解神圣批評視野下,豬八戒堪稱一個真正能夠無視神權、無視皇權,只專注于個體生存需要之滿足的文學形象。時隔幾百年,王小波和馮唐用他們的智慧之筆再次給我們呈現出了極富個性魅力的“豬”意象。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可以說是王小波雜文中最具有特色的一篇。文章以“文革”為背景,敘述了“豬兄”的故事,描寫了它種種不可思議的行為。“豬兄”不服從組織給它安排的主題生活,即長肉,并逃脫被閹的噩運成為“花花公子”。后又學汽笛叫,被認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這種行為引起“領導們”的憎惡并要對它采取專政手段。而最后,它在機警敏銳的躲閃后成功逃脫,成為一個流傳的“神話”。“豬兄”之所以“特立獨行”,是因為它敢在特殊時代背景下張揚自我與反抗權威。當時的生活環境是充滿了教條刻板、充滿了規約限制、缺乏生氣活力的環境——“文革”。王小波在雜文中一再批判、反思這個壓抑、禁錮、混亂、荒謬的年代。那是一場 “集體性的癮癥”,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魔,是一個“狂信”導致偏執而無理可講的年代。“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么消遣” 。他直言“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 在這樣充滿了枯燥的單調和窒息的遏制的情況下那只“ 特立獨行的豬” 就顯得瀟灑而無畏。它“長得又黑又瘦, 兩眼炯炯有光”,“ 像山羊一樣敏捷”,“它只對知青好,容許他們走到三米之內,要是別的人,它早就跑了”,“吃飽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頂去曬太陽或者模仿各種聲音”,“總而言之,所有喂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1]這是一只“不像豬” 的豬,豬應該有豬樣,肥胖、墉懶、愚蠢、聽話,這是人類為其設置的生長方式,只有遵守這種生活方式的豬才是正常的豬。而這位被王小波尊為“豬兄”的豬,完全違背了固有的認知方式,它的“瀟灑”正是一種自由的精神狀態,是不畏強權、灑脫自然、無拘無束的生命本真形態。
比起王小波筆下的“豬”在“文革”中的“特立獨行”,馮唐筆下的“豬”就顯得可愛而親切。馮唐沒有像王小波一樣通過故事情節給豬賦予傳奇色彩,只是在雜文中提到對現實中的豬和香港漫畫中小豬“麥兜”的喜愛。在《小豬大道》中他這樣寫道:
豬和蝴蝶是我最喜歡的兩種動物。我喜歡豬早于我喜歡姑娘,我喜歡蝴蝶晚于我喜歡姑娘。豬比姑娘有容易理解的好處:穿了哥哥淘汰下來的大舊衣服,站在豬面前,也不會自卑。豬手可以看,可以摸,還可以啃,啃了之后,幾個小時不餓。豬直來直去,餓了吃,困了睡,激素高了就拱墻壁,不用你猜她的心思。豬比較胖,冬暖夏涼,夏天把手放到她的肉上,手很快就涼爽了。[2]
如果說王小波筆下的“豬”繼承的是豬八戒人性的一面的話,那么豬在馮唐筆下則體現了豬八戒的豬性,或是一種自然屬性。但作家并不拘于表面,他有提升的才智。馮唐在翻完四本“麥兜”后更堅定了對“豬”的喜愛。在香港漫畫家謝立文、麥家碧筆下的“ 麥兜和麥嘜”圖書中,麥兜的人生故事很平常,上學、工作,希望、失望,他都一一經歷。雖然麥兜資質平平,卻有很多夢想,然而一次次遇到失敗。但麥兜還是憑他正直善良的“死蠢”創造了他美麗的世界。麥兜或許傻,或許笨,或許慢,在人生的追求中屢屢嘗試屢屢失敗,但他卻把生命過得自自然然,像在做一件簡單的事。麥兜生活在低處,麥兜們天資平常,出身草根,單親家庭,摳錢買火雞,沒錢去馬爾代夫,很大的奢望是有一塊橡皮。麥兜不僅是一只豬,而且是一只生活在低處的豬,一只飽含簡單而低級趣味的豬,一只得大道的豬。麥兜們說,“沒有錢,但我有個橙。” 因為麥兜不完美,像我們每一個人。他的希望,讓人看了喜悅,他的失望,讓人感同身受。馮唐因為麥兜麥太說,“我們現在很好。”“我們已經很滿足,再多已是貪婪。”而觸動,這是成人的童話。
二、小豬大道
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中把豬稱為“兄長”,從感慨“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來肯定豬的優秀,到幻想揮舞雙刀和豬“并肩作戰”,他為我們展示了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如何逃離秩序和規則。王小波使用慣常的調侃性語言,正反顛倒,雅俗錯位,對文革時期革命話語有意地復制和嘲弄,更是產生了強烈的反諷、解構效果。骯臟粗鄙的“豬”、“牛屎”、“糞坑”,對比高高在上的“指導員”、“軍代表”和各種革命話語,狂歡化的語言后面是荒謬的時代悲劇。而領導們認真嚴肅的召開大會討論一只豬,并將其定為“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采取專政手段”的煞有介事和振振有詞,更是徹底瓦解了政治權威的神圣和莊嚴。縱觀王小波的創作,這只豬亦是他寫作姿態的代言。在充斥著“沉默的大多數”的年代里, 王小波選擇“說話”,勇敢挑戰所有的“愚昧”、“無趣味”、“迷信” 以及“莊嚴肅穆的假正經”。他堅持“戰斗”,這樣的戰斗姿態正是背向世俗文化的高蹈獨立。
在《豬和蝴蝶》中馮唐說:“麥兜得了大道。麥兜做了一個大慢鐘,無數年走一分鐘,無數年走一個時辰,但是的確在走。仿佛和尚說,前面也是雨,在大慢鐘面前,所有的人都沒有壓力了,心平氣和,生活簡單而美好。麥兜沒學過醫,不知道激素作用,但是他總結出,事物最美妙的時候是等待和剛剛嘗到的時候。這個智慧兩度襲擊麥兜,一次在他的婚禮上,一次他老媽死的時候上。”[3]馮唐對豬及麥兜的贊美或認同其實反映了道家“道法自然”的哲理。
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為“道”是依據自然之法而存在,即“道”之存在及生成是依據自然生態之法,因而是道法自然。老莊所說的“自然”并不僅僅是指實體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種狀態,指生命存在的本然狀態。馮唐認同麥兜飽含簡單而低級的趣味,這個“低級”是人的一種普遍存在模式,生命本來就是這樣,真實而細微,具體而瑣碎,應像麥兜一樣把生活過的自然而又踏實。馮唐的“道法自然”觀念如王小波的“特立獨行”姿態一樣在其雜文中得到了呈現。相對于王小波別有意味的“有趣”,馮唐對文字有趣的營造就顯得低俗而市井。因為馮唐相信:在無聊中取樂,低俗一些,這比較接近生命的本質。這也體現了他對“道法自然”境界的追求。讓一切自然地運變流行,不假造作,自由自在,其雜文文字曼妙、才情燦爛。如在《你到底愛不愛我》中說:“我終于明白,英雄末路、美人遲暮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更加痛苦的是和英雄美人最親近的人。”[4]而在《掙多少錢算夠》中的“大奢,我不敢,畏天怒。吃龍肝鳳髓,可能得非典,請西施陪唱卡拉OK,我聽不懂杭州土話。”[5]如果說王小波是一個走著的思想者,那么馮唐就是坐著的論道者,“道”表達的是對文學藝術、對日常生活的見解,折射著他思想的鋒芒。
參考文獻:
[1]王小波.思維的樂趣[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3][4][5]馮唐.豬和蝴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173;175;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