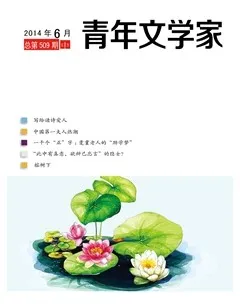論顧城詩歌親近的陌生化
摘 要:“童話詩人”顧城的創作受童年經驗的影響,以童心體悟世界,其詩歌中的視角、意象、語言都具陌生化特點,但陌生化中又具有源自大地與生活的親近感,展現了“童年質情節”的詩人對世界的體悟。
關鍵詞:顧城;童年經驗;陌生化
作者簡介:盧貝貝(1990-),女,廣西河池人,廣西大學文學院文藝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理論。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02
顧城是保持著童心而“拒絕長大”的“童話詩人”,他在論及朦朧詩時提到:“用小孩子的方式來表達痛苦期待,這所經歷的感情瞬間,和人類遠離的天真時代無意相合”[1]167。顧城用孩子的方式來表現詩歌,這與其童年經驗有密切聯系。年少的顧城隨父親下放到渤海的村落,“喂豬是我們父子流放生涯中最大的樂趣”[2]2,童年經歷被顧城有選擇的保存于腦海,并對其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個體一旦從環境中獲得安全、愛和地位,個體的發展才開始。“每個人以自己的獨特形式開始發展,這時的發展就變得更加依賴內部而不是依賴外部[3]29”年少的顧城融入到自然中并開始個體的發展,這種發展在主體的內部凝成詩歌。這使顧城保留如孩童一般對人生、環境如初見的驚奇感,這份驚奇感以陌生化體現在詩歌中。
一、視角的陌生化
顧城詩歌的陌生化并非刻意斧鑿,而是童心、驚奇感的外化。但不能否認顧城對陌生化手法全然不知,在20世紀初,俄國形式主義家什克洛夫斯基在論述陌生化時稱:“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4]6。藝術陌生化技法使感受主體對事物的感覺即為所見的視像,而不是已知的事物。顧城詩歌所展現的正是對事物猶如初見般的新奇,而非早已為人們熟知的天地。
由童心生發的驚奇感,使詩人以陌生的角度焦距事物,從不同側面了解世界。在《眨眼》中,以那個“錯誤的年代”為背景,描述“我”眨眼后的錯覺。作為特殊時期的見證者,詩人并沒有焦距暴力沖突場面,而是被鮮亮的彩虹、紅花所吸引,彩虹與蛇影是兩個差異極大的意象,彩虹鮮艷,蛇影危險,在那個“錯誤年代”里,真實的彩虹與錯覺的蛇影,哪個才讓詩人“目不轉睛”?在特定環境下產生的錯覺往往直達更高層次的真實。詩人焦距于孩童所喜愛的彩虹,繼而發現錯覺中的蛇影。以這樣陌生的角度展現特殊時期真假顛倒的荒謬,延長讀者的感受過程,在揣摩真實與錯覺的置換中獲得陌生化體驗。
二、意象陌生化
朦朧詩的朦朧之處在于通過象征手法促成意象的陌生化,顧城擅長組合看似意料之外的意象群,但回歸詩歌卻發現意象群又在情理之中。在《早發的種子》中,“種子”與“炮火”、“小旗”和“軍營”等密集的軍事意象聯系,硝煙彌漫,氛圍徒然緊張,早發的種子猶如加入一場反抗寒冬的斗爭,在寒風中揮舞旗幟、沖鋒陷陣,而早發的種子是孤獨的戰士,在春寒中夭亡,早發的種子是為了春天的信仰而戰斗犧牲的無名英雄。嫩芽本給人纖弱之感,而與陌生的軍事意象組合,則被塑造成前線的“列兵”,無畏前行,使人耳目一新。
意象是融匯創作主體意趣的形象,顧城詩歌中意象群組合的特點是超越一般人的思維習慣,意象群不僅是圖像式的呈現,還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情感的復雜經驗,”是“各種根本不同觀念的聯合”[5]202,這使意象有豐富的內涵和表現方式,通過暗示和象征等手段讓讀者領會意象群聯系,感受意象的時間被延長,在陌生化中重新認識意象,獲得詩歌審美體驗。
三、語言陌生化
日常語言是一種傳達工具,而詩歌語言則是對標準語言規則的違背。形式主義文論認為,為強化詩歌的可感性,對自動化的語言進行革命,“通過疏離、變異等陌生化手段,使語言變形、扭曲、反常化”[6]156,顧城的詩歌語言是清新、純凈的,并非粗暴地摔打語言再重新組合,其語言陌生化主要體現在簡潔而多義,看似稚語卻不乏深意。
顧城的詩歌句式短小,韻腳流暢響亮,語言天然純凈。這與政治口號式的詩歌形成鮮明對比,語言清新如春風拂面,柔軟人心,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安慰》是簡明易懂的童話詩,是孩子對媽媽的安慰,也是理想對現實的安慰,在黑夜里,成人為生計為物質煩惱,孩子則想到早晨的紅太陽能讓生活變暖變甜,盡管生活清苦,但理想照亮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紅太陽”用“甜甜的”修飾,使代表希望意義的太陽增添了味覺,甜的不僅是太陽,也將是媽媽發愁的心。在語言的運用中,顧城通過天馬行空的想象使語言陌生化,顯示他作為“孩子”的奇思妙想。“影子從他們身體里流出/我是從一盞燈里出來的”(《分布》),影子是光線投射的結果,在詩人筆下,僅用動詞“流出”就賦予影子液體的質地,朦朧詩的多義是語言陌生化的結果,顧城的奇異想象使內心生發的詩歌語言脫離大眾化的語言模式,使人擺脫機械化閱讀,使語言重新成為審美對象。
四、親近的陌生化的實現
若一味追求詩歌陌生化而任意肢解語言,則陷入難以解讀的危險,成為艱澀的能指鏈。而親近化則是“對不必要的變形進行抵制,同時對原始語言的瑣碎和蕪雜進行刈除,以最低限度的變形取得最大限度的詩意效果”[7]8。詩歌中的親近化與陌生化是一對相互作用的力,使詩歌既有生活氣息又蘊含藝術魅力。顧城詩歌的陌生化沒有遮蔽親近化,這源于詩人的本真童心對生命的真切體驗,其詩歌扎根于民間土壤,貼近大地。
首先,陌生視角距離讀者不遙遠,這是人在童年時期認知事物時都經歷的奇異旅程。成人習以為常的事物在兒童看來是未知、全新的,顧城詩歌以陌生角度焦距事物是相較于成人的自動化、機械化視角而言,而人與物的視角交換,能喚起讀者的童年記憶,這是對成年人暌違已久的童心地深情召喚。其次,陌生化組合的意象群來自生活。意象的陌生在于看似不相干的意象群組合,它們不是用變幻莫測的意象堆積嚇唬讀者,意象群有著內在的、深刻的聯系,它們有著同樣的指向,朝同一方向運行,以便在詩中形成整體組合。顧城詩歌的意象是尋常物,“雨水”、“種子”詩人以心取象,親近親切。另外,陌生化的語言貼近童語。語言的陌生化是在陌生的視角、意象以及孩童般的想象的基礎上形成,也是較于特殊年代的政治語言而言,但詩人向生活與心靈探索,童真與深刻結合,語言天然純凈,看似稚語又不乏生命體驗的哲理。
詩歌的陌生化與親近化如浮力與重力,使詩歌藝術高于生活又不脫離大地,二者之間的張力之弓拉得更大,射向讀者之箭就更有力。顧城因其“一念之本心”對世界保留著孩童般的驚奇感,詩歌是其心靈的真實寫照,這個“始終沒有長大的孩子”一如他的詩一般,對這個世界親近而陌生。
注釋:
[1]顧城.大游戲小人間[A].趙毅衡,虹影.墓床[C]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顧工.顧城和詩(代序)[G]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3] A·H·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M].李文湉,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4]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手法的藝術,見《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G].方珊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
[5]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譯.北京三聯書店,1984.
[6]周瑞敏.詩歌含義生成的語言學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7]李凱霆.詩歌語言的陌生化與親近化[J].詩歌報月刊.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