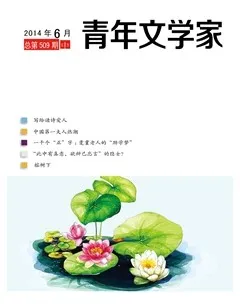文本二主義: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
摘 要:歐陽子《〈游園驚夢〉的寫作技巧和引申義》一文從寫作技巧和主題含義兩個角度對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進行闡釋。但從整體來看,歐陽子是將文本的形式與內容作為切入點,采用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等批評方法,在建構一種平行模式后,由形式深入到內容去不斷延伸了小說含義,以消解作者與文本的意義,然而其引申義最終卻向作者與文本意義回歸。
關鍵詞:結構;解構;平行技巧;今昔對等
作者簡介:李芝,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專業:文藝學。研究方向:民族文藝學。
[中圖分類號]: 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02
昆曲戲劇《游園驚夢》源自明代劇作家湯顯祖的作品《牡丹亭》,自問世以來頗受世人追捧,然而隨著昆曲歷史的由盛而衰,諸如《游園驚夢》之類的昆曲戲劇也被世人當作藝術品貶入冷宮。當代作家白先勇卻從該戲劇文本中吸取養分,結合當代的小說創作技巧,以極其縝密細膩的思維和筆觸重新進行構思與創作,小說《游園驚夢》便由此而生。作為對白先勇小說《游園驚夢》的批評,歐陽子《〈游園驚夢〉的寫作技巧和引申義》一文從寫作技巧和主題含義兩個角度對其進行闡釋,其間也運用了英美新批評派、弗洛伊德關于夢與性的解析等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文本。但從整體來看,歐陽子是將文本的形式與內容作為切入點,其批評也體現了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等兩種批評方法的特征。
(一)結構的歸一:“平行”技巧引發的模式建構
從結構主義的角度看,歐陽子先生的該批評體現出結構歸一的特點,即批評者從小說的文本形式入手,從小說《游園驚夢》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故事情節中抽象出“平行”技巧,極為細致地描繪和分析了整篇小說的“骨架”,從而使小說的結構理論上走向歸一,而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也隨著其批評的展開被建構成一種平行模式。
在對小說《游園驚夢》的寫作技巧一節中,歐陽子延續了傳統的批評理論模式,在小說文本中苦苦探尋其內在的深層結構,第一次提到“平行技巧”這個名詞,并對“平行技巧”進行了自我理解式的闡發:“為了創造‘舊事重演或‘過去再現的印象效果,作者在這篇小說里大量運用了‘平行技巧(Parallelism)”。 “可是在《臺北人》里,作者亦一再制造外表看來與過去種種相符或相似的形象和活動,作為對于人類自欺的反諷。這就需要大大依靠高明的平行技巧。”對“平行技巧”的重要性也是頗有論述:“《游園驚夢》里平行技巧的運用,遍及構成一篇小說之諸成分”。繼而從文本分析的多個角度探討了這種平行結構在小說中的具體體現。
以上可見,歐陽子對于“平行”技巧的分析,從今昔對等的大背景、大前提下切入,再逐步深入人物、情節、敘述觀點和結構形式等,在對文本平行技巧的逐步分析中,小說的結構也逐漸歸一,構成小說之基本結構——平行結構清晰可見,平行模式也在過程中得以建構。
(二)主題的多元意義:小說含義的多角度延伸
對小說主題含義的探討,歐陽子采用解構主義的批評打破了對以往線性閱讀傳統的遵循,而去尋求文本的開放性,并對小說文本的主題尋求多重解讀,這樣便使小說文本《游園驚夢》呈現為一個開放的以及可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不斷生發出新的意義。正如作者歐陽子在批評中所言:“所以欣賞這篇小說,只讀一遍是絕對不行的。”所以,《游園驚夢》這篇小說,相信歐陽子是讀了很多遍的,因為他從多角度去探尋小說的主題含義,對《游園驚夢》主題的多重闡釋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同于傳統解釋,可謂發人深省,也頗有收獲。
首先,他在批評中論述到“《游園驚夢》的小說含義,和中國戲曲史上“昆腔”的興起與衰微,有不可分離的關系。錢夫人終于‘啞掉,不能夠把戲唱完,就是作者暗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中斷。”按照傳統批評方法,也許不少讀者對其前句“《游園驚夢》的小說含義,和中國戲曲史上“昆腔”的興起與衰微,有不可分離的關系。”會有所感悟或認同,然而,“錢夫人終于‘啞掉,不能夠把戲唱完,就是作者暗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中斷。”歐陽子對作者設置此情節的深層含義的推斷可謂出人意料,可細加思考,又合情合理,不無深意。也可說,他從這個新角度去闡釋小說含義也是其解構作者和文本的重要體現。
此外,該批評還從多角度對小說含義進行延伸性闡釋,先是認為“《游園驚夢》小說從錢夫人個人身世的滄桑史,擴大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貴族文化——的滄桑史”; 接著又指出小說含義可引申到社會型態問題以及藝術創作問題上;最后談到《游園驚夢》小說的最終主題——人生如夢,并在分別探討小說《游園驚夢》和《紅樓夢》的“今昔虛實”關系之后,明確指出,“白先勇把‘昔當作實存的本體,把‘今當作空幻的虛影,然而,‘昔,不是明明消失無跡了嗎?‘今,不是明明就在眼前嗎?如此,白先勇暗示:虛即是實,實即是虛。假才是真,真才是假。”而“紅樓夢完全沒有‘昔是實的含義。”由此觀之,“我們很可以把白先勇的小說主題,視為曹雪芹小說主題的擴大和延長。”
(三)文本的互文性:與他文本間的聯系與轉換
該批評明確了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與他文本間大量存在聯系與轉換的關系,表現出文本的互文性,從而使該批評本身也體現了解構主義批評方法的特征。
首先,歐陽子指出了小說《游園驚夢》與昆曲戲劇《游園驚夢》之間所呈現的互文性。小說作者白先勇在創作中借用了昆劇《游園驚夢》中的辭句和典故,并塑造了一個和昆劇中杜麗娘的角色平行的人物——錢夫人。但是,小說《游園驚夢》與昆劇《游園驚夢》在文體、故事情節以及寫作方法上又有著很多不同,白先勇在寫作時實現了創新性的轉換。正如歐陽子在其批評中所論述到的,“此戲又可分成《游園》和《驚夢》上下兩出,游花園的部分是《游園》,白先勇在小說里,借徐太太的演唱,摘錄下唱詞中比較有名而且含義深長的句子。可是杜麗娘入夢以后,與柳夢梅交歡的‘驚夢部分,其熱情大膽的唱詞,白先勇全沒引錄,卻以錢夫人的一段對往日和鄭參謀私通交歡的‘意識流聯想來取代。而這一大段借由象征或意象表達出來的‘性之聯想,熱情露骨的程度,和‘驚夢唱詞相當。如此,錢夫人仿佛變成了杜麗娘,在臺北天母竇夫人的‘游園宴會里,嘗到了‘驚夢的滋味。”因而該小說和同名昆劇間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同時又實現了創新性的轉換。
其次,批評中還明確指出了洛神、貴妃醉酒與小說角色錢夫人之間的互文關系。歐陽子分析到,小說《游園驚夢》中有以“洛神故事即影射錢夫人和鄭彥青之事,難怪程參謀和錢夫人討論‘洛神。雖然當時兩人才剛見面,錢夫人就感覺不自在,‘觸到了程參謀的目光,她即刻側過了頭去,又覺得‘程參謀那雙細長的眼睛,好像把人都罩住了似的”。另外,又以貴妃醉酒來影射藍田玉姐妹爭奪鄭參謀的三角關系。因而,歐陽子的批評認為,小說《游園驚夢》既借他文本來傳達作品含義,又成功地將故事人物與情節與他文本間實現融合,使其形成新的文本。
此外,小說《游園驚夢》與《紅樓夢》主題間的互文性也被歐陽子所窺出。他認為,二者在主題上存在一致性,即竇夫人金光閃爍、富麗堂皇的宴會,在我們這樣一個無常的人世里,只是一個虛幻的夢境;紅樓夢中天堂一般純美的大觀園,也是個虛幻的夢境。如果要把“今日”虛幻的夢當作永恒的境界來陶醉,即不能實現徹悟“世事無常”、“人生有限”之真實性。但是,不同于紅樓夢的另一種解是,《游園驚夢》中的錢夫人把虛無的過去當作永恒來陶醉其中,那眼前的實在,也好比虛夢一般。
(四)不足:引申義向作者與文本意義的回歸
歐陽子的批評原本采用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等批評方法,在建構一種平行模式后,想由形式深入到內容去不斷延伸小說作品的主題含義,以消解作者與文本的意義,然而《游園驚夢》的主題含義不論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斷還是社會形態或藝術創作的問題,歐陽子最終還是“回頭”來談論其“最終主題”——人生如夢,走向自我矛盾的立場,弱化了其解構批評。其一,批評中主題的唯一性。從之前的不斷延伸意義使文本表現出開放性特征到最后的“最終主題”的籠統涵蓋及其唯一性特征,歐陽子使其自身又走向了解構主義的對立面。其二,引申義的最終概括。歐陽子最終將小說含義歸為“人生如夢”,以作為對于前面所述延伸義的整體概括,即一切皆將幻滅與消亡,使其引申義最終又向作者與文本意義回歸。
參考文獻:
[1] 王曉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M].上海:東方出版社,2003.
[2]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