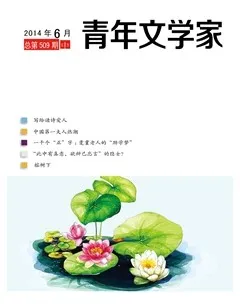行為背后的無意識
邱少蕓 凌海衡
摘 要: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小說《蒼蠅》中兩個人物截然不同,老伍德菲爾德毫無男子氣概,十分可憐;老板卻充滿魅力,令人羨慕。老板貌似幸福快樂,實際上卻是生活在陰影的威脅下。他殘忍對待蒼蠅的行為背后是一種無意識的替罪羊行為,是受到陰影威脅的他所采取的一種投射行為。
關鍵詞:蒼蠅;老伍德菲爾德;老板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02
一、引言
《蒼蠅》是曼斯菲爾德著名的小說之一,故事以老伍德菲爾德拜訪老板開始,在他離開之前,提起了他們死在戰場上的兒子,這番出乎意料的話對老板震撼很大。在他回憶悲傷往事時,一只蒼蠅掉進了墨盒,引起他的注意,之后他反復拿起鋼筆滴墨在蒼蠅身上直到它不再動彈。故事情節發展十分簡單,但人物的心理危機卻十分突出。在父系社會,有一類男性像老伍德菲爾德那樣,沒有扮演好男性角色,產生強烈的自卑感;也有一類像老板一樣,摘不下根據社會生活需要而制定的人格面具,壓抑了其它成分,最終形成陰影。當他們受到陰影威脅時,往往否認并投射到他人身上。
二、分析和討論
1. 老伍德菲爾德的失敗和老板的成功
毫無疑問,男性和女性的社會性別是有差異的。女性普遍表現為生命和營養的給予者,被充分地賦予了愛。男性則常以長者或統治者的形象出現,充滿理性和判斷力。榮格一再提到,男子氣概和女子氣質這兩條原型原則提供了男性和女性的刻板模式發揮著作用。⑴對男子氣概,或者說對主導權的追求,都原型地植根于男性當中。《蒼蠅》中的老伍德菲爾德因為失去了一切主導權,感到失敗,顯得可憐。
退休后的伍德菲爾德身體不好,只能依賴家人,即使拜訪朋友這種事也需家人同意,只能在每周二。他是被禁錮在家,被穿戴整齊后被允許進城。被動語態的使用及對他的稱呼都在前面加修飾詞“老”,使他失敗可憐的形象躍然紙上。貝特森與沙哈維奇(Bateson & Shahevitch)認為對他的所有描寫都突顯了小說最初介紹他的形象,一個坐在嬰兒車里朝外張望的嬰兒形象。⑵失去主導權的他甚至連嬰兒都不如,因為嬰兒是天真快樂的,而老伍德菲爾德已喪失了感受家人關心及人生樂趣的能力。如今他唯一的和最后的樂趣就是每星期二拜訪老板。“正如草木依戀最后的幾個葉片一樣。于是乎,老伍德菲爾德坐在那兒,抽著雪茄,幾乎是貪婪地盯著老板。”⑶看著老板是他人生中僅剩的樂趣,“貪婪”一詞更是描繪出老伍德菲爾德內心渴望成為老板那樣的人。此外,當他談起死去的兒子,絲毫沒有傷心難過,甚至喜形于色地談到墓地的鮮花和寬闊道路,像在分享一次旅游經歷。因為在他內心深處,兒子體面的死亡比他如今的生活更有價值,更令人尊敬。
和他相比,老板則是典型的成功男士。“老板在辦公椅里左搖右晃。他腰板硬朗,紅光滿面,雖然比他年長五歲,可依然身體結實,掌握著大權。”⑷即使已到垂墓之年,但老板仍然充滿魅力。接下去一系列用來描述老板的動詞,如撥弄、揮手、眨眼、轉動等等,呈現了他充滿活力的形象。雖然他比伍德菲爾德年長五歲,但似乎對自然衰老這一殘酷命運也掌握著主導權。
除了對無情歲月的免疫,老板對周遭的一切也都掌握著主導權。他牽引著老伍德菲爾德的注意力,讓他喝下早已遠離的威士忌,最后甚至用沉默迫使他離開。⑸如小說中所描述那樣,他“穩穩地坐在屋子中央……感到一種深切而真實的滿意”。⑹穩坐辦公室中央的老板就像在舞臺中心,聚光燈照耀下的主角,充分地顯示了他作為領導者及操控者的風范。此外,“成功老板”這一角色毫無疑問也讓他成為了職場上的主宰者。
2.人格面具下病態的老板
“老板”是主人公的社會角色,榮格稱之為人格面具,像“律師”、“建筑師”一樣,它是老板適應社會所必需的,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他的真實性格。榮格指出,一個人的人格面具并不是單一的,比如,在職場上他可能扮演老板的角色;回到家中則變成丈夫;出了家門,則是一個公民角色。人格面具就像是演員表演時所戴的面具,總有一些偽裝的成分,因為它是環境與自我相妥協的產物,是一個人以能被他人接受的形式裝扮起來的自己。“人格面具并不是固有的就是病態的或虛假的。只有當一個人過分地認同于自己的面具才會產生危險。”⑺“老板”這一人格面具切實符合社會對男性角色的期望,滿足男性對主導權的追求。《蒼蠅》中的老板,恰恰就是過分地認同于自己作為“老板”的這一角色,在這一人格面具下隱藏了一個虛假病態的自我。
老板并不是真心喜愛他辛苦打拼起來的事業,只是這副人格面具,滿足了自我需求和社會期望。“要不是為了孩子,它就沒有任何意義。……這么些年來,他又怎么能夠拼死拼活,兢兢業業地干下來呢?”⑻小說原文是用slave(奴役)和deny himself(否定自己)來書寫他的拼死拼活和兢兢業業。他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甚至將它視為一種奴役與自我否定,是自我需要對環境需要作出的妥協甚至犧牲。在為了兒子而擴大生意的借口下,老板向別人及自己掩蓋了真實的自我,努力工作,以求成為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和羨慕對象。然而,兒子的死去把他這點自欺欺人的借口也剝奪了,曾一度使他崩潰。剛開始他也無法抹去對兒子的思念,無法堅強、獨立地繼續活下去,所以在兒子死去的頭幾年,只要提到兒子,他就會哀痛欲絕,大哭一場。可老板并沒有中止自己不喜歡的事業,而是繼續以“老板”這一身份活下去,壓抑悲痛,最終在潛意識里形成陰影。
為了隱藏他的脆弱情感,為了達到社會對男性的期望,老板采取的方法是僅僅以“老板”這一角色生存下去,壓抑和抵制與這個角色相悖的所有成分。“父親”這一角色帶給他的只有痛苦,只能體現出他脆弱與無奈的一面,恰恰是與“老板”角色相悖的成分,遭到老板的逃避與壓抑。所以,六年來,他從未踏足兒子的墳墓,回避關于他的一切。當他一次次地向老伍德菲爾德炫耀自己的豪華辦公室時,總是避免引起老伍德菲爾德對桌上兒子照片的注意。他逐漸地迷失在“老板”這一角色中,他的所有話題都離不開“老板”這一角色,他的步伐也都局限在辦公室里,從頭到尾都只是老板,對他的稱呼不再有某某先生,某某人的丈夫或父親,只是老板了。此外,當他面對老朋友時,他也已不自覺地扮演著“老板”角色,不再是“朋友”角色。看著虛弱的伍德菲爾德,老板感到深切而真實的滿意,居高臨下;明知他中過風,還擺出“老板”的姿態,給他喝威士忌,罔顧他的健康。可見如今,能在老板面前閃閃發亮的,只有工作,能給他帶來快樂的也只剩下“老板”這一角色。他過著貌似幸福快樂的生活,隱藏在人格面具下的卻是虛假且病態的自我。
3. 無意識下的替罪羊
老板過分認同于自己這一人格面具,壓抑了與“老板”特質相反的所有特征,把它們隱藏在潛意識那個黑暗的地方,榮格稱之為“陰影”。雖然老板壓抑、逃避這個心中的異己,然而它卻像影子一樣步步緊隨。當老伍德菲爾德提到他死去的兒子后,他深受打擊,兩眼茫然,腳步沉重,但他再也不能切實感受到“父親”這一角色帶給他的痛苦感覺。“他需要、他打算、他已安排好要痛哭一場……。”⑼他的哭不再是有感而發,而是他想要的,需要準備的。面對兒子的死亡而哭泣已經變成了一項需要完成的任務,因為他的人格已不再完整,“父親”這一角色已被他腦海中的橡皮擦拭去,被他壓抑在潛意識中,剩下的只是社會道德對他起的作用,告訴他一位好父親在想起死去的兒子時應該哭泣。不過哭泣,是一種情感流露,并不像老板手頭的一項任務,可以通過準備就做到,沒有真正感到痛苦是哭不出來的,所以老板沒能如他所愿哭出來。雖然他哭不出來,但是陰影地爆發還是使他感到困惑不解,感覺受到威脅。
老板為了保持心靈的平靜,“利用了各種自我防御機制,特別是壓抑、否認和投射”。⑽他注意到了一只蒼蠅掉入墨盒當中,為了使自己免受陰影的威脅,他壓抑死去兒子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否認自己抹去對死去兒子記憶的“壞”,甚至把這種痛苦,這種“壞”推到那只無辜的蒼蠅身上。看似荒誕而非邏輯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令他人代己受過的行為,蒼蠅成了老板的替罪羊。這些基本上都是在潛意識里進行,潛藏在老板的心靈深處,所以他意識不到自己行為背后的真正動機。
蒼蠅就像老板的兒子一樣,都是殘忍“戰爭”中的替罪羊。老板看著蒼蠅面對他滴下的墨水,開始把墨水從翅膀上擦去,心想,“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這種精神才對頭”。⑾他壓抑和否認陰影爆發給他帶來的痛苦,告訴自己繼續以“老板”這一身份活下去才是正確的解決方法。當蒼蠅獲得重生之后,老板并沒有停下來,而是再一次向蒼蠅滴下致命的一滴墨水。他反復地滴墨水在蒼蠅身上其實是在將他的痛苦,他的“壞”投射到蒼蠅身上,讓它代已受過。在蒼蠅死后,老板直接把死去的尸體扔進字紙簍,但是這時他已記不起老伍德菲爾德提過他死去的兒子,記不得他為什么折磨死蒼蠅,記不得“老板”這一角色外的所有東西,“他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來了”。⑿老板一時躲過了陰影的威脅,什么也想不起來了,可是他也失去真實完整的自我。老板以后的生活是可以預見的,他只會繼續戴著他的人格面具生活下去,過著表面上體面的生活,但在心靈深處卻藏著一顆受傷痛苦的心。
三、結論
人格面具和陰影原型地植根于個體當中,每個人都擁有。但如果過度于人格面具,則是病態且危險的,如《蒼蠅》中老板不論何時都扮演著“老板”的角色,顯得不合時宜。受到壓抑的陰影能夠使人感到懷疑、震驚并壓倒自我。為了保護自己,個體會像老板一樣,潛意識地采用壓抑、否認和投射,他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這樣做的。在當今社會,這種替罪羊的形為并非鮮見,輕則有個人之間的相互憎惡,重則有對一個集體的偏見及迫害。因為這些行為是在潛意識層面進行,人們是沒有意識到行為背后的真實動機,結果會導致攻擊或消滅別人變得合情合理。要打破陰影的控制,人們只有直面陰影,使完整的人格得以呈現,這不僅對個人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營造和諧社會甚至促進國際和平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⑴⑽ (英)安東尼·史蒂文斯: 《簡析榮格》,楊韶剛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242頁。
⑵ F. W. Bateson & B. Shahevitch, “The Fly”: A Critical Exercise, in Katherine Mansfields Selected Stor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356.
⑶⑷⑹⑻⑼⑾⑿ 曼斯菲爾德:《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集》,唐寶心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265、266、269、269、271、272頁。
⑸ 宋海波:《及物性系統與權力關系》——對凱瑟琳·曼斯菲爾德《蒼蠅》的文體分析,國外文學,2005(4)。
⑺ 施春華:《心靈本體的探索:神秘的原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