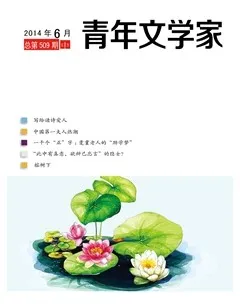19世紀70—80年代華裔女作家作品中的“母女關系”淺析
[基金項目] 該論文為長江師范學院校級青年項目“20世紀70-80年代美籍華裔女性作家湯亭亭、譚恩美、嚴歌苓筆下的女性人物研究”(項目編號為2013XJQN032)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作為19世紀70-80年代華裔美國女作家的代表人物,譚恩美的《喜福會》和《灶神之妻》以及湯亭亭的《女勇士》三部作品中描述了第二代華裔女性處于種族和性別歧視以及父母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自己接受的西方先進教育的重重矛盾和重壓下,母女兩代人復雜的關系。本人通過研究“母女關系”這一主題,通過回顧母女間從最初的沖突、隔閡和摩擦到最終的融合和認同的歷程,試圖探討母親對女兒的身份屬性和文化歸屬的建構過程中的作用。
關鍵詞:70-80年代華裔女作家;湯亭亭;譚恩美;母女關系
作者簡介:孫小靜,女,文學碩士,長江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女性主義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02
一、引言
在19世紀70至80年代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特別是華裔女性作家的小說里,“母女關系”(Mother-daughter Ralationship)這一主題被著重突出出來。197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英國等一些主流國家的第三次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女權主義的思潮逐漸深入到華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華裔美國人在美國已有100多年的生活史,在那段“排華”的特殊歷史時期里,美國主流社會出臺了許多排擠、歧視華人的政策和法案。處于種族、性別雙重歧視中的華裔美國女作家的文學作品中也記錄了這段歷史,特別是70-80年代的新興女作家,她們用女性獨特的視角深入的剖析了困擾華裔美國女性的問題,如:在雙重矛盾下女性身份的建構和歸屬等。令人欣慰的是,這些新興女作家的作品受到美國主流的普遍歡迎,如湯婷婷于1976年創作、也成為其代表作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獲得美國的國家圖書評論家獎;譚恩美于1989年創作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則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長達9個月,“其首版精裝本被重新印刷的次數達27次,銷量也達到27萬5千冊,其平裝版本版權價格則由10萬美元的底價被人們哄抬到了令人震驚的120萬美元”。⑴ 在她們的作品中涉及到了種族、性別的矛盾、沖突和融合等相關問題,而這些都很好地融合在了“母女關系”的闡述中。與此同時,她們在美國主流社會取得的傲人成績使得其文學作品中“母與女”和“姐妹情誼”的相關主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本文將分別研究70-80年代美裔華人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湯婷婷和譚恩美的小說文本,試圖找出母女關系對華裔美國女性身份構建的作用。
二、母女關系在譚恩美小說中的彰顯
埃萊娜·西蘇曾這樣說“女性文本應該彰顯女性寫作同母親之間的緊密關系,這些女性文本應該強調聲音(voice)”。⑵ 無論是《女勇士》和《喜福全》、《灶神之妻》還是《接骨師之女》中,女兒們和母親們都是在經歷了最初的種種沖突和矛盾后最終達到了母女之間的包容和融合,在這個母女都蛻變的過程中,母親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教會女兒勇敢的發出自己的聲音。年輕一代在經歷了美國社會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并經歷了自身做人妻、為人母以后,她們從母親們的苦難故事中,獲得了精神力量,并逐漸包容了母親身上所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在中美文化的雙重夾縫中構建了自我身份,而這些都在譚恩美的代表作-《喜福會》和《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中得到了很全面的彰顯。
譚恩美的代表作品《喜福會》主要描述了四對華裔母女間發生的故事,這部作品也奠定了其作為“女兒作家”(daughter-writer)的基礎。在一個個或是母親講給女兒的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里,抑或是女兒通過想象所構建的自己的故事中,母親與女兒的關系也在這些故事中達到了一種新型的母女認同。但和湯婷婷《女勇士》中敘述者的母親不同,《喜福全》里的母親們最初并沒有告訴女兒們自己曾經在中國所經歷的一切人生苦痛。她們遠離中國,帶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來到全新的美國。那時的母親們似乎更希望生在美國長在美國的女兒們帶著對生活的美好希望,逃離自己那段曾經不堪回首的“歷史”,并希望女兒們能夠帶著她們的殷切希望創造美好的將來,因此她們對女兒抱有很大的期望。如吳精美評論母親吳素云在她9歲時對她說的“你也能成為天才,你會樣樣事事都應付的很出色的”。⑶ 適得其反的是,女兒們在美國受到的教育是崇尚自由、民主、個人主義的,這和母親的嚴苛要求和逼迫是格格不入的。在母親們的過分壓力下,女兒們開始和母親產生了距離感,和母親們疏遠起來。女兒們“厭惡甚至憎恨以母親為代表的荒謬詭秘的陳規陋習”。⑷ 與此同時,女兒們開始了種種叛逆行為,和母親們的沖突日益劇增,在現實社會中試圖構建自我身份并摒棄自身中帶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母親們以及中國母親們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抗著。也就是說,雖都是女兒身,但母親生活的20世紀30、40年代的封建中國和年輕一帶生活的20世紀70、80年代開放、自由的美國形成了對抗。母親們試圖讓女兒們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女兒們卻在一味的逃避。盡管如此,文本中的四對母女在經歷了和母親的沖突、矛盾、隔閡之后,從母親的故事里汲取了力量并獲取了勇氣,創建了自身獨特的文化和身份屬性。正如文章所說,母親必須把“我所經歷的一切告訴她,這是我能滲透她的皮膚,挽救他與為難的唯一辦法”。⑸ 通過講述故事的“聲音”,母女之間最終達到了彼此間的認同,并為自身作為美國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份做出了突破性的嘗試。
在其另一部小說《灶神之妻》中,譚恩美刻畫的另一對母女也同樣有類似于上文中提到的四對母女的經歷。但不同的是,溫妮的母親為了追求自我的幸福,離開了溫妮,但溫妮并沒有因此而怨恨母親,在經歷了一生的坎坷之后,她明白了正是母親當初的選擇開拓了自己的視野,讓她見識了美國餅干和法國香水;也正是母親教會了她不屈于自己的丈夫,并告之命運在自己的手中;還正是母親讓她明白了,不管卑微還是偉大的人都有權利追求自身的幸福的道理。溫妮的母親勇敢地違背了“三從四德”的要求,⑹ 放棄了自己作為富商姨太的富裕生活。她毅然和心愛的人私奔,遠走他鄉,勇敢卻決絕。作者并未就溫妮的母親著墨太多,然而這個叛逆、富有斗爭精神的母親卻深深影響了女兒的一生,即使被中國封建的父權制阻斷了兩人的聯系,但母親對女兒精神層面的影響仍然是無法被割斷的,和母親短短6年的相處,溫妮繼承了母親的勇敢。丈夫吃喝嫖賭、且視女性如“一把給人坐的椅子或是一雙用來吃飯的筷子”。⑺ 婚姻并不幸福的她最終忍無可忍,決定與丈夫文福離婚,勇敢地向父權社會發起挑戰。最后,溫妮在美國依靠自己的力量過著獨立的生活。小說中的另一對母女溫妮和她的女兒珍珠,也同樣經歷了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溫妮給女兒講述了自己向女兒隱瞞多年的在中國的苦痛經歷,而珍珠也跟母親訴說了她的秘密,即自己患有多發性硬化癥的病情。母女互訴心聲,最終達到相互諒解。女兒也接受了母親的建議,決定用中醫來治療和控制病情,她從母親那里獲取了力量,她的中國母親“具有她的群體的古老智慧和言語能力”。⑻
三、湯亭亭小說中的母女關系
在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所有的矛盾和沖突都圍繞著“母女關系”這一主題,湯亭亭的《女勇士》也不例外。母親勇蘭給女兒講述了很多關于中國的故事,但是出生、生長在美國的女兒并不能真正理解各種故事背后母親的教育目的。母親勇蘭講“無名姑姑”的故事的目的是向其女兒傳輸女性要“潔身自好”“有羞恥感”的中國傳統美德,以此起到對女兒的警示作用,“以便養育一個順從的乖女兒”。⑼但這個故事卻令女兒迷惑不解,她并不明白母親的良苦用心。傳統而迷信的母親交代女兒的事情更令女兒迷惑不解。藥房伙計錯誤地把別人的藥物送到家里來,母親認為這是不吉利的事情,并因此要女兒去斥責藥房,而且要“索取糖果祛邪”。⑽移居美國的母親們代表著傳統中國文化,她們希望自己在家庭中能擁有主人公的家長勢態,對孩子有著絕對的支配權利,而孩子們則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但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兒們接受的文化則是崇尚自由、民主、平等、開放,她們也用此標準要求具有傳統中國價值觀的母親。在一次次沖突和矛盾后,叛逆的女兒們和母親的關系越行越遠。不僅如此,望女成鳳的母親對女兒寄予了殷切希望,她希望用花木蘭替父從軍、蔡琰(蔡文姬)以及自身的故事和經歷教誨女兒成為一名獨立、自強、勇敢的女性。但年幼的女兒卻難以明白母親講述的種種或隱晦,或迷信的中國傳統故事。她對母親寄予的期望同樣感到迷惑和費解;她不知道母親是要讓她“成為一個將庭主婦還是一名女勇士”。⑾生存在美國主流社會,華裔母親和女兒們處于種族、性別和文化等多種矛盾中,這讓母女關系變得更加矛盾重重。但母女關系也同時有著強大能量,“它可以超越所有的鴻溝和阻礙”,⑿恢復母女間的親密,從而給予彼此理解、寬容和勇氣。最終,逃離唐人街的女兒又回到了母親以及母親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身邊,和母親達成了和解,同時也對母親講述的故事有了全新的認識。她明白母親講述的這些故事實際是給自己樹立一個個勇于反抗男性父權制的勇敢女性的榜樣。這個時候的女兒突然意識到母親勇蘭“就是女性力量和成就的最好榜樣”,⒀母親自己的經歷是讓女兒懂得要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力成為一名獨立、自強的女性。最終,母女之間完成了從矛盾、沖突到融合的過程,而迷失的女兒也在這個過程中清晰了自我身份并找到了文化歸屬。
四、小結
總體來看,華裔女性作家中“母女關系”是一個永恒的主題,無論湯亭亭、譚恩美還是新興作家吳梅、任碧蓮,在她們的作品中,母親和女兒的關系都是華裔女作家的關注焦點。 各種問題和矛盾,如:種族、性別、文化沖突都是圍繞著“母女關系”這一主題展開和剖析的。母女關系的發展過程總體都是有著從最初的沖突、隔閡到后來的理解、包容和融合的趨勢。女兒認同了母親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并汲取其中精華為我所用,成為自身力量的源泉;在美國社會中,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文化屬性、身份和幸福。
注釋:
[1]Patricia Holt. "The Shuffle Over 'Joy Luck',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view, July 16, 1989:2.
[2]Helen Cixous. Reading With Clarice Lispec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Minnesota Press, 1990. 轉引自蒲若茜,“族裔經驗與文化想像”,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5.
[3]譚恩美. 《喜福會》,程乃姍,嚴映薇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1
[4]劉卓. "解讀被雙重邊緣化的文化屬性一試論湯亭亭的巜女勇士》和譚恩美的巜喜福會》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11月,第5卷第6期:452一454.
[5]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241.
[6]石萍萍. 母女關系與性別:種族的政治 ,美國華裔婦女文學研究.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141.
[7]Tan Amy. The Kitchen God's Wife. London: Flamingo, 1992: 282.
[8]田苗. 《灶神之妻》中姐妹情誼的跨文化解析,遼寧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31卷第34期:431-433.
[9]Ho, Wendy. In Her Mother's House, The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 Mother-Daughter Writing. Oxford: Altamira Press, 1999: 59.
[10]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7.
[11]付明瑞. “從傷痛到彌合-當代美國華裔女作家筆下的女性身份的嬗變 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68.
[12]同上 83
[13]Grice Helen. 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