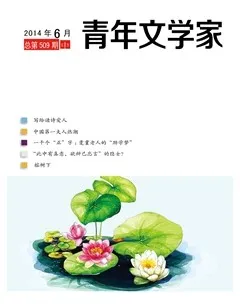由“曬”字看外來詞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摘 要: 外來詞是中西語言、文化交流的產物,也是中中西文化完美結合的表征。以近期流行于網絡并開始出現于口頭交流的“曬”族新詞為例,看外來詞在中國的文化發展。
關鍵詞:曬;外來詞;文化發展
作者簡介:曾蘭燕(1975-),女,貴州省獨山縣人,碩士,廣州科技貿易職業學院講師,從事漢語言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 H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2
外來詞是中西語言、文化交流的產物,也是中西文化完美結合的表征。筆者以近期流行于網絡并開始出現于口頭交流的“曬”族新詞為例,看外來詞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曬”來源于英文Share(分享、共享),同時兼有中文 “曬”字(在陽光下展示某物)的引申義,展示,坦露,公開化,透明化等,及廣東話“曬命”一詞“曬”的炫耀之意,從而形成了目前流行于網絡和口頭上“曬”:
“曬牙齒”(裸露牙齒);
“曬工資、曬房價”(公開展示);
“曬廚藝、曬美圖”(分享共享);
“曬幸福、曬寶貝、曬家人”(炫耀顯擺)。
我們可以看到,在“曬”詞的音譯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全新的中西方意義兼有的詞語,而且隨著網絡媒體迅速傳播并衍生了許多詞組和意群。從“曬”詞的產生,我們不但看出當代人的追新求異,個性張揚的心理特征,而且從翻譯方式的多元化、復雜化,也可看出中國越來越開放的多元文化融合和靈活的創新思維。
一、外來詞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外來詞的發展歷程普遍規律是:一個詞語的引入往往是先進行音譯,后出現意譯,而后起的意譯詞往往會取代之前的音譯詞。這是由漢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因素所決定的,由此也使得在外來詞的今后發展前景中,“意譯形式雖然不可能完全代替音譯形式,但將是主要的引進方式” [1]。由于文化心理習慣的不同,外來詞的吸收受很大的制約,除了政治、經濟、語言政策原因外,還受到漢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特點的制約。如漢語是單音節語素語言,具有強烈的表意傾向和強大的構詞能力,這都有利于意譯的發展,在吸收外來詞過程中對于同一個詞語的音譯詞和意譯詞,人們往往更容易接受或傾向于接受簡潔明快的意譯詞。例如,電話最初被音譯為“德律風”,后來最終被淘汰,而意譯的“電話”因其簡潔明了的意譯,一直為人們所用;“德先生”和“賽先生” 如今也被意譯“民主”和“科學”所取代;“卡通”(cartoon)和“動畫” 相比,大眾更能接受“動畫”。另外還有類似的husband (黑漆板凳) 丈夫,ambassador (菴巴薩托)大使,dictator(狄克維多)獨裁者,gentleman(竟得爾曼)紳士,inflation(因發熱兇)通貨膨脹,journalism(集納主義)新聞事業,parliament(巴力門)國會等等。因此,在一段時期內,意譯仍將保持著相對優勢的地位,這是由漢民族表意的文化心理所決定的。 另外,漢民族靈活意合的心理思維將會使越來越多的外來語為“我”所用,甚至將會轉變為漢語自身基本詞匯。漢語是孤立語,基本單位是字,而不是像西文那樣為空格所分開的是詞而不是詞素。因此在引入外來詞過程中,漢語對一個外來詞可以加以拆分,再和另外的詞素組在一起,形成大量新的詞群。不僅使漢語的詞匯出現了量的突破,更使漢語的詞匯出現了質的飛躍,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的內涵與表達方式,促進了語言的新發展。在詞素的組合上,如來自“的士”(taxi)的“的”構成了“打的”、“面的”、“摩的”、“飛的”、“轎的”、“板的”、“馬的”、“驢的”、“水的”,以及“的哥”、“的姐”等。 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大城市還冒出了許多詞帶“吧”(bar)字的休閑場所名詞,如“陶吧”、“餐吧”、“茶吧”、“書吧”、“畫吧”、“迪吧”、“網吧”、“巧克力吧”、“玩具吧”、“琴吧”、“玩吧” 。另外,詞義的引申上,如“鐵娘子”(Iron Lady)原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現泛指各種精明強干的女人。漢字中的“秀”意為“清秀”或“優秀”,在與英語的“show”借用后,可指各種不同的表演節目,如“時裝秀”、“生活秀”等等。再如“曬”用來表示公開,炫耀,分享,“拜拜”用來表示某人與世長辭,去世等等。我們可以說這些外來詞不但填補了民族語言對外國文化的詞匯空白,提高語言的表達功能,而且突破了現代漢語構詞法的一些局限,豐富了漢語的構詞形式,如“非”、“超級”等前綴詞和“吧”、“杯”、“星”等后綴詞的增加,而且也有諸如“馬拉松”、“可口可樂”等多音節詞的增加,都說明了這一點。與此同時,外來詞特別是英文詞語的引入,完整英文字母在漢語中使用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英文縮寫詞的使用已經成為國際化慣用語,如OPEC、MTV、CD、DVD、SPA、DIY、MP3等等,人們與這些英文的接觸頻率越來越高,對字母詞的接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對西方文化的心態已經從求新求異的態度變為作為日常語所必要接受的平常心態。
二、外來詞對中國文化心態的影響
外來詞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和語言學現象,在現代漢語與其他民族語言互交流中,使用群體的心態確定了對外來詞接受并認可,外來詞對中國文化心態的影響包括以下幾方面:
1.開放心理。隨著漢民族與外民族語言文化接觸的頻繁,中國社會由封閉型走向了開放型,漢民族大陸文化自給自足的封閉心理有了很大的轉變,對外來文化、外來語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了顯著的增強,于是外來語的廣泛使用也順理成章。
2.崇洋心理。在中外經濟貿易交往過程中,外國文化隨同外國商品涌入中國,刺激了一部分人對異域文化的向往,一些人就喜歡用洋味詞語,如不說“再見”說“拜拜”(bye-bye),乘車不說“坐公共汽車”而說“乘巴士(bus)”等等,體現出部分人在使用語言時對異文化的認同和向往。
3.求新求異心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往往喜歡別出心裁地創造出一些“人無我有”的新詞來,例如,“好酷呀”(“酷”即英語cool音譯兼意譯)、“伊妹兒”(英語E-mail的音譯)、“派隊”(英語party的音譯)等,又如“陶吧”、“餐吧”、“茶吧”、“書吧”、“打的”、“面的”、“摩的”等,顯示出人們對新奇事物的追求,同時也是張揚自己獨特個性的體現。
4.求美求吉利心理。在借鑒、吸收外來詞時,漢民族著力體現漢語語音及漢字表意的屬性,賦予其濃郁的漢語語音和語義色彩,使之不僅與漢語固有詞匯形成有機和諧的整體,且形象鮮明,極富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如“可口可樂”(coca-cola)就是一個絕佳的譯名,它相當生動地表現出這種飲品給人帶來的清爽、愉悅感──既“可口”亦“可樂”。同時,人們也考慮選擇一些表示祝福、吉祥的字眼來譯音,以滿足漢語使用者的美好祈望,如“托福”(TOEFL)和“雅思”(IELTS),“保齡球”(bowling)、“呼啦圈”(hulahoop)、“拉力賽”(rally)等等。
綜上所述,外來語在引入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受到中國文化及心理的影響,這些文化與心理也對外來語的發展也起到了一種導向作用,從而促進著現代漢語的發展完善。
參考文獻:
[1] 《漢語外來詞》史有為著,商務印書館,2000年1月第1版,第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