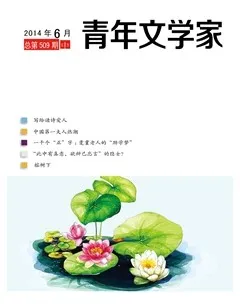淺論戲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侯志琨 李洋 張楠
摘 要:元代與明代是中國戲曲盛產的時代,其中尤以描寫青年男女沖破禮教束縛,大膽追求愛情的題材最為突出,其中《西廂記》與《牡丹亭》是極具代表性和里程碑意義的兩部作品,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當時引起巨大的共鳴,她們的果敢甚至千百年來為人們稱贊。我們將通過對比、整合的方式來闡述在不同的兩個時代里這兩種女性形象的異同,研究形成她們那般性格的內在原因和社會原因,從典型作品中多角度把握典型性格,從而還原一個更為立體的明、清時期婦女形象。
關鍵詞:婦女;禮教;覺醒;追求愛情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1
《西廂記》是以唐傳奇為原型改編而來,但基于元代的社會現實進行客觀反饋與豐盈,一改悲劇性質,給讀者一個圓滿的結局。《牡丹亭》則是在“程朱理學”僵化的明代所作,封建統治對婦女的鉗制讓人痛苦不堪,以“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愚弄大眾,杜麗娘的自我覺醒、大膽抗爭更加讓人敬佩。而無論是何種年代或社會現實,爭取自由、追求愛情都是我們該有的權利和人生的必然。
一、共同的特質與抗爭形象
無論是崔鶯鶯還是杜麗娘均是出身官宦之家,她們的貴族出身使其從小生活在一個堅固高大的堡壘之中,一方面深受多于常人的封建禮教的束縛,從小接受正統的封建教育,而另一方面她們也遠離了塵世的坎坷艱辛,不曾目睹下層窮苦人民的顛沛流離抑或食不果腹,她們無一例外的都是顧盼生姿、才貌雙全的世間尤物,才子與佳人天作之合,自然有追求的價值,而多得是相貌平平、不閱經書的平凡女子。我們揭露社會與個人的尖銳矛盾無可厚非,更應明確這種反抗具有典型性與突破性但并不存在普適性和主動性,整日以溫飽為目的的底層婦女并非人人具有資本與勇氣進行抗爭。
崔鶯鶯是一個渴望愛情、向往自由但不得不保持端莊穩重、沉靜內斂的大家閨秀,她既有少女似火的熱情又不乏特有的羞澀,她的抗爭首先表現在面對愛情降臨時大膽的沖破禮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似一把沉重的枷鎖,這把枷鎖眼看要將她帶到當朝相國之子鄭恒的身邊,可張生的出現使得她成為了時代的“叛逆者”,她對張生的愛明凈單純、不含有一絲雜質,猶記得長亭送別時她深情的叮囑“但得一個并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生怕眼前的情郎會情有它屬,她的情真意切在坎坷的來路上讓人心生暖意。其次,從對“門第觀念”的藐視反映她對封建勢力反抗的徹底性和先進性,張生雖為尚書之后,但家族已經淪落,門當戶對在這對青年之間沒有了條件。但崔鶯鶯依然情愿以身相許,面對來自父母或周遭的種種壓力她始終將“情”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家世利益、是非榮辱、功名利祿那都不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讓人歡心,這種清醒的自我意識和基于愛情的婚姻觀念大概是那個時代的女性最為深刻的思考,較之今日,這種觀念仍是值得我們贊嘆、能夠博得贊同的高尚婚姻觀念。
杜麗娘的抗爭形象較之于崔鶯鶯更具備自主性,在元代如果說婦女初具了覺醒的意識、有了些許思想的萌芽,那么在明代婦女對個性解放和自身利益的訴求便有了新的高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牡丹亭》中最動人的便是這句話。因愛而死又為愛再生是多么讓人為之動容,“至情”的杜麗娘在長久的深閨生活中沒有青年才俊于她偶遇在某個浪漫的場所,沒有“紅娘”為她投遞愛意,有的只是無窮盡的封鎖和父母的苛責,杜麗娘的抗爭必須是自己“揭竿而起”,只能是一場向自我靈魂的追問和覺醒,“生則戀,死則葬”,杜麗娘面對只存在與夢中的愛人發出了這樣的許諾,寧愿超越生死、橫跨陰陽之境也不愿放下摯愛對封建禮教表示順從而后隨波逐流了卻此生,然而現實這面銅墻鐵壁給了崔鶯鶯一個出口卻讓杜麗娘無處可走,在生活中甚至難尋夢中的他身在何方,她終究是因為愛情和思念燃盡了自己的生命,似飛蛾撲火般只留下一道刺眼的白光,死,怎會是故事的終結?即使在陰間她也據理力爭最終得以還陽,她的復活正是不屈抗爭換來的轉機與希望,杜麗娘勇敢地找到情人表白心跡知道獲得了世俗和家庭的認可。她的反抗形象更加豐盈和具有超時代意義,她大膽直率的追求更是展現了人性的光輝:敢愛、敢恨、敢死、敢生,自我的生命誠然可貴,但愛情卻死生不相辜負。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這些客觀機會給“程朱理學”封鎖下的社會一個喘息和松動的機會,那么對“人欲”和“情”的要求是時代的必然產物。
雖然所處時代各異,遭際也不盡相同,但二者在面對愛情的態度上、在對封建禮教的反抗中,在追求自由的自信力上都有高度的相似,她們所塑造的極具戰斗力和抗爭力的形象始終是值得稱道的大突破,真果敢。
二、與竇娥的比較
論及封建時期的婦女,定有竇娥的一席之說,竇娥、崔鶯鶯、杜麗娘這三個女人都是舊時封建時代的典型女人.但不同的是崔鶯鶯和杜麗娘都是一腔癡情追求愛情的女人,她們是封建時代與眾不同的少數存在,在她們的身上可以看到舊時的人們渴望打破封建的愿望和影子.竇娥則被烙下了悲劇二字,她出身悲苦、身份低微、想為而不敢為充滿了被動性,印證了上文中所說封建主義下婦女的反抗不具備普適性,但作為封建女性反抗的代表形象,崔鶯鶯和杜麗娘的確是一座豐碑。
結語:
今天的我們總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當著眼于貴族利益的封建社會中本階級的成員都有了反抗意識與行動,那就證明桎梏即將解開,作為貴族的兩位女性已經為當時的社會舉起了自由追求愛情、自己選擇人生的旗幟。她們溫柔、孝順但極具主見,性格中雖留有時代的烙印,但其超越傳統的深刻意義在今日也同樣敦促我們審視自身的價值與命運。